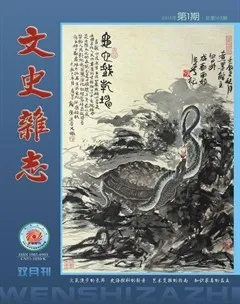谈谈《虢国夫人游春图》
一、《虢国夫人游春图》与唐诗《丽人行》
传统上说起《虢国夫人游春图》的创作背景,人们普遍认为是唐代张萱根据杜甫诗《丽人行》而创作的。它通过描绘天宝年间虢国夫人游春的场景,从侧面反映当时杨氏一家势倾天下的奢靡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从而也预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章采烈先生在其《<虢国夫人游春图>两摹本考议》一文中认为:“杜甫写了《丽人行》与《虢国夫人》两首诗,张萱则画了同一题材的画,显而易见不是偶然巧合,而杜诗在前,张画在后,张系感通杜诗而作斯图。” [1]许天浩先生也认为:“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根据杜甫《丽人行》而画,或由杜甫诗所引发灵感而画。”[2]
近些年,学术界中又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一味地把《虢国夫人游春图》与《丽人行》联系在一起有些草率,并没有切实的文献可以用来佐证两者关系。历代文人墨客都热衷于评述唐玄宗与杨氏家族的故事,但文学作品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夸大与虚构,用它来证实历史事实未免有些不科学;除非拥有充足的证据。
若进一步研究杜甫的《丽人行》,就会发现诗文所描写的内容与《游春图》有很大的差距。其诗主要是描述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场景。全诗分三段:首先描写了游春仕女体貌之美和服饰之华;然后描绘宴会的奢华;最后叙述杨国忠的权倾天下的霸道和有恃无恐的骄横。《杨太真外传》记载说:其“从官妪百余骑。秉烛如昼,鲜装袨服而行,亦无蒙蔽,衢路观者如堵,无不骇叹” [3]。然而在《游春图》中总共只描绘了九个人。如果是三家出游,骑从不可能如此简单。其次若是三家出游,张萱的画名该为《杨家游春图》而不是《虢国夫人游春图》。再次在杜甫诗中有“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句,表现路人不敢靠近游春的队伍,不敢仰视这些达官贵人的场景,但在张萱的画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笔者认为这一点的描绘很重要。如果张萱真受了杜诗的影响,描绘路人不敢仰视,才能体现出杨氏家族的骄慢无理,势倾天下的状态。就笔者来看,更倾向于《游春图》与《丽人行》无关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考虑时代背景,单纯地欣赏这幅画,画所描绘的就只是上层妇女出游的场景。从她们的神态来看,其并没有杜诗所描绘的骄横,而是面容安详,气质高贵的贵妇形象。她们都沉浸于出游的欢愉,醉身于盎然春色之中。
二、关于《虢图》主题人物的讨论
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全画共有九人,但到底哪一位是主体人物虢国夫人,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种说法。
1.首骑着男装者为虢国夫人
这种观点以陈育丞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作者为了突出主角,所以将虢国夫人画在最前面。马亦比较壮大,与后骑有所不同;并且唐代女子着男装为一时风尚,虢国夫人男装乘马是很寻常的事。在开元天宝年间,多爱三花饰马,三花者剪鬃为之瓣,这是一种贵游的标志。因为最前方的马不但剪三花鬃,悬“踢胸”(历代贵官乘马,红缨多悬于马之胸前),复鞍的障泥亦复锦绣炫目,也与后马不同。[4] 因此他认为最前面的一位为虢国夫人。但笔者有一个疑问,像虢国夫人这样拥有显赫身份的人物,在出游时怎么会被放在最前面?这不符合古代贵族出游队伍的一般布局。
2.怀抱女童者为虢国夫人
这种观点以张安治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最前单行的三骑是前驱,稍后两位服装明艳,使人注意力被吸引得渐渐集中,最后显示出主体。主角两旁的侍从一个红衫,一个白袍,和前二人在一起,正像众星捧月一样,反衬出主角的雍容、沉着的气派。中间二骑的服饰虽然艳丽,但是她俩的派头却差很多。她俩的发髻也和主角不同。二人之间很难分出风度高下,要指定其中的某一人是虢国夫人是很勉强的。如果说她们是较高级的女侍,孩子的乳母或虢国夫人的女友,应当要更合适些。[5]所以张安治先生认为最后一排中间抱着婴儿的为虢国夫人。但对这一观点,杨仁恺先生有质疑。他认为:“抱女孩妇人已经人老珠黄,毫无贵妇人风度,且列于队尾,哪有贵妇人出游亲自抱孩子的?” [6]笔者较认同杨先生的观点。古代贵族出游,孩子一般由侍女或乳母抱着。再说此妇人的长裙颜色较为暗淡。在唐代,贵族女子的服饰应该是浓艳、雍容与奢华的;可是抱婴者的衣着并不绚丽,且面容较为凝重,没有唐代贵族妇女的高贵气质。
3.中间并行的前者为虢国夫人
这种观点以杨仁恺先生和徐邦达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中间并行的两位贵妇中前一位为虢国夫人。杨仁恺先生认为虢国夫人姊妹并辔而行,正是全画的中心点。虢国夫人的脸庞非常丰润,确是淡扫蛾眉不施脂粉的本来面目。[7]他还认为历代画作主骑都是中间偏后,前有开道的,后有殿队的,这几乎已成封建定制。笔者较认同此观点。并行的两位妇人气质高贵,服饰艳丽,正符合唐代上层妇女的装束。
4.画中无虢国夫人
这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观点。2010年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来自辽宁省博物馆的研究者董宝厚对《虢国夫人游春图》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画中没有虢国夫人。此画描绘的也不是游春景象。他认为首骑与女童才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认为根据史籍文献记载虢国夫人骄奢不羁。而《虢图》中就骑鞍品制和马的品种来看,不能与虢国夫人相比。相对于其他画家的游春图而言,此画不但没有背景,更不见春的踪迹。[8]
对董宝厚先生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此处无声胜有声”,而《游春图》就有此处“无景胜有景”的效果。笔者认为,虽然整个画面没有直接描绘春景,而是在画面上留下了大片空白,但正是这空白给观者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每一个欣赏者都有自己想象中的春色,并且背景中的空白也更衬出前景人物的雍容华贵。这正是画者高妙之处。
三、《虢图》反映的唐代女性社会风貌
《历代名画记》记载:“指事绘形,可验时代。” [9]绘画作品可以反映一定的现实生活。在唐代出现了许多以女性社会生活为题材的画作。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就是一个很好的样本。笔者认为,通过其画可以窥见唐代女性的社会风貌。
此画描述的是虢国夫人带其侍从出游的场景,从中可以得出唐朝女性可以单独外出的结论。她们并不像历代封建社会中的女性受礼教制约,深锁闺中,足不出阁。唐代的妇女能够比较自由地参与社会活动。《开元天宝遗事》记载:“长安士女,游春野步,遇名花则设席藉草,以红裙递相插挂,以为宴幄。”“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 [10]这些足以证明唐代妇女社会地位比前朝及后代(仍指封建社会)都要高。她们对男子的依附关系也相应不太强。
画中女性脸庞圆润,体形较为丰满。这从侧面反映出唐代女性生活在一个礼教制度相对宽松的环境中。众所周知,唐王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思想活跃,对外开放,对内政策也比较宽松,有着海纳百川般的胸襟。唐代妇女普遍较为乐观,自信,开朗,豁达。女性之美也呈现出雍容富贵的景象,尤其在上层社会。唐朝以胖为美,是对盛唐气象最好的注脚。
画中的妇女衣着袒露装,色彩艳丽。在《旧唐书·舆服志》中对唐代女性服饰曾有这样的描述:“风俗奢靡,不依格令,绮罗锦绣,随所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 可以说唐代女性的着装在封建社会中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人们往往说袒露装是统治阶级腐朽荒淫生活的表现”,但高世瑜先生倒觉得,“这种装束正是唐代社会风气开放,妇女所受礼教束缚少的表现,也许还是唐朝人稍稍注意到了人体自然美的思想进化体现呢!” [11]笔者非常赞同高先生的观点,因为所谓袒露装应当看做是唐代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社会较为开放的重要表现。仔细观察此画,画中最前面的人身穿男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一名女性身着男装,作男性打扮。在唐朝非常盛行女着男装的风尚,此画也是对此很好的证明。在李华《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中有一段唐人对女着男装,男女衣无区别风气的评价:“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唐朝礼教比较松弛。笔者认为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可以身着与男性一样的服饰,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男女的平等,同时这也是对男权的挑战。唐代妇女渴望像男人一样拥有权力,治理天下。所以唐朝才会出现武则天、太平公主、平阳公主、上官婉儿这样的“女中豪杰”。唐朝女性的美不是那种小家碧玉般的扭捏羞涩之态,而是那英姿飒爽中带有豪迈之气的美。
笔者对《虢国夫人游春图》与《丽人行》的关系进行了简单的阐述,对目前学术界中关于画中谁是虢国夫人,有无虢国夫人的各种观点进行了罗列与分析。在笔者看来,古代的绘画其实也是一面镜子,既折射出历史,也反映了文化。通过《虢国夫人游春图》,让我们了解到属于那个时代的女性风貌;也让我们看到了当时那个充满活力、开放进取的大唐帝国领袖万邦的文明气度。
注释:
[1]章采烈:《虢国夫人游春图两摹本考议》,《云朵》,1992年第2期。
[2]许天治:《摭谈丽人行与虢国夫人游春图》,《 故宫文物月刊》,1987年第10期。
[3][10]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4]参见陈育丞:《关于虢国夫人游春图主体人物商榷》,《文物》,1963年第4期。
[5]参见张安治:《虢国夫人游春图》,《文物》,1961年第12期。
[6] [7]杨仁恺:《沐雨楼书画论稿》,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8]参见邹瑞玥:《虢国夫人游春图新解》,《光明日报》,2010年12月31日。
[9]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
[11]高世瑜:《唐代妇女》,三秦出版社,1988年。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