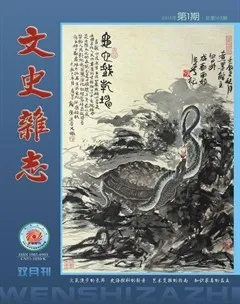简论孙中山的“国民国家”思想
“国民国家”是中国近代史上进步的思想家提出的一种国家观念,即国家是国民的或人民的,全体国民才是国家真正主人。与此相对的是“君主国家”概念。在古代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从来就只有“朕即国家”,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陆续传入中国,传统的“君权神授”观念受到动摇。近代西方思想的传播者严复提出:君民关系,只是一种社会分工,民才是天下的“真主”。[1]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也提出:先民之初,本无君民之分,君由民举,立君为民,“事不办”则“易其人”。 [2] “百日维新”以后,梁启超更进一步提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家之主人为谁,即一国之民是也。故西国恒言,谓君也,官也,国民之公奴仆也。”[3]这些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的言论表明“国民国家”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了。但在实践上,维新派仍追求“君民共主”的国家,把希望寄托于清政府的改革之上,走向了反对民主革命的一面,其结果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国民国家”。而在思想上和实践上真正追求“国民国家”目标的只有孙中山。
一
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创立兴中会时,其入会誓词写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这是孙中山第一次提出的民主主义革命立法,包含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两方面的内容。所谓“合众政府”,显然来源于美利坚合众国,美国建立的政府就公开宣示其国家的主权归属于全体人民。所以,孙中山当时提出的“合众政府”就有“国民国家”的意思。1905年,孙中山在同盟会誓词中把他的民主主义革命主张完整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其中的“建立民国”,即建立全体国民之国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明确地将“国民国家”作为政治革命的奋斗目标提了出来。
孙中山的“国民国家”思想与他反复宣扬的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是分不开的。为了论证建立共和政体的必要性,孙中山在兴中会宣言中展开了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尖锐批判,认为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是造成中国历史上国家长期纷乱和分裂的重要原因,称之为“恶劣政治的根本”[4]。为了证明作为“国民国家”的载体的民主共和制国家政权的先进性,阐明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孙中山批判了“谓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因而实施共和政治“殊难望其速效”的谬论,指出落后的中国可以向西方国家学习,比较迅速地建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正如“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情况,亦犹是耳”。[5]对于另一种所谓“中国今日亦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等而为共和”的谬论,孙中山驳斥说,中国决不能因袭部分西方国家的君主立宪制,而应当直接采用共和制。他作了一个巧妙的譬喻:“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逐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陋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6]当时还流行着所谓“中国人民知识程度不足,断不能行共和制”的谬论,孙中山也据理予以了批驳,强调只有实行共和制才能迅速提高人民的“知识程度”。孙中山并不讳言“数千年专制之毒,深中乎人心”的事实,认为决不能以此作为“不能行共和之制”的原因,恰恰相反,而应把它视为更加迫切需要建立共和制的理由。他坚信民主共和政治对于中国人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孙中山对于反共和制度的谬论的批驳,有利于民主主义的传播和启蒙。
二
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国民国家”?孙中山在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中对其表述为:“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7]孙中山在1906年制定的《军政府宣言》又指出,在这个标准中,最核心的是“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孙中山的“国民”概念是指全体国民,没有以资产来划分的阶级差别。从阶级斗争观点看来,国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工具,国民之间必须区别对待。孙中山是彻底的民主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从来就没有“专政”的成分,对全体国民一视同仁。他认为只有全体国民都能平等地参与政权的国家,才是真正的“国民国家”。
民国建立后,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临时约法》,共7章56条,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国民国家”体制。它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身体、家宅、财产、营业、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等自由;有请愿、陈诉、选举、被选等权利。”[8]由于民国初建,不可能迅速采取普选制,因此,它又规定:参议员由各省选派,临时大总统和副总统由参议院选举。这是当时形势所迫所做的一种妥协,但孙中山后来多次要求总统等国家领导人都应由全体国民普选产生。
孙中山为追求实现真正的“国民国家”,始终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民国初年,孙中山针对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显现的弊端进行了批判,说:美利坚、法兰西,固然是“共和之先进国”,但是,“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9]又说:“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10]在他看来,“据国家机关”的官吏往往“其如借人民选举以获取其资格,其继则悍然违背人民之意见行事,而人民亦莫之如何”。[11]至于“现代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有钱就卖身、分赃、贪利,为全国人民所不齿。”“各国实行这种代议政体,都免不了流弊。不过传到中国,流弊更是不堪问了。”[12]为了弥补“代议制度”、“间接民权”的缺陷,孙中山提出要实行一种“直接民权”。该“直接民权”就是要让人民能够直接参与国家管理,因此也称为“全民政治”。他说:“既曰民权国,则宜为四万万人民共治之国家。治之之法,即在予人民以完全之政治上权力。”[13]其内容可以表述为:“要人民能够直接管理政府,便要人民能够实行这四个民权。人民能够实行四个民权,才叫做全民政治。”[14]作为“直接民权的第一个”是选举权,它的内涵为实行“普选”而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15],同时强调“一切重要官吏要人民有权选举。”[16]其次,是与选举权相互补充的罢免权。孙中山对此比喻为,如同“公司之董事”由“股东选任,亦可由股东废除”,人民既“对于官吏有选举之权,亦须有罢免之权”。这样,人民便“对于政府之中的一切官吏,一面可以放出去。一面可以调回来,来往都可以从人民的自由”。[17]再次,是以立法权为中心内容的创制权。创制权和一般立法权的区别在于立法过程不经议会,而经由提议人起草议案,在征得一定数目的附议人后交付全体选民投票表决,获得通过后即成为法律。这类似于“全民公决”。最后,则为针对法律的废除和修订而言的复决权,即由立法院订立法律,人民可以用“公意”赞成或修改,或废除。孙中山认为,人民只有“能够实行这四个权,才算是彻底的直接民权”。[18]人民由此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任用、役使并防范官吏,管理国家大事,真正成为“一国之主”。这样的国家才可以称为“纯粹民国”。[19]为了使人民真正能行使四个直接民权,孙中山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方案,这是实施“民治”的主要手段;用孙中山的话说,就是“将地方的事情,让本地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20]否则, “中央及省仍行其官治状态,专制旧制,何以打破?”[21]官治是违背民主原则而必须打破的,“民治”意味着“主权在人民”,“官治”必须要为“民治”所更代。至于县以上,孙中山拟仍以立法实行代议制,由各县选举国民代表一名,参与中央政事,组成国民大会。国民大会对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和罢免权;对中央法律,有创制权和复决权。
三
孙中山的“国民国家”思想不仅强调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民权”,同时还科学、理智地规划政府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分配。早在1906年,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时就说:“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决是欧美所不能及的。”[22]这里的“社会的国家”就是孙中山对中国民主宪政蓝图的理想规划。他提出,要在西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基础上,新增加考选、纠察二权,形成“五权分立”,后被称为“五权宪法”。所谓的“考选权”,即“设立独立之机关,专掌考试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23]这不同于当今的公务员考试仅适用于一般国家工作人员,孙中山要求的是“大小官吏”,当然也包括国家领导人。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政府官员,孙中山特别强调它的独立性,不受国家其他权力机关的约束。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既有借鉴,也有创新。他一方面承认西方民主制度的先进性,同时对“五权分立”制度在西方国家演进中不断暴露出的各种弊病,又有清醒的认识,因此企图加以改进和超越。这些都反映了孙中山思想的深刻性,及对完美制度的不懈追求。独特的“五权分立”,在孙中山看来,“这不但是各国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学说上也不多见,可谓破天荒的政体”。[24]
孙中山颇费苦心地创设分权体系,其目的还是要在这些权力机关之间寻求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他认为“政治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里头的自由太多,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过,便成了专制。”[25] “分权”的原则所以合于“民主政治”的理想,就在于它使得“机关分立,……相待而行,不致流于专制”;同时,“分立之中,仍有联属,不致孤立,无伤于统一”。
人民和政府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就人民来说,拥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大政治权力,孙中山称之为“政权”,或曰“人民权”;政府拥有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纠察等五大权力,孙中山称为“治权”,或曰“政府权”。他认为,将两者结合起来,用人民的四个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权,就会形成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局面。一方面,人民可以指挥、控制、监督政府;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充分发挥效率,为人民办事,成为“万能政府”。这就是孙中山的“权能区分”政治构想。只有在“权”和“能”两个方面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国民国家”才算是真正建立起来了。
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谋求人民之幸福,需要国家政治生活的不断进步,孙中山认为,在民主立宪国家, “实际左右其统治权力者,亦常在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由他们“集合为政党,以领导之国民”。[26]政党政治是民主国家重要标志之一。同时,孙中山还进一步提出:“要知文明各国不能仅有一政党,若仅有一政党,仍是专制政体,政治不能进步。”[27]孙中山设想:“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28]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多党政治。有多党,必有竞争。对于党争,孙中山认为:“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29] “天下事非以竞争不能进步。”[30]孙中山把世间万物的竞争法则引入政党政治,认为只要“政党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有政争、党争是好事。孙中山还指出,一国国民只有通过行使普选权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才能决定由哪个政党领导政府。总之,孙中山的“国民国家”思想始终以国民直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为依归,在政党政治中亦是如此。
孙中山的“国民国家”理论,是他整个民主主义思想体系中的重要部分。它诞生于孙中山走上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之时,又在其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充实、改进、完善。在孙中山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史上面临社会转型的剧烈变动的时代,尽管辛亥革命的枪声颠覆了封建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顽固的封建思想及封建势力还依然强大,它们以各种方式同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相对抗。孙中山毕其一生,也未能看到真正的“国民国家”在中国建立起来。当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孙中山的“国民国家”理论自有其局限性。但是,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举民主主义大旗,为建立“国民国家”或“人民的国家”,勇于探索创新的开拓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仰的。
注释:
[1] 《辟韩》,《严复集》,第34页-36页。
[2] 《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增订本,第339页。
[3]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2卷。
[4][14] [15] [17][18][22][24][26][27][28][29][30] 《孙中山文集》上册,第23页,第226页,第403页,第226页,第226页,第26页,第29页,第350页,第354页,第352页,第358页,第509页。
[5] [6][7] 《孙中山选集》上册,第66页,第66页,第68页。
[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9]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8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54页。
[11][12][21]《总理全集》第1集,第1028页,第1028页,第924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6页。
[16][23][25] 《总理遗教》,第45页,第9页,第59页。
[19]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323页。
[20] 《总理全集》第2集,第299页。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