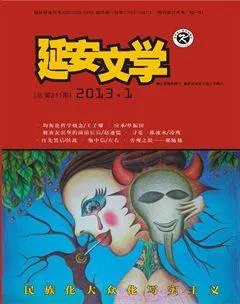乡村寓言
陈玉龙,江西都昌人。作品散见于《清明》《雨花》《芒种》《山东文学》《广西文学》等。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太阳先是泼妇似的毒辣辣盯着九爷那葫芦瓢似的头顶,盯得九爷大汗淋淋。倏忽间又像害羞闺女似的躲进那恶浪般的云层。待九爷舒心地喘口气时,黑云深处便传出一声爆炸,大地的震颤险些儿使九爷身边的几个女人跌倒。女人慌忙地看着九爷,说:算了吧,九爷。九爷抬起头,看见了天边几处耀眼的光闪,说:得抓紧哩,大雨马上要下来了。风就是在这时猛地刮起来的,风把女人们的薄褂吹得哗啦啦响,雪白丰硕的乳房在里面颤颤惊惊,九爷当作没看见。其这,她们也不对九爷忌讳什么,弯下腰去时,乳房与稻禾亲吻使她们体验到劳动的辛勤与欢愉。
脱谷机的轰轰声响丝毫不能掩盖云层深处的爆炸声,光光闪闪几乎使他们眼花缭乱。九爷再一次望天,突然对身边的女人们说:快停下机子,筛谷,要快。停下机子的女人们手忙脚乱起来,风扬起的谷屑在九爷的光脊梁上粘贴了一层麻面。九爷嘴里喊快点快点,手里帮着忙活,七八个人围着停歇的脱谷机,田里的箩筐很快就装满了。九爷在劳作时脸几乎贴在一个女人的肥臀上,一转身,手臂又碰上了谁软乎乎的一团,九爷没有停手,嘴里仍没停:快点快点,雨要下来了。
一长溜的女人们挑着筐担走出了田块。九爷是最后动身的,九爷挑着稻谷动身时再次望了一下天,一颗硕大的雨点正好打在脑门上。九爷“嗖”地一下蹿上田埂,肩上的扁担此时便咔嚓一声断裂。这时的雨点已不再是一颗两颗,九爷已很清晰地感到爆炸声早已钻出了云层就在头顶。九爷来不及回家换扁担,抓起抬脱谷机的竹杠,重新挑起了那两筐稻谷。雨点密集起来,厚厚的尘土味和稻禾味弥漫在乡野垄畈。九爷到家时,雨点早变成了一股狂烈的浓烟,村庄便笼罩在那片烟雨中。
女人们已站在各自家门口的屋檐下望雨,九爷的狼狈相自然要引起她们那夸张但却真实的嬉笑。九爷只穿着一条灰布裤衩,雨水淋透了,裆间的东西有些显山露水,女人们心照不宣地看了一眼,脸红心跳地扯着另外的话,一下子没了嬉笑的兴趣,回到屋里换衣服去了。
九爷倒没闲暇去换衣服,九爷要把女人们挑来的稻谷一筐筐地倒出来,在厅堂里的水泥地上摊开,还要到外面昨天收割毕的稻田里看看跑水了没有,还有明天的分工后天的安排……反正,九爷是不能闲的,九爷有许多事情要做,九爷的肩上责任重大。
雨当然是一场好雨,只不过是破坏了九爷的一点小小的计划。稻禾还没收割完,人受点累罢了。
雨一直下到晚上八点才停歇,村路屋沟,垄畈田地,到处是哗哗水声。这场雨下得很大,给干旱的季节带来了湿润,也使九爷对丰收的希望又添了一份信心。星星像太阳爆炸后的碎片散落在云层的缝隙处,田野里蛙声如鼓。雨后的凉爽使小村的人们都早早歇息了,只有九爷的旱烟管里发出的光点在楼屋顶上闪闪烁烁。九爷坐在这全村的制高点上鸟瞰着小村朦胧的夜景,九爷的心里便绽开了一朵生g30Pld2alQwQI+S8vmFlEg==命之花。九爷虽已不再是那种容易激动的年龄,但他常常被自己现在所处的地位而感动。九爷成了这个小村的一个标志或者一个代号。九爷很满足这种现状,甚至陶醉其中。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九爷只不过是这个村子的一个小小的小组长。但从九爷在小村的重要位置来看,九爷是小村的主心骨。因为九爷是村里唯一一个男劳力,偌大的上百亩土地便归九爷管辖,这是他的庄园,他是庄园主。在生产队的那个时代,九爷当了近二十年的生产队长。九爷没想到,在他晚年孤寂的生活中,会出现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九爷有时坐在自家楼屋顶上总觉得是一场梦幻。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轮到他来主宰全村,来管理曾经滋养着小村多少代人的广阔土地,而许多小娘们都要听从他的指挥他的安排围在他这个老头子的身边转?
都是机遇呵。九爷喷出一口浓烟后又射出一口浓痰。他看见前边那间低矮的土屋里透出灯光,九爷慢慢地下了楼顶,朝那土屋走去。
屋门虚掩着,九爷推开屋门便看见屋中一汪汪水摊,抬头看屋顶,破洞犹如天上的星星般闪耀。九爷说:秀英,你这屋要大修了。屋里走出矮矮瘦瘦的秀英,见了九爷,没有说话。秀英的丈夫前年死了,儿子和女儿都到外面打工去了,屋里就剩孤孤单单的秀英。凉爽的夏夜,叫人生出许多非分之想,走进秀英家的九爷心里不由得动了一下。秀英太瘦弱了,也太孤单了,白天许多女人小媳妇们在一起干活时,都是叽叽喳喳小麻雀似的,唯有秀英终日缄口不语。在众多的女伴中,秀英是唯一一位没有丈夫的人,而且又是她的年龄最大,四十一岁了。九爷亲昵地把手放在秀英的肩上,秀英没有拒绝。九爷说:秀英,今天累了吧,明天歇一天工。秀英在床沿的竹席上坐下来,说:不要紧,明天栽禾更要人手,菊花、二妹身上来了,不能下水。说到这儿秀英脸上有些羞涩,但对九爷来说就像盛开的一朵桃花。九爷拉着秀英的身子坐下,秀英本能地移动了一下身子,感觉到九爷粗粗的喘息声。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机会,秀英都痛苦地放弃了。秀英不明白快奔六十的九爷为何像个壮后生有那么强烈的要求。九爷没有结过婚,年轻时带一个女子私奔了一次,后来那女子嫁到了很远的地方,九爷就一直独身过日子。农村妇女秀英不懂得什么叫第二青春的。尽管她有时也有非常强烈的愿望,但仅仅只是愿望而已,毕竟离现实有距离。
九爷那晚没有回自己的家,就住在秀英那个破土屋里。凉爽的夏夜给他带来了机遇,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挑战。岁月是不饶人的,第二天清早起来扛着犁耙下水田时,九爷感到从未有过的虚脱。
栽禾的时候果然少了两个人。雨后的太阳更清新,田里的水面就如一面镜子,映出一张张各异的脸庞,也窥视出一个个不同的心思。栽禾其实是个挺轻松的活儿,最适合大家在一起说话儿,这无疑是女人们高兴的事情。九爷在抛秧,他望了望低头栽禾的秀英,不知为什么心里突然涌出一丝歉疚。秀英在这些女人中是最可怜的一个人,那些女人们对于这些农活总是嘻嘻哈哈无所谓的样子,有时会把九爷气得头皮发青。只有秀英每次总是听话地依顺着九爷的安排。九爷常常感叹今非昔比。想当年当生产队长时是何等威风,他安排的工作哪个敢不听,女人们更不敢打一点推阻。也许是因为只有秀英曾参加过生产队里的做工,所以才格外顺从九爷的安排。而那般小娘们哪里把九爷放在眼里,她们出来做工并不是想挣到多少工分,而是为了大家在一起多扯些闲话。远在外面打工的男人是不会计较她们的,公婆更不敢了。时不时地接着远方来的汇款单,便把这些田地活儿看得更轻了。
村里人也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忽地涌到大城市里去,特别是近几年,几乎所有可以走动的都走了,剩下一些老弱和带孩子的小媳妇在家务弄着责任田。其实,田地基本上荒废了,但没有谁心疼,没有谁在意。因为他们整日在田地里苦苦耕耘的收获竟然抵不上他们打工挣来的一个零头,谁还愿意脸朝黄土背朝天地种着田呐?今年他们县乡忽然有个规定,不能荒废责任田,否则要收取荒芜费。这是一个机遇,所以被九爷给抓住了,出外打工的人们一举推出九爷在家当他们的庄园主,去侍弄着责任田。要求并不高,只要不荒废了就行。九爷半夜笑醒,他要重振当年生产队长的雄风,一切按他熟稔的方式去管理去操作。遗憾的是半年多来的较量,九爷算是败下阵来。虫灾旱灾,减产是注定了的。更可气的是他在痛惜这粮食产量时,那些小娘们竟开心起来,说这样也好,省了她们许多力气。
九爷读过几年书,他的记工簿上密密麻麻。他想,年终分红,他要工工整整地把这些帐目公布在墙上。
栽禾的女人们忽然发出惊叫,接着乱蹦乱跳地跑上田埂。原来,有一个小媳妇的腿肚子上吸了一条大蚂蟥,那媳妇大喊:九爷九爷,快给我拉出来呀。九爷停下手中抛的秧,走到媳妇跟前,蹲下身子轻轻一拍,再用手一拉,蚂蟥蜷缩着贴在九爷的大指甲上,那媳妇的腿肚子上有血流出。女人们又是一阵惊叫。只有秀英没有做声,对于蚂蟥,想必是经见得太多了。那帮女人任九爷怎么发火,就是不敢再下田。九爷又吼了一阵,才见她们磨磨蹭蹭地下了田,栽几棵禾便要看一下腿肚子,进度慢了下来。九爷只有干瞪眼。
“双抢”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算搞完,不管怎样,九爷还是松了口气。九爷觉得该轻松一下,便学着先前生产队的做法,大家在一起吃饭庆祝一番。女人们听说这事,兴趣大增。爱热闹是她们的天性。她们立即行动,做豆腐,买鱼,买肉,闹出一种喜气腾腾的景象。桌子就摆在九爷的大空院子里,整整两桌人。九爷是没安排酒的,但女人们说也要学学爷们喝喝啤酒,自作主作地挑来了二十瓶。自然九爷坐上首,由众多女人簇拥着。九爷真是福分不浅哪。九爷是不胜酒力的,无奈她们都要敬九爷一杯酒,九爷也是个男人,能有不喝之理?一喝,就大醉了。女人们也都喝了许多,只有秀英喝得很少。一来她不喜欢啤酒,二来也不爱这样的热闹,与那些小媳妇们毕竟是隔了一代的人。那天的场面恐怕是小村特有的,脸色红艳艳的女人们嘻嘻哈哈你推我抓,像一群天真的小孩。院门外有小孩子来看热闹,被女人们轰了出去,把院门关了。九爷是独门独院,又是独自一人,屋子是清静的。坐在上首的九爷这时响起了如雷的鼾声。先是一个女人上前捏住九爷的鼻子,九爷似乎醒了一下,抓住那女人的手说:不要动我,让我困一觉。又一个女人上前摸了摸九爷通红发亮的光头,竟是汗腻腻的。九爷依然是打着赤膊,穿着一条灰布短裤,仰面靠在椅背上。忽有人兴奋地提议,把九爷的裤子脱了,看看是什么鸟样。立马有人响应。秀英脸色惨白地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来阻止这场玩笑。喝了酒兴奋起来的女人们是没有拘束的,也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了的。她们一齐上前把九爷扛起来,做一种她们孩童时代的“打撞”游戏,后来不知谁轻轻一扯,九爷的裤衩便被扯下来。女人们哄地笑开来。秀英猛地跑出院门。她们把九爷的裤衩挂在院子里的树杈上,风吹着啪啪作响,像一面历经战火的旗帜。女人们顿作鸟兽散,九爷仍靠在椅背上酣睡。
九爷是被一泡尿胀醒,一看情形,知道是女人们开的玩笑。九爷没有生气,反倒感到有一种久违的亲切。记得在生产队那阵,他也跟别的男女开过这样的玩笑。都是过来人,大家在一起开玩笑也并未出过什么事情。九爷光着屁股爬上树杈取下裤子,便摇摇晃晃地走出门来。先到秀英家,秀英在睡午觉,见了九爷,不理他。九爷借着酒兴本想亲热亲热,见秀英那么冷淡,讨了个没趣,竟自走出屋门。村子很小,十几户人家,屋场显得零零落落。大家都在睡午觉,女人们喝了酒,睡得更酣。有四仰八叉睡在厅堂中的竹床上的,也有睡在里屋的草席上。女人的睡姿各异,穿着也各异,有和长裤长褂的,也有短裤短褂的。在这个小村,女人们几乎没有什么忌讳,除了九爷还能算作一个男人外,其他的都不能算作女人意义上的男人。所以有的女人睡得很随意,露着雪白的大腿躺在厅堂里的竹床上。九爷见了,只摇摇头,独自回屋睡午觉了。
这一觉九爷睡得太沉了,及至醒来,已是日落西山,院子里是红彤彤的一片。女人们早在那儿收拾残羹剩菜,见了睡眼惺忪的九爷,都盯着他的光头笑。九爷知道她们笑什么,一点也不顾忌,说:你们偷着干不算本事,小心哪天我把你们的裤子脱下来,报今日这仇。有女人说:九爷你敢吗?要是你能脱了我们的下来,等年下男人回来就有你的好果子吃了。九爷嘴里犟硬着,心下却有点伤感起来。这些女人都是有宠着她爱她的丈夫的,男人在外做牛变马地挣钱,还不是为了他们的小日子过得红火吗?秀英虽没了丈夫,但总算有两个虎气生生的儿女,那是她的牵挂她的希望她的寄托所在。而九爷,他有什么呢?他曾经有过爱有过牵挂有过希望,可那都是久远年代的梦啊。梦醒了,也就烟消云散,什么都没有了。唯一有的便是这块庄园,这是九爷的兴奋点,也是九爷晚年的一次辉煌。但辉煌得起来吗?
看来这也是一场尴尬的玩笑,但对九爷来说,似乎沉重了点。
白天睡得太多,晚上当然睡不着,酷暑的日子在延长。九爷悄悄走出自己的院门。
星星密集地挤拥着,看来明天是个大热天。村庄上的沉寂是无法破解的,小村没有电,因而也就没有电视机之类的现代生活,谁能破解这沉寂的黑夜里那些女人做的各异的梦呢?
田野里却不沉寂,刚栽下去的二晚在夜色中滋洇生长,九爷几乎听到了那片拔节的唰唰声。这是一种极亲切的声音,还有那独特的禾苗味,无不刺激着九爷那不甘寂寞的心灵。往年,这片垄畈是荒芜的,其景其状以九爷的眼光来看是惨不忍睹。而现在,即使是黑夜里,九爷也可以看出一片绿来,这可是一片蓬蓬勃勃的生命呵。这生命是九爷赋予的,是九爷创造了这么多生命,并主宰着它们。九爷是这儿的庄园主,九爷是它们的上帝啊。九爷自个儿笑了。
九爷独自在田野里踟蹰着,下弦月不知什么时候悄悄钻出来,田野便露出了明朗些的脸庞。九爷抚摸着,亲吻着,像对待想象中的女人、儿子,目光含情脉脉。九爷干脆坐下来,把赤脚放进禾田里温柔的水中。他想抽烟,才发现忘了带旱烟管。不过,这也不要紧,有这温柔的禾苗,有这朦胧的田野,九爷可以不抽他的旱烟,可以踏踏实实坐在这个田埂上眺望着这片绿野。九爷就想,这样多好呵,就像睡在女人的怀抱中那样舒贴。
九爷坐在田埂上竟然睡着了,月色更明朗起来,露水越来越浓重,禾苗上已是湿漉漉的一层。
睡梦中好像一声巨响,九爷就醒转了。满眼的金光四射,禾苗似铺上了一层白银,新的一天就在九爷一睁眼工夫到来了。九爷抖擞精神站起来,急急向村里走去。他要向妇女们分派今天的工,自己还要到乡农技站买农药。村里早已有炊烟飘出,池塘的石板桥上女人们在洗衣服,调笑嗔骂成为小村夏天清晨的一大风景。九爷感到一种生命的真实和生活的厚重。
在去乡农技站回来的路上,九爷遇到了村委会的王专干。王专干姓王,全称是计划生育专干。王专干见了九爷,忙说:我正要去村子找你哩,省得我一阵腿脚,给你一个通知吧。九爷接过通知,原来是环孕检人员的通知。也就是说,那帮小媳妇明天上午都要赶到乡里进行环孕检查。九爷问:后天可不可以?王专干说:后天不行,就在明天,这是定好的,刘乡长主抓这事。九爷又说:其实,她们不检查也不会有问题的,丈夫年头就出了门,春季已检了一次,怎么会有事情呢?王专干一下来了兴趣,说:你这个当头的真是艳福不浅哪,她们的丈夫都把她们交给你,谁晓得你给没给她们播种呢?九爷伸手要打王专干的样子,王专干躲开了,说:九爷你别不相信,全乡有这样的例子呢。九爷没有时间多搭讪,把通知放进口袋,挑起地上的两箱农药。王专干叮嘱了一句:九爷,别忘了呵。九爷说:没问题的。
九爷当然没想到,王专干的预言在第二天竟成了现实。小媳妇们去乡里环孕检时,还真有一个出了问题。那个叫小月的女人已怀了两个月的身孕,要立即做人流手术。因为她前年生了一胎女孩,还没到间隔二胎的时间。丈夫年初出外打工已有七八个月了,怎么突然又有了两个月的身孕?这可是个大问题了。小月检查完后没有跟同伴回到小村,而是悄悄地回到了娘家。女人总是这样,娘家是她的保护伞,避风港,不管女儿犯了多大的错,娘家总是宽容地接纳的。
这几天干田地活儿时女人们在一起议论的话题就离不开小月了。小月本是上了环的,落环的事并不奇怪,怀孕的事就是个大问题了。起码说,小月除了丈夫外还有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是谁呢?小村除了九爷是找不出第二个可以使女人怀孕的男人来。那么九爷——女人们又开心地笑了,由此又想到那次脱九爷短裤的情景,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刺激。可一旦有了这样的推理,女人们看起九爷的眼光就不同了,终于忍耐不住,瞅着休息的空隙把九爷围在中间说:九爷,你要老实交待,小月的事是不是你干的?九爷对于女人们的审问没有生气,其实,他也盼着有这样的机会来洗刷自己,以便今后向小月的丈夫交待。九爷说:你们问得好,我是那样的人吗?女人们都看着九爷,没有做声。九爷知道用任何语言都难以证实自己的洁白,九爷只好指着天上明晃晃的太阳赌了一个毒咒。九爷心里轻松下来,女人们反倒觉得没有趣味,就像满怀喜悦去看一场自己喜欢的戏而到临场时却换了另一出戏一样。女人们的目光不再盯着九爷看,而思念起自己远在他乡的丈夫。有人说:还只八月,这日子过得太慢了。马上有人接应:过年也只有三个多月了,快的。又有人说:日子还是慢慢地过才好,快了,过年也就一晃过去了。她们都没有提到自己的男人,但心里却把丈夫的名字喊了无数遍。小月的怀孕,使她们增添了一份自豪和优越感,她们更有资格去想自己远在他乡的男人了。
九爷当然不懂这一切,也难以理解女人们的这种心思。当他催促着女人们做工时,女人们有些恼怒了。她们狠狠地瞪了几下九爷的光头,身子懒懒地干着田地活儿,心里依然延续着那份念想。
太阳辣辣地照射着脚下的土地,汗水也从身上叭嗒叭嗒滋洇进去,庄稼有灵性似的抚慰着九爷的小腿部,九爷便像拥着秀英的身子般全身心愉悦。早稻欠收,二晚争取夺个丰收吧。九爷当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一直是受表扬的人物,粮食年年丰收。孤身一人的九爷没有家庭,也就没有私心,真可以称得上全心全意为生产队。后来分田到户,九爷分到了一亩二分田,亩产依然是全村的首位。再后来,物价大涨,粮食不值钱起来,除了各项开支,所剩无几。小村几乎所有的劳力出外打工,大把大把的钱往家里寄,人们对田地看得更淡了。
九爷又在心里盘算着,等小月回来该如何处理好这件事。他必须向小月的丈夫交待,这是他的责任。由此,他又想到自己与秀英之间的事,竟有点不寒而栗。幸好秀英早实施了结扎手术,倘若不是如此,秀英再挺起个大肚子,秀英的儿女不把他给劈了?
一个礼拜后,小月回到了山村。小月的脸色苍白,并不仅仅是做了人流手术的缘故。小月很年轻,漂漂亮亮挺活泼的一个女子,现在她是无论如何也活泼不起来了。说严重一点,从此以后她将离开那个群体而独自沉默。不管小村女人的思想如何保守或者开放,在这件事上是无法沟通的。小月面对着一个难题,要不恪守自己的秘密,要不倾诉自己的苦衷以求得她们的同情,但无论怎样,都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小月是个生活很随便的人,以为上了环就万无一失,一个月没来潮还不以为意——以前也是有过的。小月回到家见到满脸鼻涕的三岁女儿,不由紧紧抱住,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淌。小月的公婆年迈,他们木然地看着小月,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晚上九爷独自来了,这是小月早就料到的。也许这事只有向九爷诉说才可以排解出胸中的一些郁闷。九爷先到另一个房间里给小月的公婆打了个招呼,而后堂堂正正来到小月的住房。小月的女儿睡了,毯子被蹬到脚下,露出两只胖胖的小手臂。小月拉过凳子给九爷坐了,九爷抬眼见小月的双眼红肿,心中便有些怜惜,心头暗想小月怎么看也不像那种女人,莫非有什么隐情?九爷捡起柜上的一把竹扇叭嗒叭嗒扇起来,天气还有些炎热,九爷也不大习惯年轻女人房间里的那种气味。九爷说:小月,这个事你看我怎么向大毛交待?大毛是小月的丈夫。小月哀戚地看着九爷,说:九爷,你可不能写信告诉他,会影响他在外面的情绪,等年下他来了我会主动交待。全村的女人中认识字的不多,九爷是读了几年书的,因而小村与外界的书信往来就由九爷代办了。九爷说:你能告诉我那个人是谁吗?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不问清楚我心里不踏实。小月说:你不认得的。他是我娘家人。九爷的心里似乎“咯噔”一下,他是想问出里面的原因,可又不好意思开口,不料小月这时却说:九爷,你不来我也会把这事告诉你的,你是俺村的主心骨,我也不想隐瞒你,但有一条你要答应我。九爷忙说:当然会答应的。小月说:你可要为我保密,包括我的丈夫。
九爷的头皮开始发亮起来。不要以为九爷是那种猥琐之徒,听到人家的隐私就兴奋起来,九爷是被小月信任和尊重才激动起来的,而这件事与九爷的想象相差甚远,九爷难以无动于衷。
小月的丈夫大毛看上去是个壮壮实实的小伙子,其实质里却是个外强中干的废人,新婚之夜的小月就以泪洗面。这样勉强过了一年夫妻生活,小月提出离婚。大毛是个爱面子的人,死活不同意,提出了个条件,他要小月为他生个儿子才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大毛是个孝子。当然他是不能和小月生儿子的,小月就和娘家的一个青梅竹马的后生好上了。没想生下一个女孩,计划生育抓得紧上了节育环,要间隔五年才可生二胎。小月的这种生活是无人知晓的,起码说瞒着了小村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公婆。现在出了这事,无论如何是不好向公婆和村人交待的。小月把这事憋在心里实在难受,现在吐给了九爷,总算轻松了一些。
九爷从屁股头边摸出旱烟袋,装上旱烟抽起来。昏暗的煤油灯下,小月苍白的脸上已和顺了许多。九爷没有说话,一个劲儿抽烟,半晌工夫,九爷才说:这事就当你没讲给我听好了,我知道明天怎样说给她们听。九爷在柜子上磕去烟管里的一颗烟屎,站起身来,望了一眼床上的小月的女儿,倏忽觉得那张脸很陌生很丑陋。小杂种儿!九爷被自己心里蹦出这样的话儿吓了一跳。他踉踉跄跄走出那屋门。
九爷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敲开了秀英的屋门。一进门,九爷紧紧把秀英抱住了,秀英嗔怪道: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年轻的后生了,等下吧,先给我儿子回封信。前几天她儿子来了信还有一千元的汇款。九爷却“噗”地一声把灯吹灭了,说:明天吧,明天中午写,晚上眼睛不好使。
第二天的太阳地里,九爷对身边的女人叹了口气说:小月真是太不幸了,两个月前回娘家被一个蒙面持刀的歹徒给强奸了,才留下这颗苦果。女人们听过此话,问九爷怎么知道。九爷说:昨晚我在村里走动,见小月在房里准备上吊寻死,可吓了我一跳,急忙解下绳索,才逼着她说出了实情。小月说她没脸见人,更对不起她的丈夫。女人们仿佛自己被强奸了一样,说:那个千刀万剐的强奸犯,抓住了没有?九爷说:没有,他蒙着脸又拿着刀,逃了。女人们的眼前便出现了那样一个情景,心想自己遇上了怕也只有乖乖就范。这样一想对小月不由同情起来。晚上女人们都到小月家去看望了她,劝慰了许多话,当然也大骂了一阵那个胆大的强奸犯。小月的公婆也过来了,对小月说:出现了这样的事,我们也不怪你,今后回娘家千万小心一点。女人们在小月的房里叽叽喳喳说了半宿,后来竟传出了快乐的嬉笑声。
天气很快转凉了,庄稼也长得十分茂盛。由于灭虫工作做得好,二晚的禾苗绿郁郁一片,在风中犹如海洋中的波浪,九爷舒心地笑了。农活有点闲散下来,九爷给女人们放了两天假,自己仍然忙乱着。
那天晚上九爷刚睡下,有人急促地喊他。九爷灵巧地下床穿衣,开门一看是桂珍。桂珍焦急地说:九爷,孩子发高烧,快给我去看看。九爷慌慌跟在桂珍的身后来到村头的那幢屋内,见七八岁的孩子面红耳赤地躺在床上,手一摸额头,烫人。孩子迷糊着,口里说着胡话。桂珍几乎是带着哭腔:九爷,孩子要不要紧呀?九爷不是医生,但九爷是村里的主心骨,九爷的话就是真理。她多想九爷说声不要紧睡吧,但九爷没这样说,九爷说:孩子的病很要紧,赶紧送医院吧。桂珍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九爷说:哭什么,到医院就不要紧了。九爷背起孩子,说:走吧。桂珍问:要不要喊其他人?九爷说:算了,她们都有孩子,走不开身,闹得惊惊慌慌,一村子的人都睡不好觉。
到乡卫生院有二十里路程,九爷背着孩子和桂珍走在这没有星光的夜空下。野外黑糊糊的一片,不时从哪个角落里发出一声响或者鸟鸣,要在平时,桂珍果吓得惊叫起来的。但现在,桂珍对这一切置若罔闻,她不敢想象,这小村要是没有了九爷她该怎么办。九爷真是个好人,等年下丈夫回来了一定要让他去九爷家谢这个情。二十里的路程,不是说到就到的,九爷感到背上越来越沉重了,他想停下歇口气,可又不敢这样做。桂珍说九爷让我来背吧,九爷知道她是绝对背不动的,连走路都喘个不停。九爷就那么艰难地向前走着。黑夜里走路越显漫长,因为四周没有让人分心的景物,一门心思只有放在这无尽的山道上。桂珍开始听到九爷大口大口地喘起气来,桂珍上前一只手托着九爷背上的孩子,一只手搀扶着九爷,这样好让九爷身子轻松一点。
九爷被桂珍温热的身子搀扶着,九爷想这样轻松多了,九爷没想到脚下一个沟坎正在等待着他,一脚踩进去,人一趔趄,身子就跌倒了。桂珍也没提防,跌在了九爷的身上。幸好孩子被九爷牢牢抓住在脊背上没被摔着。桂珍爬起来,九爷也艰难地爬起来,九爷明显地感到双腿的异样和疼痛,九爷没有吭声。
前面有星星在闪耀——啊,那不是星星,那是乡街上闪烁的电灯。九爷抽出一只手摸了一把脸上的汗。桂珍说:九爷,快到了,快了。
背上的孩子仍说着胡话,九爷在桂珍的搀扶下终于走进了乡卫生院的大门。
医生给孩子挂吊针的时候,九爷靠在了那个长椅上,等他想再站起来时,脚腕处的疼痛使他怎么也站不起来。医生问怎么了,桂珍回转身说:刚才跌了一跤。医生卷起九爷的裤袖,用手轻轻一捏那疼痛处,九爷“哇”的一声倒抽了一口凉气。医生说:骨头断了。九爷吓了一跳。桂珍一下子哭了起来:医生,这可怎么好啊!医生很冷静地看了桂珍一眼,走了出去。不一会儿进来一位年长的医生,对九爷说:躺下来吧,是小骨折了,可以治好的。
桂珍的孩子三天后便出院了,可九爷在医院躺了一个礼拜后才拄着拐杖下地走动。九爷说什么也要出院,便在乡街上租了一辆自行车推着回村。九爷住不惯医院的床铺,再说也放心不下田地里的庄稼。在住院的日子里,女人们轮流来照看他,还带来了好些慰问品。九爷很感动。九爷想这些女人别看平时对他不怎么样,可关键时候还是记着他的。特别是秀英对他就更为不同。秀英是个很难交往的人,但你一旦交往上了,她就会把心把肝地对待你。
回到小村,九爷拄着拐杖到田野走了一遭,见庄稼活儿干得好好的。自从他住院,女人们反而更自觉更卖劲。女人们不傻不懒,女人们平时只不过是在男人面前撒娇罢了,尽管只有九爷这样一个男人。
庄稼一日成熟一日,看样子丰收在望了。九爷的腿也渐渐好起来。秋收冬种一搞完,一年的辛劳也基本结束了,那么他这个庄园主肩上的担子就可以轻松放下来。待严寒一到,便可以坐在火炉边享受着一年来的胜利成果,期待着外面男人们的到来,把丰收的成果连同他们的女人完完整整交给他们。
九爷天天晚上做着这个梦,九爷觉得这个梦是有点辉煌的,他当然不会想到他是以另一种辉煌来照耀小村的。
每天晚上,九爷都要在小村巡视一番。这巡视的时间也没个定准,有时是睡前,有时是睡了一觉过后,反正,全凭九爷的意愿。九爷那天晚上是睡了一觉后出来巡视的,像往常一样,他轻手轻脚,好像生怕惊醒了村人的美梦。巡到秀英屋门边,忽觉有异。大门竟是虚掩的。难道是等我进去,给留了门?九爷这样一想心里一热,正要进去,屋里忽然闪出一条黑影,闪身就往村外跑。九爷猛地回过神来:有贼!他急转身紧紧追赶,那黑影背上背了一个蛇皮袋,里面鼓鼓的,显然是赃物。九爷大喊一声:给我站住!黑影没有停留,但脚步慢了许多。快要追上时,黑影猛地停住,回转身说道:给我滚回去吧,再要追,老子就不客气了。九爷哪里见过这等猖狂的盗贼,冷笑道:你不放下东西,我可要喊人了。黑影说:你敢!嘴里不住喘气。九爷这时忽地一声长喊:抓贼呀——寂静的夜里,悠长的声音飘进了小村的家家户户,许多人的窗户都亮出了微弱的煤油灯光。女人们颤颤惊惊地扒着窗户往外观望,没敢打开大门。睡梦中的秀英听清了九爷的呼喊,爬起床后见大门敞开着,心里什么都明白了。她急着大喊:起来抓贼啊,有贼偷东西了。声音阴惨惨的,有几家女人打开大门又给关上了,屋子里的孩子被吓哭了,她们也吓得乱抖。这时又传来九爷的呼喊,秀英一惊,她又喊:九爷赶贼去了,大家快直来捉贼!
桂珍起来了,小月也起来了,她们跟着秀英胆战心惊地朝着刚才九爷喊叫的方向走去。
黑夜沉寂下来,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刚才只不过是谁的梦呓而已。寒风冷飕飕的,三个女人手拉着手向着那个路口走去,不知谁一声惊叫:贼!三人几乎软瘫下去。待定睛细看,却是躺着的九爷。三个女人扑上前去,摸到了九爷胸前一摊湿黏黏的东西,是血。九爷手里还抓着那个蛇皮袋,对秀英说:这是贼在你家偷出来的,拿去吧。
九爷是在清晨死去的,九爷的胸前被捅了一刀,血把他的灰布褂裤染红了。
九爷的事迹上了报纸,那个歹徒在报纸刊登的第二日便自首了。九爷的辉煌事迹照耀着小村,可惜,九爷看不到。
田地里的庄稼成熟了,沉甸甸的稻穗向人们报告着丰收。小村的女人们却没有一点丰收的喜悦。九爷没了,谁来分派她们的工作,谁来当这个庄园主?还有,明年这大块大块的田地怎么办?谁又来给她们念信写信呢?她们真盼望着男人们早点回来——没有男人,就没有主心骨啊。
冬天来临的时候,小村的垄畈里还有许多稻禾没有收割。寒风中的谷穗在痛苦的呻吟中坠落。村委会的村长经过那片垄畈,见了这情景便对小村的女人们说:我们要收你们的荒芜费呵。
寒风中,女人们没有做声,目光一齐转向村头的那道山岭。
责任编辑: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