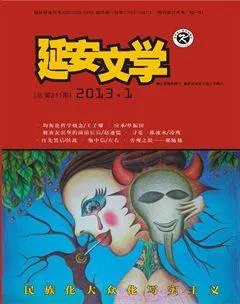澄清·喟叹和郝随穗的书写
郝随穗的写作,涉及多种文体,就我所见,以散文为优。他是个情性突出的人,对生活的概括和对艺术的传达常常浑合。多年来,正是这种独特的语言背景和艺术张力互为澄清,见证着他在写作领域的持续进步。就此而言,他对生活的书写具有一种悖论式的特色:每隔一两年,他写作的方式都在变化;每隔一两年,他笔下的刻画力量都在增强。前者是在写生,后者却是在创造。这种变与不变的犹豫和长期拉锯过程,构成了郝随穗生活性书写与精神性书写的双重收获。
作为一匹在梦想里负重驰骋的奔马,他的诗歌和小说显得过于透明,那里挤满了蜂拥而至的热烈情绪,也缺乏必要的冷却。造成层次的阴影部分和引发兴味的想象在分寸上还不是那么准确。与此对照,就可以见到他写散文的好处:在散文里边,那个情怀卓异的写作主体似乎放得更开,也足以聚集充分的才华去调整思路,随物赋形,抓住那飞在智慧天空下、转瞬即逝的无形之鸟。在这种相对准确的更为适宜的文体方案里,那本来不在其位的词语变得驯服,磁铁般的思想场域指引它们迅速皈依到信念的各个角落。
暴雨有力但往往落在空处,河流依岸却穷尽风景。
从暴雨到河流,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郝随穗在写作中的精神历程。
与之伴同的,是精神主题上产生的涣散和凝聚、炽热和冷静的差别。这是前后迥异的两个阶梯式层级,但对郝随穗而言,又常常交织在一个具体的难解难分的书写现实里。他和其他写作者之所以产生类的区分和质的异同,全在于此。就文章而讲文章,郝随穗散文写作的公共性和为我们所熟知的摇摆不定的私密性质,有时候结合得很好,有时候却突然散架,就和他对那两种精神主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直接关联。在学院式的文学理论讲堂上,主题涣散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被称为“动机冲突”,而在我的命名范畴里则称之为“动机排异”。观察经典作家,不难知道:一个写作动机成熟后,它就势必排斥与之异样的其它竞争,哪怕新来加塞的动机是天才的产物。艺术传达的力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大越好。有时候,这个“多”和“大”产生的矛盾近乎无解。在文学的历史上,大作家因此而写不下去并导致作品成为烂尾楼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茅盾的一些长篇小说和卡夫卡毁掉的众多底稿。那个有名的寓言里讲过,四个大雁从不同方向拉一辆马车,结果可想而知。促令一个作品难以分娩出来的阻碍,经常性的,就是这故事里的一堆大雁。写作的智力原则在这里会以强烈的理性排斥动机簇里那些试图帮倒忙的同伴。现代写作的智性化趋势,更是强化了这一原则。
郝随穗好像不太看重这个基本事实。个人以为:他对散文的“杂”有时候追求得稍微有点过头。看过某一部分带有写生性质的作品,我感到他的散文在有些情况下真的太“散”了。就“写作动机必须集中有力”这一点来说,肖云儒先生当年在特殊年代和特定背景下提出的“形散神不散”的散文本质论正在成为一个陈腐的教条,严重阻碍了新一代散文家的成长。
有时候,常识比教条来得更尖锐。
一个深具精神性的又领先他人的创意主题,在郝随穗这里常落得两种不同结果,一旦他排除了来自其他动机造成的杂念,一旦他写得凝聚而冷静,那个作品便无可置疑地高人一筹,也因而造就出一个集中而动人的形象;反之,凡是涣散而又单纯依靠众多情绪产生的热气球勉强升空的文章,都严重缺乏前进动力,自然也就丧失了令人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说,当他写得越单纯,结果越理想,当他写得越繁杂,即越“散”,结果却必然趋向令人叹惜的脸谱化的简单。精神生活可以无限错杂、丰富,但对于它的表述却必须简练、准确。在写作的进展阶段,需要最大限度达到准确,这是第一位的。写作的柔情蜜意永远不能体现在对主题之外的杂念和芜杂的材料的留恋不舍上。在这个方面,是保持材料尽可能杂乱,还是尽可能简洁呢?这是个大问题。形散神必散。这几乎是无可置疑的状况。我看,写散文的作家们有必要在这一点上狠下心,斩除文中芜杂的根须。
在完成精神较量和主题选择以后,郝随穗的书写真正开始了。
郝随穗散文所属的类型是某些评论家们曾经界定过的“艺术散文”,或叫“纯文学散文”。这种散文的一般特点是:从文学的立场与眼光出发看待身边的事物,抒发观察者的感情和艺术化的思绪。这种散文现在发展得很快,并越来越接近随笔,风格自由,面貌各异。郝随穗艺术散文的精神主题来自他的故乡——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大陕北——他多年来耕耘着这片创作的沃土,从中发展出他的文学见解,也很好地寄托了他的文学理想。以我的阅读体会来说,我觉得郝随穗在这个文学王国里发现了一个分量很大的事物,那就是“陕北”。我个人认为,陕北现有的本身的形象和它在文学世界里的形象是有差异的,在文学世界里“陕北”是美的化身,是自由的化身,当然,也是北方所特有的壮烈情怀的化身。所以,文学中的“陕北”形象,是自由民的热土和美丽的家园,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地”这个宏伟的存在,象征了二者合二为一的“精神的北方”。
三边地域之大,可以纳下所有的高天厚土。这里的天蓝得干净,有白云飘过,那也是被清洗过无数次的白。这里的大地上始终刮着不小的风,风展的旗帜、头发以及衣襟从没有停息过对大地的情感表露。所有的天空把那片蓝聚集到这里,所有的大地把心事汇聚到这里来抒发,所有的高天厚土集合在三边多少年来不曾分散。(《三边三日·三边》)
一个城池的灵魂像击碎的瓦片,洒落了一地。一个城池的容颜像醉了酒的壮士,红了脸庞红了江山。西门台,这个最隐秘的城池和悲壮,这么多年来悄然蜗居在陕北大山深沟中,独享岁月落尽的安详。(《三边三日·西门台》)
郝随穗对这个延续近一个世纪的主题做出的贡献在于:他不是从观光客的好奇出发,而是从一个作为“生身父母”的存在物的灵魂之痛写起,他想要写出的大概是这北方土地上广泛而久远的喟叹之声。这个“喟叹”,不是悲伤的叹息,不是偶尔为之的感怀,却是有所预谋的写作指向,它指向了大陕北的内部皲裂,和那种岩石裂纹般的美学质感。这是力图从事物内部发起暴动的激烈角逐,建立其上的表情质量无疑是凝重、沉酣的,是具有男子气质的历史继承和寸土不让的语言复古,是对一个久被埋没的故乡意在此而言在彼的象征化叙述。此叙述不是如此这般的叙述,而是饱含转折意味的纵向开掘。
郝随穗散文的普遍语法规则是:“XX是这样的……但是XY是那样的。”这个XY就是郝随穗最终要落实的那个包容一切XX里的人文变数的大陕北,是其历时不变的东西,或者说,就是那个“文学的陕北”。通常,被他书写到的XX都是构成XY的一部分,比如父亲(《红尘父亲》)、母亲(《再望当年明月》)、某一地方(《三边三日》)、某一历史遗迹(《廖工桥》)、某一植物(《老家的味道是槐香》)。只要从所写的事物中追踪到它与陕北的内在关联,乃至隐约发现那种精神的相关性,这个文章对他就成立了。“文学的陕北”和秉承其基因密码的变动不居的人文风景,这就是郝随穗创作激情的来源。在历史纵深处,他寻找到一个令人感喟的画外音。他在书写技艺的巅峰时刻,摆脱了一个溜冰艺术家的花哨,走向沉着、奇崛。
槐花依旧如约而来,冲破春寒料峭的冷日子硬是在一片阳光中白花花地开满一树花儿。等到槐花开满山坡的时候,似乎所有的树木都归顺了槐花,在这温暖而明亮的阳光里竞相绽放出甜丝丝的香味。
在陕北,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嗅觉盛宴,唯有槐花能够在这片土地上酣畅淋漓地挥洒出这漫天遍地的香味。这恰似大地的胭脂味,给荒凉了一个冬季的陕北大地平添了几分妩媚和浪漫。(《老家的味道是槐香》)
综合地阅读郝随穗这些散文后,带给我很深的感动。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内心也情不自禁地激发起一声感叹:我们的生命,为什么总是这么平凡啊?
比照起那个更大的并远远比我们存在得更其久长和愈发伟岸的故乡,我们禁不住要发出这样的喟叹。可是,我们热烈而深沉的喟叹在北方大地沉默不语的包容里显得多么苍白。
我们的喟叹也许可以达到苍凉,但永远达不到故乡的苍老。我想,这就是郝随穗在近期一些散文里频频写到故乡的原因。他是真的心有所感了,并清清楚楚地意识到那个感受的临界点在哪里,而作为个体的人的局限又在哪里。
我看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