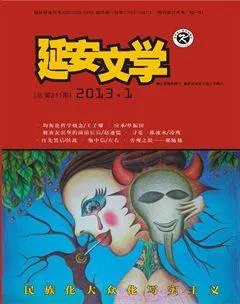迷恋故乡谈论问题:文化及历史
郝随穗是这样的一位作家:他迷恋故乡,谈论问题,抒写文史,他喜欢把散文当作史诗来写。
关于他散文写作的地域性问题,很容易让人想到沈从文的边城,莫言的高密,或者福克纳的小镇——一个作家内心无限伸缩的世界。他畅通无阻地在精神和文化的故乡任意表达。可能是由于虚妄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这种矛盾的焦虑感,带来的结果是为作家确立一种身份的认可——乡村知识分子,因而他在遭遇城市日常生活的庞杂和琐碎之后,开始寻找精神的归属感,并试图还原时代黑白的内容。
我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作家确立公共的地理意义的书写坐标,并展开自我的辩论、旁白,并且布道,但这样处理的结果消解了日益庞杂的细节能力,遮蔽了原乡的意义:故乡成了异乡。这种地域鲜明、个性公共化后的符号化和概念化,构成了读者的后置的被植入的经验。而这个被放大的“地方”成了许多所谓乡村知识分子追忆的来路。
我在故乡侨居变得才有批判的意义。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经验,艰难明晰的相关情感,已经变得无可依靠。从这个意义来说,经验的书写是靠不住的,充满疑虑地不断寻找失去的故乡,可能会使原本真实的故乡变得更加模糊,命名可能变得重要起来。虚拟的中国故事里的故乡成了我们衣食无忧的田园牧歌。
但弑杀故乡的情结也无处不在,它成了我们这代人身上不可抚平的情感伤口。我们从故乡到他乡,从他乡到异乡,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达另一个地方,故乡于是变成了小三。不停迁徙的故乡和他乡,使得作家要么迷失自己,要么过于迷恋故乡的非凡意义——因为我们要为它立言、立碑、立传,布道者不说家常话。
再回到郝随穗的散文。我喜欢他写村里的王老五这样的小人物们。这些鲜活的中国人的命运历程,他们在不停轮回。无论地理的故乡如何变化,人性总刻骨铭心。我想这是故乡于我们的意义。
谈论问题是哲学的书写。无论中外,经典的文学向来如此。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只要人类的困顿还在,这样的宿命永远存世。诗人屈原《天问》把问题抒写到极致,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勇敢的艺术超脱,让后来者高山仰止——他是最早把诗歌当哲学来写的诗人。作家能够谈史论今,浮想联翩,这从来就不是什么问题。在物我化的写作中,个人的重心是对时间的进程作出修正或判断,但在丰富和残缺的线装文明的两极冲撞中,取舍成了作家的问题。价值的意义是让我们表达合理的想象,以便切入当下的最日常的问题。
那些遥远的、不可捉摸的、尘封的历史或生活史,我们需要一层又一层细心地剥落它。真相通常在背光处,所有的疑难杂症都在骨子里。我们每走一步,十分吃力,又经常靠不住。那么捷径又是什么?它是个圆周,不说和少说,便意味着呈现。
我一直对关于文化的和历史的散文写作表达退缩的意愿。我觉得戏说和仿材料式的胡说,字正腔圆的理说,假大空的谎说,都具有隐蔽的欺骗性。对于读者来说,猎奇的心理是人类的共性,越是离奇,越是荒诞——文化不复,历史无存,这对于散文写作的谈论问题是极大的伤害。文史不分是散文写作有史以来最大的问题,这样导致学术规范不严谨,散文写作不鲜活。
文化或历史应该怎样被抒写?把我置于历史之中,作为旁观者,又要假若自身是当事者和见证者,这是复杂而困顿的。冷峻而准确地抒情,需要作者一颗强大的不为所动的心。我想说的是,历史不需要表演,但我们的写作却成了表演。
读了郝随穗有关文化和历史的《黄河过客》《帝国童话的质感》等篇章,我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想站在历史和文明的面前说话,但说着说着就成了个垂头丧气的人。而郝随穗即使说了很多话,还是一个理直气壮的人。
栏目责编:杨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