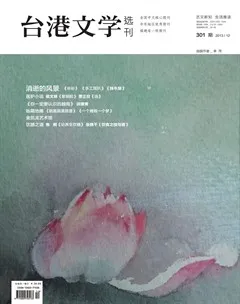炼毒小酒馆

“安南姑娘有一个迷信,只要情人抽了鸦片,即使远去法国,都一定会回来。抽鸦片会斫丧男人的性能力,但是她们宁可要情人忠诚而不在乎性能力。”葛林在《沉静的美国人》中如是说。
是什么原因让葛林在《沉静的美国人》开头的第三页就毫不避讳,甚至相当自恋地描述当年他在西贡一天可抽上四管鸦片的真实情景?据葛林自己说,他第一次抽鸦片的感觉很好,就像是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而你知道自己将与她发生关系一般。
除了葛林,莒哈丝在小说《情人》里也提到了她那位生性凶残、不学无术的大哥嗜吸鸦片,而莒哈丝的中国情人提到自己的父亲时,也曾这样描述:“十年来,他鸦片烟不离口,面对着湄公河,躺在行军床上经营他的财产。”
不仅合法,还拥有保全系统的鸦片精炼厂
五十年后,我来到这座让葛林吸了三年鸦片烟的城市,也终于在一间过去曾是鸦片工厂、现在名为“炼毒”的欧式餐厅找到了答案。
“炼毒”坐落于胡志明市中心Park Hyatt Hotel旁边。一想到这里曾是法属印度支那最黑暗、最不堪的烟毒地带,心里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唏嘘感慨。
我想正是因为鸦片,让受过英国军事情报六局训练的葛林,对越南的了解比任何人都更深刻。他像一个老练、顾人怨的卡珊德拉,不仅亲眼见证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法国的失败,也精准预言了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越战)美国的狼狈,只不过赋予他神力的不是太阳神阿波罗,而是那一缕缕,渊薮的,鸦片烟。
还记得历史课本里的中英鸦片战争发生于公元1840年吗?
其实法国人用鸦片控制越南人的卑劣手法是跟英国人学的。大约从1880年开始,越南鸦片正式进入鼎盛时期,现在胡志明市的Hai Ba Trung、Le Thanh Ton、Thi Sach、Nguyen Sieu四条路围起来的区域,当年就是一座大型的“合法”鸦片工厂。
到了20世纪初,越南因三项垄断事业而造成国力积弱不振:鸦片、酒、盐。荒谬的是,鸦片是当中最不受攻击的,因为人们认为要不要抽鸦片可以自由选择,但酒是越南的文化,而盐是民生必需品。在这样的认知下,1914年光是鸦片的收入就占了越南国家总预算将近四成,而炼毒小酒馆前身的鸦片工厂,一直运作到1954年法军撤出越南后才正式停止。
2006年,这座鸦片工厂正式挥别了声名狼藉的过去,两年后,这里成为胡志明市最受外国人青睐的一间餐厅。走进这里,圆拱的门窗、老旧的照片、复古的地砖、铜色的吧台、斑驳的残壁、待沽的版画…… 一切的一切好像是1950年代萨特与西蒙波娃会去的巴黎小酒馆,谁还会记得当年这里存放着一箱一箱的鸦片?
越南鸦片生活史
1950年代西贡的有钱人(特别是华人),宁愿小孩去吸鸦片也下愿他们染上赌博,他们认为吸鸦片至少还待在家里,而且吸鸦片的花费比起偿还赌债所需的金额要少很多。因此即使有人只剩一个肺,每天还要抽上一百五十管鸦片,或者有人吸鸦片吸到像葛林小说中描述的“他瘦得似乎不占空间,薄得就像饼干罐边上的那层防油纸”,大家也都睁只眼闭只眼。当年那些吸鸦片的越南华人甚至拥有自己的金融体系,吸鸦片吸到可以组成俱乐部来招揽同好,真叫我这个“卫道人士”大开眼界。
事实上,当时在印度支那的外国人,不只葛林,有许多法国军官即使自己不抽,三不五时也会主动作东,呼朋引伴去鸦片烟馆感受一下那种特殊的气味与氛围,可见当时吸鸦片是一种社交活动,而且葛林第一次吸鸦片就是一位法国官员带他去的。
据说吸鸦片有许多规矩,例如你不能让烟在肺里停留太久,因为这样代表你很穷,你必须要顺吸快吐,这样才显示你根本不在意这些鸦片有多么昂贵。而装填鸦片也是一门艺术,需要娴熟细腻的技巧,无怪乎葛林在小说中需要“凤”,一位温柔纤细、深谙此道的越南情妇来帮他打理鸦片。
周末下午的热巧克力布丁
周末下午四点以前,“炼毒”只供应早午餐,选择虽少但酷得有理,因为我在这里吃到有史以来最好吃的Omelette,光从简单的煎蛋卷就可测知这儿的料理绝对美味。
还要特别介绍一下“炼毒”的热巧克力布丁,布丁一反柔嫩的口感,乍吃第一口以为是玉米做的,再吃第二口又觉得是米糕,到了第三口你还是很狐疑,于是干脆把铺在上面的一球冰淇淋推到旁边,不顾布丁烧到烫嘴的温度就这么一口接一口地吃完,咂咂嘴之后仍是不解,终于问了厨房,原来布丁是用杏仁渣做的,无怪乎有一种粗犷却又不失精致的口感。
至于主餐,从一堆外国人与日本人争相光临的盛况来看,我相信“炼毒”一定不会让热爱美食的你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