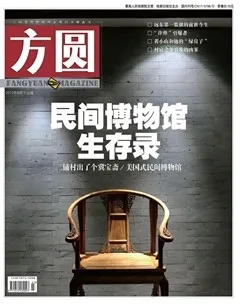远东第一监狱的前世今生

提篮桥监狱会不会关闭,现在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但在监狱附近居住的人们时时为拆迁做着准备
1903年投入使用至今,号称为远东第一监狱、东方巴士底监狱的提篮桥监狱在今天看来,算是外国殖民主义者侵犯中国司法权的产物。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段,提篮桥监狱先后经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日本人、汪伪政权和国民政府的“四朝”统治,各种政治力量轮番在提篮桥登场谢幕。如今,这座上海黄浦江畔私密、坚固的建筑物,因为一则要拆迁的传闻重新被人提及,关于此地的记忆又被人重拾……
提篮桥钩沉
上海地处江南水乡,河道纵横,不但桥梁众多,而且桥名色彩缤纷,带有几分诗情画意,如枫林桥,白渡桥。作为地名的提篮桥最早可追寻到清代乾隆年间,当时上海吴淞江下游的江边上有一座下海庙,该庙原为当地渔民供奉海神的庙,渔民、农民和其他香客为了进香方便,就在吴淞江的支流下海浦建起一座宽6尺、长3丈的木桥,进香的人提着篮子,带着香烛过桥拜佛,桥因此得名“提篮桥”。
昔日小桥流水的提篮桥已成为通衢大街,但名称依然保留。如今提篮桥区域的范围一般为:西北近杨树浦路和惠民路,南接黄浦江,西至东大名路南端,东北临霍山路,西北通海门路一带。但在大多数上海市民眼中,提篮桥,指的是一所监狱,或者说是上海监狱的代表。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通过《南京条约》首先在上海建立英租界,接着美国人也来到上海滩,在苏州河以北地区建立美租界,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成立公共租界。随着殖民统治的日益加剧,上海各巡捕房的监舍设备拥挤不堪,1868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厦门路建立了主要关押英国籍犯人的监狱。1895年11月工部局警务总监唐纳·麦肯齐向公共租界董事会提议设立一座新监狱,并拿出一副新监狱的草图,全部设施约需要6万两银子。后来经过公共租界董事会批准,在虹口新建监狱,于是唐纳·麦肯齐买下了靠近霍山路的22亩土地。1903年5月18日,新监狱交付使用时,整个监狱其实是围在一垛17英尺高的界墙中。
初建时,监狱大门开在今天的长阳路111号,规模比较小,除去办公楼,炊场等设施外,只有两幢各4层的监舍,共480间牢房。后来公共租界的押犯人数急剧上升,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记载,1903年底监狱押犯仅156人,1911年底达1302人,1927年底竟上升到2457人,所以提篮桥监狱在20世纪20年代,就陆续向北和东面扩展。
当时,提篮桥监狱东边基本上没有什么房屋,仅有中国人搭建的几间平房和一两间小店。在工部局的干涉和批准下,提篮桥东边的爱尔考克路(今安国路)被圈入监狱的范围内,几户居民另行搬迁。到1935年,进过几轮扩张后的提篮桥监狱已经占地60.4亩,形成今天监狱的规模,其建筑风格是英国式的,共有各类监室3700多间。有人形容,如果一个犯人每天换一间监室,10年下来,全监狱的监室他还没有轮遍。由于提篮桥监狱建筑精良,规模宏大,又大于同时期的印度孟买监狱、日本巢鸭监狱,因而有“远东第一监狱”之称。
这座远东第一监狱在1903年投入使用至今,又被称为东方巴士底监狱,今天看来算是外国殖民主义者侵犯中国司法权的产物。在上个世纪的前半段,提篮桥监狱先后经历公共租界工部局、日本人、汪伪政权和国民政府的“四朝”统治,各种政治力量轮番在提篮桥登场,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汪伪政权、国民党当局各种政权匆匆而过。众多历史风云人物如章太炎、邹容、张爱萍、任弼时、江上青、周立波、陈璧君等人都曾在此羁留。在时光流转中,那些因为各种因素曾囚禁于此的名人反过来给提篮桥监狱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公共租界时期的司法
作为上海滩最重要的入口监狱,提篮桥监狱不但关押了中国人还关押了外国籍犯人。这也与上海滩风云变化的历史有很大关系。
提篮桥监狱于1905年起开始接受第一批外籍犯,到1925年8月,因为时局原因,所有外籍犯被移押到厦门路监狱关押。到1935年9月,厦门路监狱被撤销,所有外籍犯人又重新回到提篮桥监狱。1937年8月13日,日本人侵犯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提篮桥监狱一度处于中日作战区,曾有炮弹击中监狱围墙,造成部分犯人伤亡。在紧急形势下,关押外籍犯的监楼暂时关闭。外籍犯全部放出,轻型犯提前释放或假释,重刑犯移送香港等地。
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外籍犯大多是在公共租界内犯罪,人数不多,最高峰为1938年的562人,涉及来华的20多个国家的公民和一些无国籍人,案由为杀人、抢劫、强奸、纵火、吸毒贩毒、酗酒闹事、私藏军火等30种。
旧上海分为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大行政区域、三大司法体系,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主要来自公共租界区域。这些犯人有些是经过领事法庭判决的,但大部分是上海地方法庭判决的。由于判决单位不同,犯人的管理费用来源渠道也不同,这导致外籍犯人在提篮桥监狱有两种伙食标准,由领事法庭判决犯人的管理费用由各国领事属(即领事馆,彼时上海称领事属)开支,伙食标准高,而由上海地方法院判决的犯人管理费用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开支,伙食标准低。
当时在提篮桥监狱里,中国籍犯人和外籍犯的待遇也不同。比如监狱内有一幢“十”字状监楼,专门关押外籍男犯,建筑面积6500平方米,还建有电梯。另有一幢“一”字形、专门关押外籍女犯的。这些关押外籍犯的地方成为“西人监”,单独围城一个院子与中国籍犯人分开。西人监内有140间单独囚室,每间8平方米,远大于普通的3.3平方米监舍,而且配有固定的单人床、凳子甚至抽水马桶。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收回租界,上海形成统一的行政和司法管理体系,提篮桥监狱仍然关押了来自东欧和朝鲜等几十名外籍犯人。一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上海监狱系统在对外籍犯的管理中开始坚持贯彻与中国籍犯人同等管理的原则,外籍犯从此一律穿起囚服,佩戴罪犯标志。
在公共租界时期,提篮桥监狱内的管理人员根据国籍是分层的,它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各国在国际地位上的差别。监狱的最高长官典狱长大多数由英国军人出任,监狱下设的科室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人、俄国人、挪威人、西班牙人等,统称西籍人员。负责监房看守的看守员因制服袖口上的几道横条,俗称一道头、两道头、三道头,三道头级别最大,他们主要是印度人和菲律宾人。
1930年,一起由50多名印度看守举行的监狱大罢工,给英国人管理的监狱在管理理念和人员的构成上带来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人开始进入提篮桥的管理层。
当时,提篮桥监狱典狱长拟在200多名印度看守中提拔一名中层管理人员,但声望颇高的49号看守意外落选。于6月27日,监狱中的四分之一印度籍看守实行罢工,监狱管理工作顿时乱了套,犯人的日常管理、包括用餐、放风都没了时间感念。值班看守该下班,没法下班,各岗位该接班的,没人接班,有的则是拆东墙补西墙,到处借人。
英国驻沪领事最后采取强硬手段,对出头的印度籍看守以“煽动罪”问罪,对其他参加罢工的看守一律开除公职。不少印度看守丢了工作,只能暂去虹口东宝兴路的一个印度教堂内栖身。
在看守人员缺额的情况下,华人很快被纳入看守的行列。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年报》统计,到1934年底,华人看守已经占到所有看守总数的42.5%。到193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犯罪学博士学位的浙江余姚人严景耀出任提篮桥历史上第一任华籍典狱长,华人在租界的地位上开始逐渐提高。
民国抗战的往事
提篮桥所在的虹口区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是战场中心。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日本的海军陆战队从提篮桥附近的汇山码头登陆,向虹口、闸北进犯,次日拂晓,中国军队向日军发起全面反击。此时的提篮桥监狱一直处于炮火的前沿,原本驻守在监狱担任警戒任务的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俄国分队撤离。炮火袭击下的提篮桥监狱多次遭到日军的轰炸,累计有9名犯人被炸死,70多名犯人及12名看守受伤,多处监舍被炸。 1945年7月17日抗战胜利的曙光到来时,提篮桥一带的隔离区再一次遭到轰炸,这次是来自盟军美国人的“误炸”。
“飞机在头顶上呼呼的飞,我们以为日本人又来了,一枚炸弹掉在舟山路那里,还有几枚落在了居民的楼顶。当时我15、6岁记得很清楚。”
这是一段史书上很少提及的插曲。2013年8月1日,今年82岁的宋仁飞在他家的祖宅里,向《方圆》记者回忆了那个血色的午后。
时年15岁的宋仁飞当时还在日本人管理的上海国棉十九厂做童工,他的家就在提篮桥附近的临潼路上。7月17日那天潮湿而闷热,天空阴云密布,几声空袭警报刚刚响过,炸弹就开始倾泻爆炸,很多老房子被炸毁。由于虹口的大多数房子没有地下室,为了躲避横飞的碎片,一些家庭在桌子上堆上床垫,空袭时就钻到桌子底下避难。
宋仁飞的母亲从四行仓库那边跑回家里,带着宋仁飞兄弟姐妹一行人往河边跑。“村里的人都躲在杨浦路、军工路,那些一听到炸弹声就往屋子里跑的人好多都炸死了。我们躲在河浜的斜坡上,就没事。”
轰炸过后的第二天开始下雨,雨水透过炸坏的屋顶和墙壁灌进房子里,泡坏了内壁,毁坏了难民和很多居民积累的家当。
这场误炸还导致了提篮桥区域31名犹太难民死亡,500多人受伤,700人无家可归。当时与提篮桥监狱相隔不到百米的就是日本人在虹口设立的“隔离区”。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为逃避纳粹屠杀,数以万计的欧洲犹太人逃亡上海,这其中至少有一万四千名犹太人被强迫迁入提篮桥一带的隔离区内。如今提篮桥监狱对面的舟山路上一排维也纳式的阁楼建筑就是当时富有的犹太人留下来的。
欧洲犹太难民到达上海时,大多数身无分文,他们先在提篮桥的隔离区落脚,当地许多学校、仓库和兵营被匆忙改建成收容所,各收容所容纳300至600名难民不等,男女分开居住,最大的一件屋子可容150人。初来乍到的犹太难民一时很难找到正式工作,他们只能到处打零工,干些杂活糊口,如送煤球,修电器、卖报,渐渐地他们开始跟中国居民杂处。当地上海居民虽大多属于社会底层,但他们为犹太难民让出房子、介绍工作,甚至给他们送去炊具,教他们生煤炉。
宋仁飞回忆:“尽管我们跟这些犹太人在提篮桥生活了好几年,但很少有说话的机会,他们很多人被圈在一个范围内不能随便出来。”在虹口隔离区一带,两处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被日本人在出口处焊上了铁栅门。
共同记忆之地
建国后,宋仁飞离开国棉十九厂,进入大学深造,后来被分配到上海元件五厂一直做到车间主任退休。由他负责的车间生产的半导体元件曾伴随着我国第一款试验卫星东方红号进入太空。关于提篮桥监狱的往事,宋仁飞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民使用的“劳动牌”扳手就是里面的犯人制造的,还有一些光学仪器也是里面生产的。
在提篮桥一带生活的人们或多或少对监狱有过直接的印象。舟山社区居委会离监狱仅隔着长阳路相望。每逢有车来送犯人时警笛大作或者士兵出操时发出的洪亮声音,住户们都能本能地识别出声音的方位。
宋仁飞的三女儿宋建萍告诉《方圆》记者,她在1983年生儿子时就住在与提篮桥一墙之隔的虹口区中心医院,病房的窗户对着监狱楼顶,每天早上她都能看见穿着囚衣的犯人成排站着倒马桶。
在较长时间内,上海人的口语中,“提篮桥”就是监狱的代名词。提篮桥监狱既具有重要的司法功能,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价值。1994年2月,提篮桥监狱被上海市政府列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单位”,也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座在原地保存完好并使用至今、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大型老监狱。
在众多虹口区老年人眼中,提篮桥不仅仅是一座监狱,而且几代人的上海记忆。因为历史上与犹太难民的重大渊源,提篮桥也成为犹太民族的“诺亚方舟”。以色列前驻沪总领事兰·毛尔曾说:“除了提篮桥地区,全世界所有犹太人在二战中聚集过的地方都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但展示的都是扭曲、杀戮,只有提篮桥展示的是友谊、阳光、生命。”
位于提篮桥监狱斜对面的长阳路62号摩西会堂,当年曾是许多犹太难民维系宗教情感的所在,如今作为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对外开放,述说着犹太难民在上海获得新生的过往。
2013年8月2日11时,在摩西会堂的诵经台下,来自以色列的耶赛胡·巴山和比拉·巴山夫妇聆听着大学生志愿者张驰的讲解。在听到载着到达上海的欧洲犹太难民的卡车队通过外白渡桥驶向提篮桥难民接待站时,比拉默默地流下眼泪,她激动地对在此场的每一位中国人用英语说:“我爱上海,我爱中国人。”正是70年前,提篮桥一带底层的中国人收留了巴山夫妇的祖父辈,才让他们有机会来此凭吊那段充满温馨的往事。
今年58岁的宋建萍曾是南京某冶金单位的员工,2003年单位被上海宝钢接管,在缩减人员的政策下,43岁的宋建萍早早退休。如今,她每天早上会去霍山公园是带领一群老年人跳伦巴,70多年前这个公园是犹太人避难的唯一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