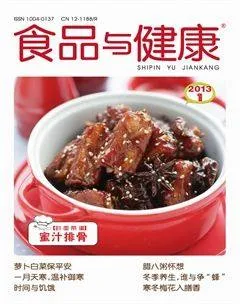陕北记忆
土 炕
一到冬天,总是想起老家的土炕。
老辈人传下一则谜语:“一个老牛没朵榔(朵榔,陕西方言:头),一家大小都驮上。”谜底就是土炕。乡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炕,大多是两面靠墙、一面连灶的满间炕,足够承载祖孙三代一大家人。炕和锅灶之间有一道尺把高的矮墙,叫背栏,饭做熟了,炕也烧热了,老家人把这叫隔山掏火。炕上靠近背栏的地方烧得最热,不光暖和,盛饭递碗也方便,所以通常是老人的专属座位。
炕用泥巴和土坯垒成,故称土炕。农村不缺柴禾,割罢的麦秸,秋后的苞谷杆,足够一年烧锅煨炕了,这叫烧炕。炕在陕北农村和锅灶一样不可或缺。很多民谚俗语都与炕有关——自给自足,日子过得滋润,就说“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愿受冷去露天看戏,就说“好唱不敌热炕”;媳妇生娃做月子,叫“上炕了”。寒冬腊月,一家人围坐在烧热的土炕上,铺开大厚褥子,或拉家常,或看电视,女人们通常会拿出针线笸箩,纳鞋底,缝棉衣,准备一家老小过冬的穿戴。婚丧嫁娶的家庭大事也都是在热炕上商议敲定的。屋外白雪飘飘,天寒地冻,屋里欢声笑语,暖意融融。家里来了人,主人一边拥促着“坐炕,坐炕”,一边把炕上最热的位置让出,不会顾忌你把裤脚上的泥巴带到炕上。那份质朴、随意和热情让人感受到浓浓的亲情,比坐在客厅里矜持地品着茶,少了些拘束,多了些亲和。
生活在小城的人大多数来自乡下,虽然不务农事,却总也摆脱不了与生俱来的土气,总觉得睡在炕上比睡在舒适绵软的席梦思床上踏实、解乏,因此老家的好多人搬进城里的单元房时,特意在房间的一隅盘一面炕,满足自己的怀旧情结。不同的是这种炕用水泥和厚铁板盘成,外表贴上光滑美观的瓷砖,炕洞里放一个蜂窝煤炉。据说这种独具匠心的盘炕方法一度让一些能工巧匠很吃香,需要四处打听、提前预约才请得到。
傍晚的乡村,远远望去,青烟袅袅,静穆的树木和房屋笼罩在缓缓流动的暮霭中。正是家家户户烧炕做饭的时候,有经验的农人会根据烟的形态和走向判断第二天天气的阴晴。此情此景,使人顿悟“人烟”一词的真正含义。
铁 勺
铁勺曾经是陕北农家重要的烹饪工具,在今天的陕北农村已不多见了——铁制的,碗口大小,带一个长柄。炒菜时往里滴些油,手执柄端把铁勺伸进大黑锅底下的灶膛里,借着烧锅的火烧热铁勺。把油烧得冒青烟时,赶紧抽出铁勺把切好的菜放进去,再伸进灶膛炒熟,炊烟缭绕的屋子里便飘起一阵混合着油烟味的菜香,老家人管这叫“油滚菜”,视为佐饭佳肴。
因为沾油和烟熏火燎,家家的铁勺又黑又亮地挂在灶间的墙壁上。铁勺炒鸡蛋是艰苦年月里孩子们的奢望,大多数孩子只能在生日那天享用到。过生日了,一放学就跑着回家,祖母小心翼翼而又郑重其事地从炕头那个平时谁也不能动的瓦罐里摸出一个或两个鸡蛋,递给正在做饭的母亲。母亲把筷子伸进油瓶中蘸些棉籽油在铁勺中烧热,倒入搅拌好的鸡蛋糊,随着滋啦啦的响声,香味马上弥漫开来。一会儿便有邻居端着饭碗进来问:“今天谁过生日啦?”过生日的孩子则在兄弟姐妹馋涎的目光中有滋有味地享受着这份属于自己的珍贵菜肴。
铁勺炒的鸡蛋,香味里有淡淡的柴烟味,今天的煤气灶、电磁炉搭上精致的炒锅是绝不会炒出那种味道的,那种味道香得铭心刻骨,伴随它让我记起的,除了过生日,还有老屋、炕头、柴火灶,这些奇妙的温馨回忆,几十年来萦绕心头,挥之不去。
乡 俗
在陕北民间,有些被视为禁忌的言语或行为是说不得、做不得的。如小孩子喊腰疼,长辈会马上阻止:“说不得,细娃哪来的腰!”小孩子不解其意,明明裤带系在腰上,我怎会没有腰呢?长辈们只是笑笑,并不说破。从孩童直到成年,这个问题一直困惑着我。忽然有一天我恍然大悟,其实说小孩子没有腰是为了避讳,因为“腰”、“夭”同音,“夭”是未成年人的一大忌讳,小孩子说出这个不吉利的字眼自然要委婉地绕开。再如幼儿闹了病,就说“不乖”或“变狗娃了”,“病”字也是说不得的。还有,老人们通常把“半碗饭”谐音成“抱碗饭”,这也是为了避讳,因“半”、“拌”同音,“拌碗”即摔碗,秦地有习俗,人刚倒头(死亡)时要拌碎一个碗。
这样说不得的话还有很多,如诅咒的言语,冒犯神灵的言语,忤逆犯上的言语,揭别人短的言语,不吉利的谶语等等。人们被告诫说了此类话,呼噜爷(雷公)会掐掉鼻子或遭其他报应。与此相呼应的还有一些行为是做不得的,如月亮、太阳、神像以及父母、长辈的脸面是用手指不得的,否则手指会短一截;吃饭时筷子竖插在碗中、盛好饭后筷子横架在碗上都是要不得的,这样不吉利;白米细面糟践不得的,否则会遭罪;还有房屋“前不栽柏,后不栽柳”等等。
老家的这些禁忌在潜意识里对人有一种神秘的约束力,使人的言行有所顾忌,不至于过分或出格。淳朴的乡下人凭着与生俱来的善良以及敬畏自然、敬畏神灵、敬畏生命的本能,对这些禁忌的理由不去深究,却自觉遵从,以自己的悟性恪守着心中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