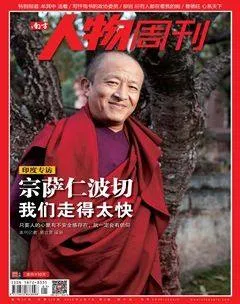服饰与政治
近日,在广东省委书记交接大会上,汪洋穿着中山装亮相,引人注目。
“中山装”据称是孙中山亲自设计的。孙中山解释说,衣服是按照共和国理念和“五权宪法”设计出来的——5个口袋装的是“五权宪法”,3个袖口扣子代表共和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另3个扣子代表的是“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后人穿起“中山装”,则更多就是以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之嘱托来自勉。
汪洋说:“5年前我是穿着西装来与大家首次见面的,今天我将穿着中山装离开,带走的是广东文化,中国特色!”
的确,政要穿着打扮,一直是人们热点关注的问题。近期有两本“奇书”在世界权力圈被广为阅读:一本是英国时尚名记罗伯·扬的《权势穿着》,另一本是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现身说法《读我的胸针》。
每逢国家盛典时,奥巴马必穿美国货“林荫大道”皮鞋,丑闻缠身的克林顿为讨好民众而着“华盛顿装”,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十年不变的阿富汗披风和羊皮帽只为突出阿富汗的“国际存在感”。
政要对服饰的迷恋,很大程度上是受政治动机所驱使,懂得在复杂的政治氛围下如何包装自己。例如,奥尔布赖特会见萨达姆时,戴蛇形胸针,以示强硬。
但也有一些拙劣的领导人,纯粹出于奢侈与自恋,沦为服饰政治学上的笑柄。据说,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西服上的条纹,全是他的名字。他的自恋,正好投射到权力上的恋栈,最终遭人唾弃。
服装与权力个体有如此密切的关联,同样也关联于在国际舞台备受瞩目的重要国际组织。
以APEC组织为例。1993年,美国倡议每年召开一次领导人峰会,但环太平洋国家差异明显,贫富、人口、宗教、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国力等方面,存在千差万别,难达共识。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复杂的经济体之间的主权关系,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原因则是,美国急于找到一个平台来拉近被西方国家80年代末孤立了的中国,但西方对华的制裁依然还在。
为了平抑峰会的“强度”,以消除有顾虑的成员的担忧,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开创性地制造了一个概念,叫“非正式会议”。为突出“非正式”政治,要求成员国领导人和地区领袖及代表,穿便装参会,以营造轻松的气氛。1996年,东道国菲律宾在会议期间,突然拿出一件“神秘礼物”——送给每位领导人的一件被称为国服的“巴隆”。礼物人手一份,领导人欢天喜地,穿着“巴隆”, 一起照了“全家福”。
峰会服装从便装回归统一服装,这不仅是审美情趣上的事,更是一种政治信号。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2011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到时与会领导人将穿上夏威夷风味的“草裙子”和“花衬衫”。然而,到2011年,时局变迁,“中国元素”无处不在,昔时为接触中国打造的平台,已经变得越来越没有现实价值。2011年夏威夷峰会时,奥巴马以金融危机节约开支为名取消了两年前承诺的“草裙子”,没有穿便装的集体照,峰会也被美国另起炉灶的“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所取代。TPP的邀请单上再无“中国”。2012年的APEC峰会上,奥巴马干脆就没有出席,峰会也再无统一的华丽民族服装。一些成员国扬言,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其领导人断不可接受穿上“和服”。
APEC服装的盛衰,就是地缘政治权力变迁的图景。服装上浓浓的政治意涵,是生来就给政治家们准备的,品味出服装里的政治气息的领导者,服装会为他的政德起正面作用。那些只是把奢侈服装当时尚的,或把新奇服饰作品位的,除了昔日世袭帝王之外,再无政要会幼稚到接受这样低级的形象包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