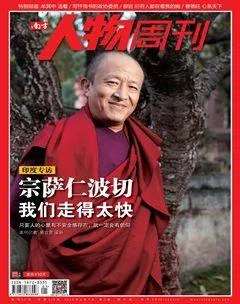初入社会
辍学之后,父亲经常对我甩臭脸,所以我也尽量不留在家里,闲来与邻居或一些顽劣分子到处游荡,亦有和先前在校内和Party认识的所谓兄弟联络,不时打架生事,无聊至极。
母亲没工作,所给零用实在有限,我亦不想加添母亲的负担,所以也急于找工作。经姐夫介绍到香港湾仔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作,那是一间外资公司,规模十分大,地处湾仔,外表全是红砖,像一座大堡垒,很是特别。我是经特殊关系才得到这份工作的,当时我还年幼,工资已算优厚,日薪8元,还供给午餐。因为姐夫是厂内的工程师,我才能得到这份优差。
我的工作是杂务,通常留在仓库里跟班,最多是跟仓务员替烟叶照虫。那些装烟叶的大桶,高逾十多呎,我们要登木梯才可爬进里面照虫。虽然看似简单,实则也很辛苦,桶内除了烟虫外,烟叶也很湿臭,气温又闷热。每天由家里出门,搭公车到码头,再转搭渡轮过海,那时又Vm8POxN7Ca9NH40xkGSrxQZiDuzWQkgeo7xNvTvr7WA=刚好是冬天,寒风凛然,在过海期间常常冷到龟缩一角。
大约半年后,我被调到包装部。那里是很先进的机械化部门,工作也比较舒服,只可惜我对加工烟草的化学气味,有特殊不良反应,闻到会作呕胸闷,最后抵受不住,向公司辞职。到现在我也不吸烟,最大原因在此。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这样完结。姐夫和家人都以为我怕辛苦才不干,对我也有微言。这份工在当时并不容易找到,姐夫花费了不少人力和物力才取得。当时要找一份普通的学徒,还要铺保和人保,还经常受气,能到那样一家大机构工作,简直是梦寐以求,我就这样放弃,实在辜负了他的一番努力。他们不大相信我辞工不干的原因,我百辞莫辩,也委屈了一段时间才释怀。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特别烦躁,经常和区内的坏孩子冲突,也涉及一些帮会分子,他们有时更会上门找我寻仇,结果惊动了父母亲,又给臭骂一顿。就在此时,我开始产生了离家的念头,一来免了家人的啰嗦,二来也避免有事时连累家人。
数月后,我和几个老友到旺角街边摆摊卖毛衣,生意不错,第一次尝到自己赚钱的滋味,开心得很,几个兄弟一起到一间宾士餐厅酒廊庆祝一下。这晚是我第一次喝醉,可惜好景不常,供应我们毛衣的公司断货,其他的又太贵,结果就此打住。
这时我和旺角同年的帮派分子也混得越来越熟,闲时和他们去Party“沟女”(泡妞)或去跳茶舞,那时入场费只需两元,吃东西另计,可带女朋友,并提供香片茶一壶,白瓜子一碟。场内有乐队演奏,中间有一大舞池可供多人跳舞,场内男男女女都穿得很新潮,我也不例外。这些地方正是是非与罪恶的温床,因争风呷醋或其他鸡毛小事也会“开片”(打大架),我也参与过不少次,战战兢兢,侥幸没有受过严重伤害。
就这样浑浑噩噩又过了几年,年纪大了,我也成了小头目。在这段日子里不多不少也做过一些法纪不容许的事,但正行的事我亦有做,也混得不错,女朋友也有一大堆,自问年轻的时候也算帅哥一个。
其实在这几年中我也做过几份正行工作,一份是在新蒲岗新马制衣厂,那时李嘉诚就是在那里开胶花厂。另一份工作就是在旺角火车站旁的一家保龄球场,那时球瓶给打倒后需要人手把它摆好,我就是做摆球瓶的工作。当时保龄球是高消费的玩意,场内装修很高档,有一个相当大的酒吧连餐厅,让打完球后的客人饮酒进餐。这里薪金不高,唯工作容易,最重要是酒吧的领导人俗称“Barking”,他对我很好,晚上除了给我留宿外也可喝酒吃东西。在这里差不多待了一年多,一天部长叫我到经理室,说有同事见到我和几个非公司员工在宿舍聚集,更严重的是看见有几把利刃,所以要把我辞退,我也只好“执包袱”。
之后惟有全身出来混,又找到一份在“社”(即妓院)带小姐的工作。那时的尖沙咀酒吧林立,又正值越战时期,很多英美舰队的水兵都乘休假期间来到香港玩乐。他们大把美钞,也很舍得用钱,很受吧女们欢迎。我就是在街头兜搭他们,价钱是Whole Night(过夜)150港元,性交易一次港币50元,我也因而学了不少洋滨径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