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伟岸的山
我一直相信仁爱、善良、智慧的父亲吉人天相,老天会保佑他活到八九十岁,可他带着我们的思念和人生的遗憾匆匆远去了。
父亲出生在重庆綦江一个小富的传统家庭,爷爷在他两三岁时就病逝了,有些文化知识的奶奶管理起家庭,养育了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1947年,在重庆读书的二哥在一次房屋倒塌事故中丧生(这起事件在电视剧《凌汤圆》中有描述,是国民党贪腐军官为陷害“凌汤圆”所为)。二哥读书聪慧,与父亲兄弟情深,此事对年少的父亲造成很大的心灵创伤,也加深了他对旧政府的痛恨。
四川解放后不到一年,父亲以优等成绩从县高中毕业,为寻找人生出路,在“抗美援朝”热潮感召下,投考川东军区璧山军分区文化干校,参军入伍。此后6年,他从陆军到空军,从连队文化教员,到西南军区空军技术干部,主持完成国民党在川东地区遗留的十几个旧机场的测绘工作,建立起原始资料,因贡献突出,获得军功。
这期间,由于“土改”,奶奶突然离世,让身处革命军队中的父亲遭受情感和理智的巨大冲击。一两年后,老家的伯父一家得到安置,父亲才慢慢从情绪低谷走出来。不过,这更加重了他含蓄、隐忍的性格特征。我从没听他亲口谈过老家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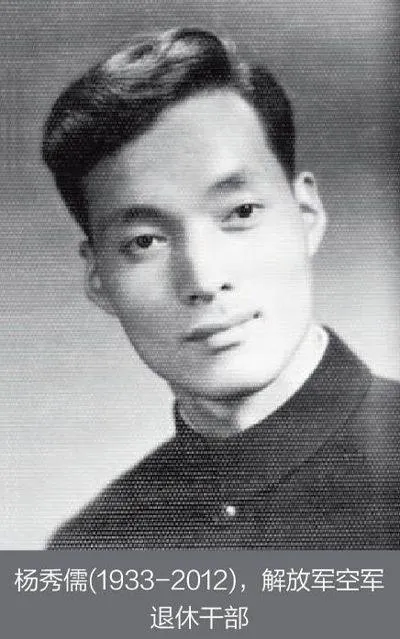
1956年后,父亲从西南到武汉军区空军机关。1957年,他投考湖南大学营建系被录取,用6年时间边工作边上学,往返于武汉长沙,放弃全部节假日和业余文娱生活,以优异成绩毕业。翻看他1960年代的学科笔记,详尽的数理逻辑、数据统计结合钢笔书法之美,我们这些后人无法企及了。
1978年之前,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和部队整编,父亲始终头脑清醒,没有随波逐流,同事和上级不断更迭,而他始终在稳定努力地工作。在那样的年月,他对保持武空机场管理业务的连续性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其走在空军前列。他参与或主持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并将多年的技术突破和成果编写、摄制成两百多万字的专业教材和教学片,在空军推广,成为军校教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政策的调整让年届五旬的父亲走上了技术领导岗位,他结合战备需要,狠抓技术革新,带领基层研发的多项技术成果获空军、全军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为此,他再次获得军功章。
或许是因青少年时期就失去3个至亲,父亲的情绪很少外露,什么事都放在心里。他言语不多,很多时候在沉思。他喜欢山的雄伟和起伏多姿,眷恋土地,关心气候雨水的变化对农民耕种和收成的影响。他还醉心于丰沛的植被,在他管理过的营区,绿化面积能多则多。
父亲还喜欢音乐,感知力天生过人,拉二胡无师自通,1958年,他的二胡独奏被评为空军优秀节目,在首都公演。“文革”期间,父亲很少再拉二胡了。改革开放后,高兴时他也会拉上几曲,母亲觉得二胡曲大多悲凉,他也就渐渐不再操琴了。
父亲有修养、好脾气、心思缜密,我读书时遇到再难解的数理题,他边思考边画图,总能拿出完美答案,教我破题方法。我小时候资讯不发达,上学出门前,他就是最准确的冷暖预报,提醒我增减衣物。武汉冬天湿冷,我爱长冻疮,又疼又痒,父亲会把我的脚放在他怀里,用他温暖有力的手给我按摩。
武汉的夏天炎热难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没空调,入伏后的酷暑天,室内像桑拿房,和我家一样住顶层的人家搬几张竹床到楼顶去纳凉。那时的天空深邃,繁星点点,父亲教我认识了不少星座——银河系、大熊(北斗)、小熊、巨蟹、织女……父亲说这些是他中学时代在野营训练中学到的自然常识。他回忆自己的高中地理老师可能是地下党员,他入伍参军多少受到这位老师进步思想的影响。
父亲从旧家庭走出,在军队成长,信仰毛泽东思想,就连子女的名字也取“为”、“民”二字。他随和、仁厚,为人处事总为对方考虑。他热衷于为基层官兵解决切实困难。父母都是重庆人,川菜手艺上乘,节假日总会请回不了家的战士到家里吃饭。1980年代,他还送几十名基层干部到地方高等院校学习专业,取得文凭,让他们终身受益。
离开老家近六十年,他乡音未改,偶尔会冒两句很土很形象的家乡话开开玩笑。有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对四川的百岁老夫妇接受采访,可能是很久没听到父亲说话了,一听那老爷子浓郁、平实的方言,不禁泪流满面,仿佛听到父亲的声音。父亲走了,再也回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