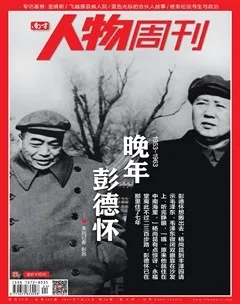歌手Silvi
7月1日凌晨,睡前照例查一下电邮,收到爱沙尼亚朋友的来信:“我记得你曾经采访过我们国家的歌手Silvi Vrait。她昨天去世了。”震惊到睡意全无,脑子里全是那天傍晚分别后的情景。4月20日的塔林气温还很低,天色渐暗,我隔着Palace Hotel大堂的玻璃窗,看她裹着大衣一个人在街对面站了很久,要等的6路电车还没来。
4月21日就要离开,Silvi是我在爱沙尼亚最后一个采访对象。我关注的是“歌唱革命”(The Singing Revolution),国人大都知道捷克天鹅绒革命,但对同一时间发生在波罗的海三国、同样是非暴力的歌唱革命却了解不多。我给Silvi写邮件,她回信告诉我她的手机号码,但加了一句:手机不太好用,我希望它明天能接听电话。过了几个小时,她又发来一封电邮:我的手机用不了了,也许我该直接去你的酒店?

我们最终在Palace Hotel大堂见面,我提前5分钟到,她已经在那儿了,窝在最边上的椅子里,看着有点憔悴。我们点了橙汁,年轻的服务员没认出这位曾经非常著名的歌手(Silvi走后,她才反应过来:“原来是她!我说怎么看着有点面熟!”)。Silvi从1972年开始唱歌,那会儿还是苏联,她去集体农庄唱丰收,也去club唱爵士,“当时的club和现在的night club(夜店)没有一点关系,更像是一个文化活动站。”Silvi跟我解释,她大概忘了我也来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都记得工人俱乐部。
她们唱得最多的是爱沙尼亚语和英语,有时一些干部会到俱乐部来,要求她们多唱苏联歌曲,“但基本上,我们想唱什么都行。当然,俄罗斯甚至苏联歌曲里也有一些旋律很好的。”这正是爱沙尼亚让人着迷的地方:用音乐保存着自己的民族认同,即便唱的是苏联歌曲。从1987年开始,爱沙尼亚人以歌唱传统带动抗议运动,最终赢得国家的独立,“我没有参与保卫电视塔的行动,也没有在地下室私藏爱沙尼亚国旗(苏联时代被禁止),”Silvi说,“但当你有机会在自己的人民面前唱爱国歌曲,你一定会这么做的。你以身为爱沙尼亚人自豪,那是非常动情的时刻。”
“现在一些人不再考虑自豪的问题,他们正在离开这个国家。”她对我感叹,“统计数据说,年轻的女性离开得最多。”尽管爱沙尼亚在前共产主义国家里经济领先,但还是落后于西欧与北欧。“如果我离开了,将靠什么为生?我教过很多年的英语,也许哪里都需要英语老师。”Silvi说她自己也想过离开的问题。一位同事告诉她,毛里求斯非常美丽,你得去那儿看看。这位同事上个冬天不慎在结冰的路上摔倒,去世了,“也许我今年冬天该去那里看看。”
革命以后,Silvi继续唱歌、教英语,有时参加一些表演,也曾短暂参与政治,但坐在市议会(town council)的麦克风前,她说自己“就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她说自己眼下在塔林一个艺术学校教孩子们唱歌,4月30日学校会上演根据《简爱》改编的音乐剧,Silvi在剧中扮演里德夫人,“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女人,是吧?”她笑着说,“但是你有机会和年轻人一起上台演出,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
实际上她过得不好,“曾经的名气不代表任何东西,没人会一直为你付钱。”她说,“有一些音乐会、表演,但他们给得不多,我得开口向他们要。”说到这时她尴尬地笑了笑,“他们给的不常是我期望的数字,但我还过得去,虽然不总是开心,但还过得去。也许我该过得稍微好一点儿,不必为第二天如何挣钱操心,很不幸,我没做到。”
她说她打算今年退休,也许就在4月28日——62岁生日那天。“从那以后我就要靠养老金,我就是一个pensioner了。”她又一次笑了。一周后,4月28日那天,她被送进医院,诊断出脑瘤,再也没有恢复。
Silvi前年写过一本名为saatus的自传,翻译过来就是“命运”,我们聊天时,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you never know。你不知道6路车什么时候才来,你也不知道生活到底会被吹向哪里。分别时Silvi和我拥抱,“Write to me.”她说。22日我回到北京,随后辗转广州、云南,5月上旬再次回京才给她写信,她没有回复。想来那时她已卧病在床,不知意识是否还清醒。“如果我离开了,比如,去了毛里求斯,谁会在那里等我?”我记得采访临近结束,她边说边陷入沉思,“谁会在那里等我?”
Silvi Vrai(1951-2013),毕业于塔尔图大学英国哲学专业,爱沙尼亚最著名的独唱家之一,擅长爵士与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