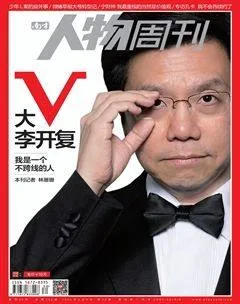后知后觉
有时我特别后知后觉,5月起和尼曼工作人员通了无数邮件,他们所在的Lippmann House也在邮件里出现过无数次,我从来没仔细看过那个词,大概潜意识觉得,反正也是我搞不懂的老外人名。来美国后,某天打量了一番Lippmann,突然脑子里“叮”的一声,我就像烤熟的面包一样弹起:这不是李普曼吗?后来才知道,75年前,正是这位20世纪美国最著名的记者的建议,哈佛才创立尼曼学者项目,“旨在提高美国新闻业的水平”。
报到之前的某天,去李普曼house打印资料,推门进去看到一个有点面熟的大叔——之前我研究过其余23位同学的照片和简介,便主动打招呼:“你是Greg吗?”彼此寒暄几句后就各忙各的去了。当晚躺在沙发上看书,又不知为什么掏出手机,登陆尼曼官网,看到Greg的简介上写着,《The Bang Bang Club》一书的联合作者。嗯?之前好像没看到这个?等等,这书名怎么也有点面熟?Google之,这回是“哐”的一声,直接把我砸回两年多前的一个傍晚。
那天已近黄昏,我在家里无所事事地上网——有一回跟一群不用朝九晚五的写字朋友聊天,说到最不喜欢一天中的哪个时分,大多数人都投了傍晚——设想你从一个迟到的夏日午睡中醒来,天色已晚,广场上大妈们热烈起舞,楼下的烧烤摊熙熙攘攘,你却四顾茫然,而这一天就要结束,是否也会“细思恐极”?
彼时我刚从埃及的广场回到中国的厨房,满脑子是开罗披萨饼——这是跟《纽约客》驻中东记者W聊了一个下午后的结果,她提醒我,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在某个地方重建开罗,结果它的历史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如披萨饼般摊开来。我从科普特开罗走到伊斯兰开罗,从“尼罗河畔的巴黎”来到纳赛尔城,又从穆巴拉克时期的“嘈杂和混乱之地”来到革命当中的“解放广场共和国”,满心欢喜,自以为从这只披萨饼上看见了历史。
那个傍晚我在网上撞见一部叫“The Bang Bang Club”的新电影,4个战地摄影记者的真实故事。从1990年废除种族隔离到1994年首次全民普选,是南非民主转型最为重要的4年,期间流血冲突不断,他们在枪声中穿梭,发出一张张珍贵的现场照片,而自己也在职业的痛感里挣扎。1994年4月,在拍摄又一次冲突时,Ken中弹身亡。3个月后,Kevin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纽约时报》刊发的女孩与秃鹫的照片及其引发的巨大争议,Kevin正是那位拍摄者。此后若干年,Greg和Silva继续行走在战乱地区,南苏丹、喀麦隆、巴尔干、索马里、阿富汗……2010年,在坎大哈,Silva踩到地雷,失去了双腿,比较起来,Greg是幸运的,但我一直没有问他,经历了那么多,你怎么理解人性?怎么理解道德?我猜想也许他仍在为此探索,有一天orientation(熟悉、适应校园的课程)时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正研究一门探讨“人为什么作恶”的伦理课。
如今Greg早已不做战地记者,他现在是南非一家线上日报的副主编,正写一本关于去年南非马里卡纳屠杀(南非警察向罢工的金矿工人开枪,震惊全国)的书。在李普曼的时代,新闻业一步步走向光荣与梦想的顶峰,而在我们这届尼曼学者抵达校园前,最大的业界新闻是《华盛顿邮报》被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以2.5亿美元的“低价”收购。并非所有人都对传统媒体的黄昏感到忧伤,但你可以闻到这种情绪,一个同学说,他已经厌恶了那种对于自己工作的担心。“我不担心自己丢掉工作,目前我们不愁钱,但我担心这种趋势席卷过来,最终你得裁人、减薪,越来越为钱低头。我懂新闻,不懂商业,现在做新媒体的很多人懂商业却不懂新闻,我希望学一些商业的东西,掌握自己工作的命运。”
W也成了我在尼曼的同学,她带来朋友拍摄埃及革命的纪录片,放映完后众人聊如何报道革命,最后大家都认可这样一种说法:你几乎不可能先知先觉地在革命洪流中看清历史脉络,而只能在随波逐流中,尽你所能采访你遇到的人,逐渐加深自己的理解。我有时觉得,也许对于绝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新闻业的革命也是如此,你只能做好手头的事,然后和大家一起等待,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