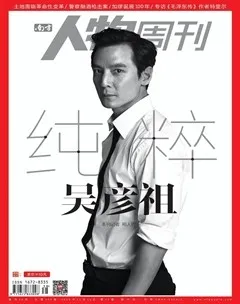桥

河北、河南;塞族,阿族;塞尔维亚科索沃自治区,科索沃共和国……这些在现实中强烈对立的名词,都被米特罗维察一座无辜大桥分割成触手可及又沟通无望的两极。这座桥矗立于流淌过米特罗维察的伊巴尔河上,南岸的阿族与北岸的塞族怒目而视。
19岁的普利什蒂纳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学生Feniks,在城南车站接上我后,走了大概十分钟,就来到大桥南侧的咖啡馆。复杂的出身和迁徙轨迹,让他颇适合这个特殊地区的国际关系专业。他父亲是科索沃阿族人,母亲是犹太人,和同样“祖籍”、来自前南斯拉夫的混血球星伊布拉希莫维奇一样,Feniks生在瑞典,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丰富的经历和文化血统,让他在18岁入学后,就创办起自己的NGO,负责米特罗维察南部阿族青年的能力建设和潜能开发。首都普利什蒂纳距离米特罗维察仅40分钟车程,3欧元的便宜往返车票,让他能同时兼顾学习和工作。
即便有完整的国际视野和开放的人生态度,Feniks也绝不愿意踏过面前那座奇特的桥。不清楚是否一半的阿族血统影响着他对河那边的态度,Feniks坚持认为他们阿族人是友好和爱好和平的,“塞族人想到我们南边来喝酒甚至泡妞,一点问题都没有;可如果我们踏入他们那边半步,轻则被给难看脸色,重则危及生命。”
不过,Feniks坚信,我一个人过桥毫无问题,因此我也就放心大胆地向桥边走去。南侧桥墩那儿,有意大利维和部队的野战帐篷,旁边的墙上,涂鸦着以F开头的最著名英文脏字;北侧同样位置飘扬着塞尔维亚国旗,墙上回敬着另一句英文“NATO,Go Home(北约滚蛋)”。
如若离开标识民族身份的国旗和字母,北岸的建筑和街道与南岸基本无异,都由曾经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子规划出来。星期天清晨,有居民爬上山顶那座新的东正教堂去做礼拜,有的开始到菜市采购,更多的则以最慢的节奏叹着咖啡,日复一日地暂时冷却愤怒。河边大理石纪念碑上刻满了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遇难的塞族军民的姓名和生卒之年,碑顶的圣天使光环已经淡去。
两岸少年们至少还有足球和摇滚两门共同语言,但是,在高度警戒和对抗意识下,前者很容易成为更对立的战斗语言。
如今,整个巴尔干地区最大牌的明星,自然是人见人爱的德约科维奇。即便恐塞的科索沃阿族人,也急不可耐地声称对小德的“主权”。我先是从南岸人口中听说,“小德是我们米特罗维察人”,几天后,又从黑山人口中听到,“他是我们黑山人。”可网球迷们知道,这个出生于贝尔格莱德的明星,早已成为一个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他的故乡确实是米特罗维察,但成长与成名却与这块冲突之地毫无关系。


摇滚倒是试图以荷尔蒙去弥补深深的南北沟壑。米特罗维察摇滚学校,类似北京的迷笛现代音乐学校,有着组队4大件(电吉他、贝斯、键盘、架子鼓)的培训课程,以及录音工程、乐队经纪和专辑促销等唱片产业一条龙教学服务。学校也分为南北两个分支,在其官网首页清晰显示着办学宗旨:重新带回被族群割裂所断代的摇滚文化,努力复兴青年文化,让经验丰富的当地音乐家培养出未来享誉全欧的摇滚明星。每年夏天,两校共24名师生和协调人,去往马其顿首都斯科普里,进行为期一周的进阶培训和乐队磨合,学员们可以就地找人自组乐队,为夏令营最后一天的城市公园演出进行排练。
然而,这儿毕竟不是中立的发达地区,摇滚作为直抒年轻胸臆的介质,难以走出高呼和平主张的Beyond和蝎子乐队。我走向距北侧桥边不远的Dolce Vita(甜蜜的生活),在这家可以放肆抽烟的咖啡厅里,轰鸣着塞语说唱。
“这是什么歌?”我问。
“骂对面人的。”咖啡厅伙计用简单的英语描述。
一辆老款奔驰霸道地在不准调头的广场标志处玩了个漂移,广场一角的公寓楼面,挂着一大面塞尔维亚国旗,上面写有英文“This is Serbia(这里是塞尔维亚)”,下面涂鸦着双头鹰和抗议的黑色群众,以及“在这里你无法回头”。
“出入境”注意事项:对持全球有效申根签证的护照所有者,科索沃都实行90天免签政策。但由于其独立性不被全球各国完全承认,尤其塞尔维亚坚持其是自己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若试图从科索沃向北进入塞尔维亚,即便有塞尔维亚签证,也绝不可行;若往相反方向,除非你以后不想再去塞尔维亚,那么进入科索沃没问题(你将没有塞尔维亚离境章)。解决办法是,从科索沃通过马其顿或黑山两国,中转进入塞尔维亚。
关于旅行安全:当地人非常友好,但若赶上游行示威,尽量别去凑热闹。实时政局描述和安全警告,请参看英国外交与邦联事务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