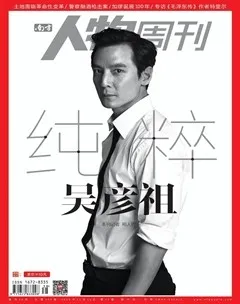来信
“文革”的基因还在
陈小鲁,陈毅元帅的三公子,他的叱咤风云,是在四十多年前。“文革”、红卫兵、联动、西纠、文攻武卫,几乎都和他的名字以及他的同时代人有关,他也是红二代一个历史记忆和符号。
他选择在年近七旬,开始为四十多年前的“罪与罚”道歉, 并不是所有红二代都愿意这样“低下高贵的头”,陈小鲁算是其中最具有真诚和勇气的人。
红二代的身上有着时代深刻的烙印,他们和一般泛指的官二代,在本质上还是有明显区别,他们有使命感,痛恨权力腐败,因贪渎或其他原因锒铛入狱的似乎还不多。
陈小鲁的访谈中,直言不讳贯穿始终,他谈宪法、公民,忧心跃然纸上。他说,“文革”的基因还在。这句话让我震撼。
这句话,不知道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隐约感觉,另一批“两头尖”已应运而生。
《红二代陈小鲁》
他们是红二代,在政治上曾经炙手可热,如今一声道歉仍能掀起波澜。“文革”与他们的父辈和自己都有太多的瓜葛,以至于多年以后仍如此郑重其事。此时道歉也许正是红二代对数十年前的自己的一个隔空回应,一种以身自鉴。
《建邺城里“建业”事》
为何不符合相关程序、动辄数十亿的工程项目能屡屡“闯关”上马?在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今天,造城往往与政绩挂钩,地方父母官为官一任则造城一方,而其 “官帽”也常能盖过民意,压住争议,因而制造出更多的造城市长。
《何怀宏 寻求极端之间的中道与厚道》
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现代人,在享受着丰富物质生活的同时又常感到心灵空虚。如今,旧的传统道德文化秩序被打破,但新的道德文化秩序还没有真正被建立起来。而何怀宏教授重建道德基础的药方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一种道德重建,也是其背后的制度重建和社会重建。
《保罗·乔尔达诺 一个物理博士的文学旅程》
真心佩服保罗的编辑,把书名《In and out of the water》改成了《质数的孤独》,把数学文艺化成这般——“质数是多疑而又孤独的数字”。一个才华横溢的科学家,用自己特有的敏锐嗅觉去感受孤独、体验战争,带着他的读者一起逃离现实,在他构建的文学世界里尽情奔跑。
《京城最贵烂尾楼背后故事》
风水界总是会与房地产业联系起来。在长安8号数次更换开发商,预购豪宅的业主们维权未果后,业主们继而转向风水大师寻求惟一的精神慰藉。房地产大亨与宏观市场、政府政策之间的战争却也波及到了普通的购房者。而如何通过相关的合法制度途径保护业主们的利益,而不是只能依靠风水大师,这是我们还需要思考的问题。
《猝不及防的真实》
我承认,在泛娱乐化的年代,我已经习惯麻木。但在某些瞬间,又会被结结实实地打动。那天,央视播出洋河股份梦之蓝冠名并公益支持的《梦想星搭档》,屏幕上出现阿里地区等待医治的孩子们,这些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安静地坐在床上,眼神干净地望向你——我整个人一下子进入另一种状态,我不好意思说感动,但这猝不及防的真实让我看到了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或者说中国梦的所在。
反思的局限
本刊记者 杜强
陈毅之子陈小鲁为“文革”公开道歉,45年前,他是北京的红卫兵领袖。
在东城区某处深宅大院里,坐在我面前的已经是一位头发半白的老人,精神很好,似乎刚从生活琐事里抽身出来,神情中还带着匆忙劲儿。他总是不等记者问完,就抢过话头发表见解,也许几十年来,疑问与解答已经有了固定的套路,是个人版的“历史问题决议”。
我问陈小鲁,在整体性的政治狂热中,人们应该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力?又感到似乎无法回答——自由是意志无可救药的深渊,不能被体验的历史经验在启发未来方面,几近于巫术。
“在多数场合,我是随波逐流,但也有自觉的成分。毛主席的很多想法,跟我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我也觉得‘反修防修’这个观点对”,“因为我们是他培养出来的嘛。”他回答说。
为什么当时不反思?我感到这样的追问很无聊,所谓意识形态狂热,不正是理智毫无用武之地的困境?局限在特定的极端时空里,人怎么能反思?
“有些领导人子女跑到彭真家去造反,斗彭真,让张洁清阿姨在地下爬。他们都是长辈啊,过去我家和彭真家里的关系挺好的,见面都要叫他们叔叔、阿姨,我就觉得心里非常难受,不理解。”
“‘破四旧’的时候,我也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听人说,在八中附近发现了反动的东西,一看,确实有些国民党时代的委任状之类的东西。当时都说,对阶级敌人要满腔仇恨,但我看到那家里破破烂烂的,人又被打成那个样子,对他就是恨不起来。”
“我在北京站看到一些‘地富反坏右’被遣送回家,很惨啊,被扫地出门,什么也没有了,拉家带口的,回去怎么生活?人皆有恻隐之心,我总是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陈小鲁对“文革”的反感从这几件事情起步。当理智被废黜,足堪凭借的还有良知、情感,以及道德信条。而宣扬“阶级感情”、批判“封建糟粕”,良知、情感以及道德传统是被冲击的最后屏障,一旦突破,文明将无险可守。
听他讲述过去的狂热故事,我几乎变成彻底的悲观主义者——人们习惯了在事后讲述一个自洽的故事,期盼它能够启示未来,所谓“以史为鉴”,可历史好歹也几千年了,总还“鉴”个不够,人祸翻来覆去,有些还似曾相识。历史上已经有太多感慨,人而已,终归没办法。
当谈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陈小鲁说自己身上受的传统教育多一些,大过了革命教育,所以“文革”中“比较清醒”。我问他,怎么看从辛亥以来中国在政治、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他回答说,“左中右永远都有,你把右派消灭光了,左派又分化了,激进分子总是有的。”事实上,我们的对话不时陷入这样的龃龉当中,不能互相理解。
“红二代”陈小鲁的生活异常简朴,他告诉我身上的衣服没有超过100块钱的,没有珠宝古玩,“不怕别人说什么”。我在走廊上发现了他的老年证,因为经常使用,边上已经磨破了。他居住的地方是粟裕大将曾经的居所,院子很大,稍微有些冷清,我禁不住去想:在无人造访的日子里他怎么回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