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老炮都是愉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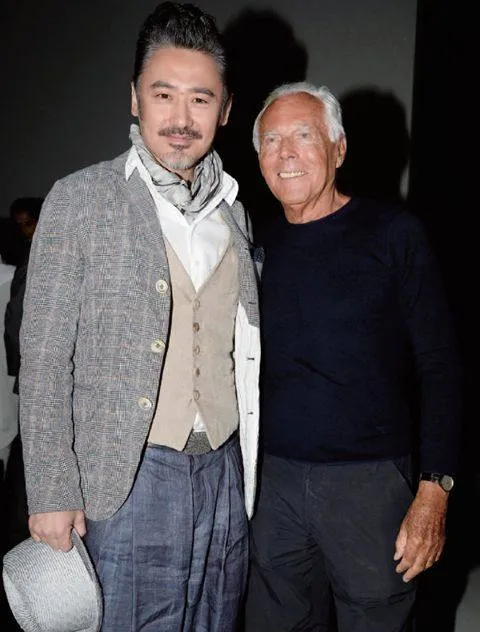
发动机没有了,演戏就是特难为的一件事
人物周刊:今年为什么会尝试接拍农村题材电视剧?
吴秀波:其实这一年啊,我对电视剧和电影的剧本选择,都特别艰难。因为行业发展越来越迅猛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投资方在左右行业的节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公司在做一个剧本,做到一半儿突然发现另外某一个品种或者某一个类别的戏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迅速弃前两个月于不顾,赶紧做出一个剧本就拍。而从业者要想生存,就必须适应这种节奏,不停这么去拍。矬子里面永远有高个,大家就在这种挑选中活着。
你知道你要去应对的,不光是演戏,一定是特别艰难而为之的二度创作。靠什么来引发你二度创作的兴奋点呢?如果故事、题材、人物都没有,我只能找一个它选定的故事环境。我希望这个环境是我所感兴趣的和没有经历过的,我演过所有戏只有一个地儿没去,就是农村。
你问我演戏的动力来源于哪儿,我告诉你是从心里的那一部分去找诉求。那东西如果没有,演戏就是特难为的一件事儿,有了以后,这件事儿一点都不难为,对我来说,无非是你喊完开始以后,我活着。
那个动力是生命最初的缘分,就像父母结婚一样。那个东西要没有,我从哪儿来呢?我在戏里就没法活了。它就是我的发动机。
人物周刊:发动机是你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如何解释?
吴秀波:发动机这个词,我所指的并不是你为了生活背水一战。如果把这个动力叫作发动机的话,就没有真正理解发动机在这个行业的意义。任何人都需要工作,都需要收入,为了工作和收入去努力从事一个行业,这个责无旁贷。但这并不是发动机。我所说的发动机,特指当你和戏剧本身达到了某种共振频率时产生的那种激动感。简单说,如果你拥有跟角色同样的态度,可能就有了这个发动机;你拥有这个跟你生活中几乎等同的世界,你可能就拥有了这个发动机;你拥有了你梦寐以求的爱情,你可能拥有了这个发动机;你拥有和角色共同的愤世嫉俗的态度,你可能拥有了这个发动机。

人物周刊:那个环境最终实现了你当初内心的预期吗?
吴秀波:我最初体会这个戏的环境就是我们到了真正的乡下,我几乎没有特别认真地在这种地方生存过。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一开始有很多的不适感。你每天回一趟住的屋子就要走好远,还要爬山,在这边看不到一家星巴克,没有任何城里的东西。但过不了多久你会发现它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每天出门不用想穿什么,穿个大裤衩大背心和一身运动服都行。这和你在城市里恨不得武装到牙齿、西服衬衫领带是不一样的。第二就是你心里只专注两件事:演戏和休息,变得特别简单。随之而来,你看到剧本上以前认为特别简单的功能变得非常有意义。当戏里有人要把村口那棵树拔走,你会泪流不止。因为那对你已经不是一棵树了,它意味着生存环境的标志,意味着生命里的一个图腾,意味着你的一个意义。你会从特简单的戏剧里想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你开始适应这个环境,开始适应进入这个环境里的人,你会发现,其实大家是等值的。你会去捍卫那个曾经你觉得特无聊的一件事情,这是我选择这个戏所获得的最大的快乐。
跷跷板永远不知道天平的乐趣
人物周刊:所以你的发动机,不光是心境,还有环境?
吴秀波:心境和环境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词。我们常说这个人心境不错,导致他进入这个环境给大家带来的影响会好些。还有另外一种,从唯心角度讲,如果我一直拥有这样的心境,就可以改变环境。演员之所以能够进入别人心境、迅速转换情绪,就是入境。他能在任何环境下让自己融入,体会出异心。演戏就是如此,所以说演戏像修行。什么是强大?就是永远能让自己心境好。在每时每刻,越来越好,你就是最强大的。
人物周刊:面对不够好的外部环境,怎样实现好心境?
吴秀波:大凡人的心态都是跷跷板,都在一个支点的两端,那两端是我们知道的所有对立。如果这是好,那就是坏;这是高,那就是低;这是对,那就是错……人们不停在这儿翘来翘去,然后不停地找自己要翘起来的那端,所以跷跷板永远不知道天平的乐趣,也不知道天平的智慧。
在早期我觉得,剧本是最重要的,在改变不了剧本的情况下,这场戏就是不能拍。但是那只是你站在一个所谓看得见未来的长时段里对胜利的假想,我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办?你首先应该想到自己是演员,要遵从所有剧本占有的立场和方法。你首先要进入这个环境来创作,其次还能不能找到你的发动机,一旦找到了,再烂的剧本也会是一粒好种子。你一个人这样,就可以影响到另外一个人;两个人,就可能影响到4个人;4个人,就可能影响到全组。这才是真正的创作。
创作是从态度上开始的,而不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句台词。真正的创作者要从态度上进入一种创作状态,这才是真正的老炮。所以你看,真正的老炮都是愉悦的,愁眉苦脸、愤世嫉俗的人不能说他不是天才,但他一定不是老炮。
10年变化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出道10年的老炮,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吴秀波:我从一个毫无名气甚至于生活都很窘迫、工作都没有着落的演员,变成了现在这个工作上可能算是有所成就和被人熟知的演员。我对自己工作上的认知,从毫无办法、愤世嫉俗变得随顺和职业。还有就是,我从一个孩子变成了父亲。
但在进青岛剧组那个化妆间的一瞬间,我知道,其实是没有任何变化的。特别巧,我这次拍《槐树花开》,剧组驻地就是10年前拍戏的地方。我一进那个化妆间,就知道所有变化只不过是你心里所产生的对比感受到的变化,或者说,这个世界需要这些刻度来与别人交流。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需要这种刻度。但我心里知道,没有时间上的变化,没有质量上的变化,没有任何差异上的变化。你以为自己是个跷跷板,其实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一个恒久不动的天平。
人物周刊:但是你毕竟撬动了你所在行业的一部分。
吴秀波:因为最开始做这行的时候,你自己本身还不够完善,对于整个行业和你所从事的工作本身,没有太多的安全感,你自己还在一个摸索和毫无经验的状态里。那个时候你能付出的可能是天性里你适宜做这个行业的基因,可能还有你的吃苦耐劳。但不管怎么样,你要让用你的人占到便宜。无论从工时、工作状态还是你最终呈现的表演,你都要完成这个。随着你越来越有名,大家对你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其实你要做的依旧是这个工作,你是否还能让人家占到便宜?这就变得尤其难。要做到这一步,不单单要从作品上,你可能要从更多的方面,态度、与人交往、对于整个行业的认知,你都要比以前更知道如何识大体。我以前干过无数次不识大体的事儿。
人物周刊:比如呢?
吴秀波:比如在创作上的专横和跋扈,在艺术见解上自以为是,在捍卫自我利益上不冷静和冲动。我原来做过制片公司的监制,尤其对编剧会特别不客气。我会特别放肆和强硬地告诉他,哪场戏你写得不对。一方面是当时自己自负,另一方面也是无知。到现在慢慢才知道,这行业不是每个人都是天才,我也绝对不是。每个人所站的立场和最终所书写的笔触,都有他的缘由和道理。也许是他做得很完善而你根本看不懂;也许他做得不完善,但你有责任用平缓的语气和他交流找出解决的办法。以前我做演员,态度都是我要怎么怎么样,接下来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我要怎么怎么样,而且你还必须怎么怎么样。(笑)现在我学会了,您要怎么样,我就可以怎么样。这是我在表演过程中的一个转换。
还有就是,可能因为以前生活窘迫吧,我非常捍卫自己的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人能给你,有人不能,有人答应了给你却没给,你会觉得有不甘和愤怒。但现在想想,其实每个人都给了你工作的机会,都是应该感恩的。我觉得,知足、本分、尽职、识大体,是老炮必须拥有的素质。
人物周刊:圆润之后,棱角不在了,这怎么平衡?
吴秀波:我不认为棱角是把事情解决和达到某种层次的最好方法或状态。相反,真正能到达那种状态的,一定是水,绝不是一个枝枝杈杈的固体。一定是水到渠才成。
在这个圈子待久了就会发现,你身边的每个人都是聪明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观点和生存方法。所以,学会尊重,才会成功。这一点让我特别受益。
我从尊重这个词里受到的收获和福报最大,我今天得来的所有一切,全都受这个词的福报。我所有的表演动机与来源,来源于角色对他周边人的尊重;我整个表演的情绪,来源于角色对戏剧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尊重;我所有台词的语气,来源于人的自我情感和自由的尊重;我所处的工作环境给我带来的收益和别人对我的认同,来源于我对他们的尊重。我拥有很多喜欢我的观众和影迷,也来源于我角色表达的尊重和我对他们的尊重。这些就像我突然间看到农民是那么尊重土地,而土地给他们的回报是如此的丰厚。你花重金买了一个金碗或者玉碗,摆在这儿拍卖可能值几千万。当你没饭吃的时候,你让它给你变出碗饭来,事实它不会变出一粒米。但是牛踏马踩、遍是粪汁的一块土地,看起来平凡而不堪,但只要你守着它,年年春种秋收,养你生生世世祖祖辈辈。这才是大自然的精神,就是我们每个人活着的状态,我们根本是一体的。你见过独立的人吗?他独立,离地10米我瞧瞧(笑)。没有真正独立的生命,人也一样,鱼和树也一样。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再坐回那间化妆的屋子,我就知道,其实我没有一点点变化,所有的变化都只是我们想象的变化。

惟真致上
人物周刊:你为什么这样强调表演状态里求真?
吴秀波:我觉得抛开所有的技巧,最重要的是创作态度。在我看来,最本真的创作态度就像一粒种子在一个土壤里生长一样,这就是表演的状态,真实地把自己放在生长环境里,汲取那个环境里的营养,然后肆意生长。
情感的传递是极为细腻和神奇的事儿。很多时候,你听一个人的访谈或者去看死刑犯最后的留言,在他克制和语言停顿的一瞬间,他脸上几乎毫无表情,那个画面没有任何动的地方,但是你能够感受到频率的共振。在这个行当里,惟真致上。它其实就是一个游戏,我们首先要信以为真,要有所感触,要打动自我。要以为那是一段生活,作为创作者才不虚此行,才有可能打动观众。
人物周刊:在打通和每个角色融为一体的求真路上,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吴秀波:演员最难跨越的,也是他最需要保有和最难坚持的,是变化。特早以前我开始琢磨演戏的时候,我的认知是,要有所变化必须是新的变化。感受态度产生变化再表达才可能产生节奏上的变化,这也就是我们有句老话叫相由心生,演员要在短短3个月的创作时间内完成。每个人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和说话拥有的这个语气,绝不是巧合,这是他生命中种种缘分造成的。生命的状态其实就像我们用两只手紧紧扒住悬崖的两侧,不让自己掉下去,这是固有状态。但是在演戏的时候,你需要把两手松开,并且一定要以为自己还能飞翔,这就是每个演员不停在完成的功课,叫解放天性。人的天性在出生后就不停被禁锢,被套上枷锁,这是不争的事实,直至死亡的一刻才会解放回来,所以演员永远在做这个游戏,尝试解放自己被禁锢的天性。你在戏中看到的他熟练也好不熟练也好,你觉得那是好的也好不好也好,与其他戏的与众不同,都是他在努力解放天性的结果。
我相信每一本翻译过来的著作都会有误读,在传教的过程中孰轻孰重可能教授者每一个人的理解也不同,再加上嘈杂的课堂和年轻的心性所导致的接受程度也迥然不同,所以我觉得真正看懂斯坦尼斯拉夫表演体系的人恐怕不多。我们知道表演课有几个大的题目,注意力集中、解放天性、真听真看真感受,我相信释迦牟尼坐在菩提树下所依据的原则也是这些,没有分别。表演也是需要放下我执的,因为你要放不下自我就等于无法解放天性,无法变换角色,所以一个真正做过演员的人,或者知道怎么做演员的人,永远不会说我会做演员了,他会知道每一场戏都是一次新的修行,做得到做不到还得看那一瞬间,你是否能放得下,是否能再一次入境。
放手就不焦虑
人物周刊:10年前就有导演说你会成名,但是直到3年前这一天才到来。圈子里也有很多优秀演员,至今无名,你怎么看?
吴秀波:我演戏最初大部分的需求只源于一个,就是家庭生活来源需求。达到了这一目的,几乎达到了我全部目的。除此以外,其他目的至少在我这儿并不重要。从艺这么长时间,如果我把任何一个导演对我说的类似的话放在心上,我都走不到现在。记住一个就走不到现在,记住3个绝对是现在什么结果都没有,想都不用想。(笑)
我现在所谓的成功,也只是在采访者眼中的采访标题而已。在这个世俗的成功里有无数的对比,很难定义。第二,在我心里如果说我演戏成功了,我就是个骗子。我至今仍然认为我是刚刚明白演戏而不足道的人,也许能做到一场、两场、30场、50场戏很精彩,做到一部戏的百分之五或者百分之十乃至百分之二十就已经很不错了,但完完全全在一整出戏里活在那个戏剧世界里,这依旧是一句梦话。
人永远是焦虑的,这种焦虑来源于需求、欲望和不舍,这就像演戏就是活着的道理一样。放手就不焦虑,但是谁能放手呢?这是用3分钟就能说明白的一个道理,但是全人类的进化史都没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说更快更高更强,那么后边呢?还是更快更高更强。再后边呢?还是更快更高更强。所以要解决看似外界引起焦虑的原因,其实是解决自己能够产生焦虑的内心。我一生中的敌人,也是自己,我用一生的时间与之争斗。
儿子是一生的圆满
人物周刊:家人跟你谈过你这些年的变化吗?
吴秀波:他们看见我的变化就是从一个平常人变得不平常,然后又变回平常人的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会更加拉近距离。如果我们今天依旧聊着午餐和晚餐,恐怕你就不满足于这次采访,因为你需要和上次采访不同,需要有所理解。但其实也许我们过5年再做采访,聊的可能是家长里短,也是一种递进。转了这么大一圈,我们聊聊怎么把馒头蒸好,把这个菜炒好,才是人生最本质的事。
其实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一种环顾四周的无暇自顾而已,直到有一天还是那个大腹便便居家自作的平常人嘛。所以能放下分别程度越大那个人,入境越稳。这事对于演戏来讲,确实可能是一种财富。演戏只要一搭手,喊完开始,就能知道对面的人放下了什么,这个并不因为片酬的高低和演员的大小来决定。
以前,我能够关心的就是我车前后左右轮胎怎么了,坏了的水管子应该怎么修,然后慢慢去想剧本应该怎么修,角色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怎么去参加这个活动,这次穿什么衣服,然后慢慢再回到儿子上学要不要戴口罩,他得的感冒会不会转成肺炎,(笑)人生不过如此而已。
人物周刊:你曾经跟我说,儿子是你一生的圆满。
吴秀波:我至今也这样认为。儿子依然是我一生的圆满,也许我这一生都找不到最终和可捍卫的信仰,可能最后会在他的身上,这是一个正常人最正常不过的可能性。对于孩子来说,只要他们不做坏人,不以不尊重别人的方式去掠夺别人,不管他是富有还是乞讨,他们都是我一生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