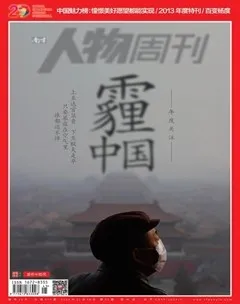寻找啤酒的味道

我是一个自觉无趣,且生硬的人。有一次,一位女性采访对象被我激怒了,她掌管着一家几十人的投资公司。她猛地站起来,转身离开。我大声说:“你不能走,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还有一次,一位男性采访对象也被我激怒了,他掌管着一家数百人的互联网公司。他叹了一口气,严厉地对我说:“燕青,我是一个喜欢掌握主动权的人,你要跟着我的思路走。”我什么都没说,继续按照我的思路从他那儿问出了我要的东西。
我又是一个商业记者。在别人看来,我有可能更无趣。我曾执迷于研究各种数据,它们让我更接近商业的本质;我也曾执迷于只相信我所见的,它们让我更接近事情的真相。
去年下半年,金志国,一个创造了青岛啤酒增长奇迹的知名企业家突然辞职了。我很兴奋,这其中包含太多可琢磨的细节了。我花了一天一夜梳理其中的脉络、逻辑,然后马不停蹄地连续采访,终于在当期赶上了这个新闻热点。这个选题的处理,没有超出我的经验。那时,我刚到《南方人物周刊》不到半年。我沾沾自喜于这个平台超强的影响力。因为文章发表后,我接到了青岛啤酒、青岛啤酒的竞争对手,甚至白酒酒商的各种反馈电话,他们对文章观点的认同,让我觉得这应该能算是一篇“不糟糕”的报道了。
“太糟糕了!”杨子老师的话让我真想在评刊会上找个地洞钻进去,“我没有闻到啤酒的味道!”他和我的编辑提醒了我,商业报道的意义,不是数据,不是事件,不是行为,而是这些数据、事件、行为背后存在的,人性中让人产生同理心的部分。
“啤酒的味道”贯穿了我的整个2013年。这一年,我努力让我和我的采访对象都变得有趣。
牢里的牟其中绝对不再是一个有趣的人了。我和夏宗伟,他的红颜知己,一起搭夜车去武汉采访。在去的路上,我们都有感冒的迹象。她立刻买了感冒药和板蓝根,嘱咐我要扼制感冒的势头。我们在板蓝根的微苦微甜中聊起她的命运:她和姐姐们的恩怨情仇,她和牟其中的剪不断理还乱,她和这个社会的冲突,她的困惑和她的感情故事。采访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又连夜搭车赶回北京。我们在火车站待了8个多小时,我似乎忘了我们的关系。面对她情感上的一些困惑,我给出了我的建议。我很揪心她遭遇的不寻常。她说,“这些你都不要写出来。”这些成不了文的内容,让我更加理解了牟其中的种种切切,也比别的记者更接近他内心的可能性。当编辑把标题改为“活着”时,我想,它就是这样子的。
汪小菲是一个有趣的性情中人。我站在空旷的马场采访他。摄影师抓拍了现场。汪的助理看着我们的照片说,绯闻就是这样产生的。约访汪小菲,源于我想看到各种绯闻背后那个真实的他。去年7月,我给他发了第一条短信。他主动给我回了电话。去年12月,张兰国籍事件沸沸扬扬,我再次给他发短信说想聊聊他的母亲。他是一个不会用场面话跟媒体打交道的人。他没有向外界打开自己。今年4月,海天盛宴的谣言触碰了他的底线。我跟他说:“我不关心这些谣言和八卦,但我很在意他们将你归为明星一类。”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茶品牌。我试着去理解他,我们都是80后,有共通的地方。后来,采访很顺利。再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自信的汪小菲。
王石是一个天生自信的人。他在拍摄空隙自顾自地走来走去,无视周围的一切。我问他:“你的胡子是不是特意打理成这样子的?”他大概觉得这个问题很无趣。其实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有人特意打理你的形象?”那时,他和田朴珺的关系扑朔迷离。田朴珺也不愿回答。田的采访结束后,我们一起吃拉面。那天下午,她接了好几个电话。她对着话筒柔声细语地说:“你的声音听起来很疲倦,要好好休息,我嘱咐XX买VC泡腾片给你吃。”XX竟然跟王石的助理同名。
陈九霖大概是一个只相信自己的人。他的内心有一根绷紧了的细钢丝,时刻提醒他要谨慎。在采访完他的合作伙伴、同窗、同事、挚友后,我问他:“做了这么多,你到底想做什么?”我用了这种直白的方式,因为他能应付所有的方式。“别人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你还不知道吗?”他默认了我对“他”的判断。
对采访对象做出一个接近他本真的判断,是一种考验,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我想做一个有趣的人。”2013年,我的最后一个采访对象王江对我说。他说这是对自己更高的人性上的要求, “有趣的人首先是会讲笑话的人。”
那么,我们来讲一个笑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