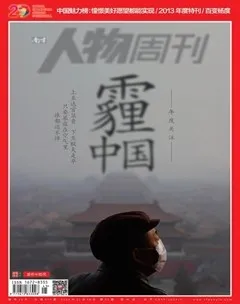原始尖叫

晚上收到错误情报,走到Harvard Yard时发现哈佛先生铜像前一片漆黑,连个鬼影都没有,偶有人经过,都把头缩在高高的领子里。这一天寒流来袭,气温降到零下3度。
到附近24小时开放的本科生图书馆避寒看书,一派期末备考的气氛,有人桌上的书可以砌墙了,还有两个哈佛学生心理健康协会(SMHL)的女生挨个派发巧克力和小纸条,上面印着励志作家H. Jackson Brown的话:“Think big thoughts, but relish small pleasures(雄心勃勃,不忘享受微小欢愉)”,底下两行加感叹号的大字:别放弃!你很棒!11点多,眼前突然走过一个只穿红内裤的男生,特别自然地穿过人群,戴上耳机坐下自习。临近午夜,图书馆门口有点躁动,我对面的哥们站起来宽衣解带,也是脱到只剩底裤,穿上靴子,披着貂就出去了。
跟着人群往外走,没两步已听到Yard那边低沉的嘶吼,到铜像前,发现鼓乐队已经就位,草坪对面一栋教学楼下,几百裸男裸女挤在一起,像刚从冰窟窿38d7a3c061b5ee2da4132b8ae1cfd0e629a63658e2f72e46e6964234636d12a7里捞出来活蹦乱跳散发着热气的鱼,在唱《我们是冠军》呢。唱了一会儿改喊USA,午夜钟声一响,就尖叫着欢快地潮水般向前涌动,把旁边举着手机的一群亚洲面孔冲得七零八落,这就是哈佛著名的Primal Scream(原始尖叫)了。
1960年代,这仪式的确以尖叫为主,每学期期末考试之前的一周,学生会打开所有宿舍的窗户,集体咆哮10分钟。1990年代左右,尖叫演变成了裸奔,但目的是一致的:减压。一个学生曾在报上描述自己的体验:“我看到象征着这个国家学术尊严和光荣时代的Yard被1000个光屁股填满。经过那些寒冷、尴尬、悲惨但很爽的瞬间,对期末考试的焦虑被抛到了几光年之外……”不知道那个几天后搞出诈弹风波想取消期末考试的韩裔学生有没有去尖叫,收没收到小纸条,无论如何,他也算是think big了。
尖叫前一周,课程陆续结束,每堂课的末尾都照例是学生鼓掌感谢老师,我想普鸣(Michael Puett)教授的最后一课一定比较壮观:七百多个学生齐刷刷鼓掌。他教授的《中国古典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这学期第三受欢迎的大课,选修人数仅次于《经济学入门》和《计算机科学入门》。《大西洋月刊》为此写了一篇长文,探讨为何这么多哈佛学生想要学习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智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大脑依逻辑地做出各种决定,但在中文里,表示‘mind’和‘heart’的是同一个词语:心灵……庄子教导人们,应在日常生活中道法‘自然’,而非受困于各种理性抉择。”读到这段我停了一下,想想似乎很久以前自己就已经把mind(头脑)和heart(心灵)区分开来,而今却借助一个西方人,“重新进入中国”;又想起刚来美国那段时间,不断被问到“是不是和中国很不一样”,我每次都老老实实回答:其实没有那么不同。说到底,都是被全球化与现代性冲刷的一拨人,彼此能有多大差别呢?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借学生之口说,这门课可以改变你的一生,“有一点乐观了吧。”去年选过此课的一个本科生微笑着告诉我。她解释说,其实这门课的火爆,有一些与学问无关的原因,比如说这门课不容易挂科,而Ethical Reasoning(伦理分析,哈佛鼓励博雅教育,本科生必须在几个不同大类里修够一定学分,桑德尔之前的《公正》课也属此类)这个大类里可选的课也有限,此外,不论是《公正》课还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哈佛已经成了一种Cult(在特定群体里流行的),一种“正面的peer pressure”,好像你来到哈佛,就应该听一听这样的课,正如你来哈佛,就该尝试一下冰天雪地原始尖叫一样。
Cult也有邪教之意,我也很邪地想到另一件据说在哈佛读书“该做”的事儿:至少在widener图书馆里嘿咻一次。我曾许多次下到像外星球那样巨大荒凉的widener藏书室里,里面陈旧的纸张气味不敢恭维,但曲径通幽的书架的确提供了很好的掩护。某天我很想翻翻东欧知识分子写的书,发现那个区域全是伸缩书架,这意味着当你触动按钮想看看罗马尼亚人作品时,摆放波兰人著作的书架会缓缓合上——希望大家办事都不要来这里,被一堆The Captive Mind(被禁锢的心灵?头脑?中文两个译名都有)夹住,大概是最讽刺的死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