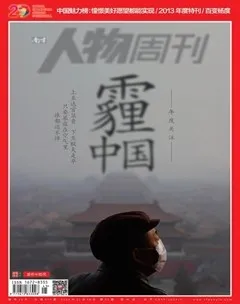陈小鲁 自省之魅

尽管数次对昔日老师表达悔意,67岁的陈小鲁还是决定正式道歉。2013年10月,他组织了一次同学聚会,坦承自己在“文革”中的过错:批斗校领导、组织批斗大会、勒令民主党派解散。作为北京八中学生领袖,他向“文革”遭到冲击的老师,郑重致歉。
陈小鲁是开国元帅陈毅之子,当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他全票当选八中革委会主任。他鼓动造反,燃起的情绪却走向无法控制的深渊。在他组织的一场批斗中,口号很快升级为暴力,他无力阻止,中途离去,最终副校长温寒江被打3小时。暴力持续升级,北京八中党支部书记华锦、教师高家旺自杀身亡,党支部副书记韩玖芳被打致残。华锦被关押期间,陈小鲁派人防止学生半夜揪斗,悲剧却未能避免。
反思是漫长的道路。整体性的政治狂热中,人们应如何运用自己的理智与判断力?陈小鲁出于近乎本能的良知而否定武斗,华锦死后,他和孔丹、秦晓发起“西纠”,维持红卫兵秩序。
1981年,陈小鲁前往英国,任驻英武官助理。学习材料中的雾都伦敦竟是蓝天白云,而在过去描绘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防部长却坐地铁去上班。4年后,他回到中国,在政改研讨小组办公室任职,被视为“红二代中的改革派”。法治观念日益坚固,对“文革”的认识,也从“政治错误”变为“违宪”。
“文革”运动随着“彻底否定”戛然而止。“四人帮”背负了全部罪责,历史没能深入反思便匆匆翻过,人们被号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过去三十多年里,“文革”是难以讨论的话题,然而“文革”的基因从未远去。当怀旧情绪呼唤“文革”卷土重来,陈小鲁一遍遍申明:要接受“文革”教训,要长治久安,最重要的是树立宪法权威。
道歉前一晚,陈小鲁读“五四宪法”,他说自己违反了第8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反躬自问:“没有人强迫我造反,我为什么选择造反?”追问的结果是,“我虽然没打人,但我作为一个学生领袖造反了,破坏了学校秩序,才造成了侵犯人权的事。”进一步说,“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自由他的人身不得侵犯是神圣的,你有义务去保护其他公民,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你放弃了义务你旁观,你就有愧于公民的称号。”
道歉会上,老师们宽容了学生,不愿他们执着于道歉,回忆起“文革”,却依然流露出痛苦。那是一段将被永久铭记的日子,是未曾治愈的集体创伤。
沉默的状态终究有了变化。这一年“道歉”之音频频发出。64岁的宋继超决定向老师道歉,那年揭发“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初中语文老师郭楷时,三条“罪证”脱口而出,这让他愧疚终身;59岁的张红兵致歉母亲,因他的揭发母亲被枪毙,这使他一生背负沉重枷锁;61岁的山东刘伯勤,刊登了一则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公开道歉的还有温庆福、卢嘉善、雷英郎……
陈小鲁先生,作为红二代,以自省的姿态出现,立刻成为关注焦点,“文革”致歉的文化意义和对社会心理的影响得以放大。陈小鲁看重反思,却反感舆论“将道歉者崇高化”,在他看来,自省是为了“灵魂的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