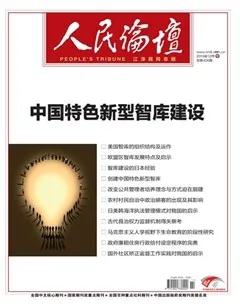彼得斯的道德教育思想:目标、内容与方法
【摘要】彼得斯视道德教育为培养遵循规则的、具有理性道德的个体的过程,认为道德教育的内容就是通过对基础规则的传递使儿童形成对层层递进的原则的认同,在原则的指引下,灵活地运用具体的规则,并把这些原则和规则内化为品格。他在揭示了以往道德教育方式中所存在的矛盾之后,把培养习惯看成是达到理性殿堂的必要途径。
【关键词】彼得斯 道德教育 规则 原则 美德
理查德·斯坦利·彼得斯(R.S.Peters)(1919~2011)是英国著名的教育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他因在教育理论研究中运用哲学的分析方法而成为分析教育哲学流派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之一。彼得斯对道德教育与道德发展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正如凯尔(Carr)和斯蒂特(Steutel)所说的:“在把亚里士多德的美德理论转向道德教育的目标方面所做的努力,也许最有影响的就是彼得斯。”①但是长期以来,彼得斯的道德教育思想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培养能自觉遵循规则的具有理性道德的个体
道德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从事道德教育的理论者和实践者所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经典的亚里士多德理论认为道德教育应着眼于对个体美德的培养,而康德认为培养遵循规则的理性个体则更能体现现代契约社会的现实要求。而要清楚这个问题,显然需要了解社会的需要,这样,道德教育的目标问题就转化为美德与规则在社会中的现实需要问题。
在麦金太尔看来,亚里士多德的美德思想显然没有给予规则以应有的关注,他认为道德哲学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就在于规则应该在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他也指出当代道德哲学对规则的过度关注也反映了启蒙以来的错误转向。麦金太尔认为,在任何社会中,美德都需要规则的补充。对规则的承认和遵循,不仅体现了社会的要求,也是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建立起与他人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
彼得斯基本上认同麦金太尔的观点,而且,他对美德、规则以及它们在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又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彼得斯先是明确了品格的含义,认为“品格与对规则的服从是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②。接着,他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品格的三种意义做了区分。品格在第一种意义上,通常被用来表示一个人的品格特征的总和;品格在第二种意义上常用来指一个人具有某一类型的品格;品格在第三种意义上用来指具有品格的人,他们能不受自己情绪和意向的控制,习惯性地坚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在面临诱惑、恐吓或其他社会压力的情况下也能始终如一。③
彼得斯认为第一种意义上的品格特征“可能仅仅是社会准则在人身上的印记”④,也就是说,这些品格特征由于是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一旦脱离了那种环境,它们就很可能不复存在甚至向坏的方面转化。在第二种意义上的品格可分为自律型的、无目的型的、传统导向型的、他人导向型的品格等多种类型。在第三种意义上来说,“具备品格的人将发展自己服从规则的独特方式”。尽管品格特征是具有品格的人的必要条件,但具有品格的人,……无论他展示了什么特征,都将存在一些他在展示它们的方式上的控制与一致性。⑤
在对品格的意义进行澄清的基础上,彼得斯进一步根据不同的品格特征,对美德进行了分类。他指出,归纳起来,第一类:十分特殊的美德,比如守时、整齐也许还有诚实,它们与特殊类型的行为相联系,缺乏任何固有的、说明以一种既定方式行动的理由,不是动机,不像第二类美德,如同情心,也是行为的动机。第三类:更为人为的美德,如正义和忍耐,其中包含了与权利和制度有关的更普遍的原因。最后,第四类:更高层次的美德,如勇敢、正直、坚持不懈等,它们必须在面临相反倾向时得到运用。⑥
彼得斯认为,第一类美德,是可以被称为习惯的美德类型,它们可能缺乏任何内在固有的按规则方式行事的理由。而第二类美德是一种自然的美德,这些美德(比如同情)的价值就在于它们可以“成为行为的内在动机”⑦,能够唤起人们的感情,激起人们与他人情感的共鸣,这种内在的行为气质使得人们遵循着理性正当原则去行动。第三类美德,就是休谟所说的人为的美德,它们不包含内在的动机,但是因为其包含了与权利和制度有关的更普遍的原因,所以就像原则一样对社会生活的调控是非常重要的。而第四类美德,它们的价值在于能够使得人们在面临相反倾向的时候同样能遵循原则。
根据彼得斯的说法,有品格的人基本上具有坚持、决心、一致和勇气,他把这些品质看成是更高一级的美德,在他看来,诚实、礼貌、热情等,这些都是属于低一级的美德,这些美德更多地诉诸于对规则的遵守,或者追求特定的目标或目的。而更高一级的美德则更多地关注于遵循规则或追求目的的方式:持之以恒地、英勇无畏地、不屈不挠地等等。
应该说,彼得斯对美德的分类应该是“一种系统的、有条理的关于美德的阐述”⑧,但对于彼得斯来说,他所做的这些努力显然是为规则和原则服务的,在他看来,美德发展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们能有助于人们更为理性地遵循规则,这也是他被认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的原因,而且他自己也声称:“我是一个坚定地支持理智地掌握并且明确地运用道德准则的人”⑨。
正因为如此,他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由接受一定规则的个体的人联合起来的整体”,是一个“基础规则的体系”⑩,对基础规则的遵守应该服从更高一级的原则。他对规则与原则做了区分,认为从具体程度方面来说,规则更为具体,而原则更为普遍。“但规则和原则更为重要的不同在于它们在彼得斯所理解的理性道德中所起的作用的不同,即规则是告诉一个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而原则使得一个人能够判断规则是否合理”。对于规则来说,光有理由还不够,它们还必须是好的理由,而原则通过展示是否一定的理由有价值来使得一个人区分出好的理由和坏的理由,原则是“使所考虑之事变得恰当的东西”,“它们规定了什么样的原因可以作为理由”。一个理性的个体,他能够根据更高层次的原则,在变化的环境中对规则做出适当的调整。他说:“为了坚持一个理性的准则,一个人必须服从一些更高层次的原则,这些原则将使他能够根据环境的相应变化明智地运用规则,并且根据环境以及关于规则运用的条件与结果的经验知识的变化,不断地修正规则”。
而原则或规则一旦内化,就会“被个人化为品格特征”,这就意味着规则不再需要外在的力量而能被自觉地遵守,而一旦我们认识到这种内化的因素,那么“社会是一个由接受一定规则的个体的人联合起来的整体”这种说法也就毫不奇怪了。在彼得斯看来,一个自由的社会,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在善的理解方面的一致性,但在实践中却需要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凝结起来的对行为规则的认同和一致。
正是着眼于美德和规则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彼得斯把培养“具有理智的、明智地并且十分自觉地引导自己的人”作为道德教育的首要目标。
对基础规则的传递和对原则的灵活运用
个体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要实现成为理性个体的道德教育目标,道德生活就应该凸显原则的地位,而道德生活又是复杂的,要让儿童进入道德生活,必须首先了解道德生活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是那些十分重要的以致必须劳心费时让儿童加入其中的活动。这些活动都归属于诸如“好的”、“可取的”及“值得的”之类概念之下。这些活动能够给个体提供追求自己的爱好、实现自己的生活理想的机会。第二,与社会角色相关的义务;第三,则是与一些基本社会规则相关的责任;第四,则是以动机的形式被个人化的广泛的生活目标;第五,则是一些非常普遍的与遵从或追求他们的目的的方式密切相关的品格特征。
在彼得斯看来,对道德生活的复杂性进行分析,有助于摆脱通常人们简单地把道德教育认为是“‘使儿童具备良好的人际关系’或使他们观察人际关系的规则的看法”。道德生活的这几个方面是层层递进的,让儿童从事有价值的活动,并将其作为道德教育的一部分,旨在抑制他的自私心。而让他履行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在培养其责任意识,而这种责任意识的形成与尊重他人等原则密切相关,并随着儿童理解力的提高而逐渐加深。
道德生活的过程也是原则和规则逐渐在个人思想中内化的过程。彼得斯把个人思想“理解为社会规则以及与这些规则相关的功能的焦点”。在彼得斯看来,儿童最初就有各种各样的包括愿望在内的心理活动,这些心理过程与外界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就转变成为欲望,而这些欲望,“借助于审慎小心和社会适应而得到控制、定型及改造”。这样,“儿童的品格就呈现为他自己发展起来的特殊类型的规则服从。而且也发展了与这些规则有关的其他功能。”也就是说,“不仅存在着调节个人行为的规则,而且也存在着关于这些规则的‘缩小了的’立法的、司法的和行政的功能”。立法功能是依据原则对规则进行修订;司法功能则是学会运用规则,或者发展辨别与判断;而最后的行政功能则是要使儿童发展其服从规则的独特方式,也就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品格。因此,道德教育的过程也就是通过原则和规则的内化逐渐在个体思想中建立起对原则和规则的理解和灵活运用的过程,同时也是品格形成的过程。
道德教育的渐进过程也表明了对梯级原则理解的渐进过程。彼得斯认为,原则“它可以而且必须被理解为以一种完全具体的方式构成道德生活的一部分,而不使它们完全受文化的局限。”而他所说的这些适用于任何文化中的普遍原则,就是在原则的梯级上处于更高层次的、可以成为较低层次的原则的理由的原则。他说:“为了坚持一个理性的原则,一个人必须服从一些更高层次的原则,这些原则将使他能够根据环境的相应变化明智地运用规则,并且根据环境以及关于规则运用的条件与结果的经验知识的变化,不断地修正规则。在我看来,那些能够进行一些理性判断的更高层次的原则,是公正不偏、说真话、自由以及利益考虑”。这些高层次原则要发挥其作用,必须要建立在对基础规则的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上,这样,在道德教育中教育者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首先要引导儿童了解和掌握社会的基础规则。
由此,道德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对一些基础规则的传递。彼得斯认为:“教育者必须决定哪些是基础规则,并且坚定地在儿童的每一个早期年龄阶段传递这些规则。”而儿童的早期年龄阶段,正如彼得斯所说,是“理性苏醒”之前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儿童可能会做一些伤害自己和他人的事情,而这些基础性规则,必须是儿童从很小的时候就必须要遵守的。应该说,对基础规则的传递阶段,也是保证儿童向高一级规则理解阶段即第二级序阶段发展的基础。在这一阶段,儿童逐渐了解基础规则以及它们存在的理由,并能对自己的冲动进行控制,然后“发展一种根据这些理由评价规则和创立自己的准则的第二级序的习惯”。这样,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提高,他们就会逐渐发展到对原则的灵活运用阶段,建立起其自身的行为功能。
培养习惯并发展理性
为了实现道德教育目标,实施道德教育内容,道德教育究竟该采用何种方式,是通过习惯养成的方式,还是通过发展理性的方式?
在彼得斯看来,“亚里士多德试图把两者联合起来,但却陷入了一种关于道德教育的矛盾之中,这源于他同时强调理性与习惯的地位的尝试。”彼得斯所说的亚里士多德在道德教育方式中所遭遇的矛盾无疑具有客观性的一面。因为亚里士多德的确强调了习惯在道德德性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亚里士多德把德性分为两种: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而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而养成。为了说明道德德性的养成来自于习惯,他还运用了一些类比:“德性的获得,是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这就像技艺的情形一样……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而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而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而成为勇敢的人。”然而,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这种类比在有一些方面会被打破。技艺的产品,其善在于自身。只要具有某种性质,便具有了这种善。但是,合乎德性的行为并不因为它们具有某种性质就是,譬如说,公正的或节制的。除了具有某种性质,一个人还必须是出于某种状态的。也就是说,首先,他必须知道那种行为。其次,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并且是因那行为自身故而选择它的。最后,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的。也就是说,一个具有美德的人并不只是单纯地、以一种未加思考的方式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能够意识到、自觉地选择并且具有稳定的行为倾向。
这样,就出现了彼得斯所说的亚里士多德所陷入的道德教育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道德教育的方式是对儿童进行习惯的养成,而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培养有理性的、自主的、正直的个体,那么可能在方式与目标之间存在着冲突,这种对儿童进行习惯养成的方式势必会使儿童形成习惯,而习惯又与所希望的结果不相容。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与一些行为分析者的论证也表明了培养习惯与发展理性之间存在的矛盾。
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心理学家着重于从认知的角度对儿童的道德发展进行研究。皮亚杰的研究表明,儿童的道德发展始于处于道德他律阶段的活动,在这个阶段,由于儿童认知能力的局限性,以及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自然的权威关系,儿童表现为对规则的严格遵守和对权威的完全服从,而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逐渐提高,儿童会逐渐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规则,并试图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对规则进行修正,这样,学校就应该重视和培养儿童在团体中的合作性,通过让儿童在公平的基础上制定出共同的规则来促进道德发展。而柯尔伯格也认为儿童也是在逐渐的经验积累中形成他们的思考方式的,这些经验积累包含着对一些像正义、权利、平等和人类的福利等概念的理解,他在皮亚杰理论的基础上,区分了道德判断发展的三个水平和六个阶段,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道德教育的认知阶段发展理论,并把道德教育看成一个促使儿童道德推理和判断能力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
而对一些行为分析研究者来说,他们认为道德发展主要是由道德行为的获得或习得。在儿童很小的时候,道德教育就已经开始了,父母会通过奖励或惩罚的方式对儿童的行为进行引导,并且通过自身榜样的力量影响和塑造儿童的行为,使他们逐渐形成关怀、诚实等品质。道德行为也可能是间接地由父母来根据道德准则塑造的,但这种道德训练或习惯养成的道德教育方法在本质上也多是非理性的。由此,儿童的道德教育就在于训练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理性是不参与其中的。那么,在道德教育中,是采用习惯养成的方式,在儿童的道德理性尚未建立起来的时候,对他们进行习惯的培养和训练,还是如认识论者所提倡的根据儿童理性的发展逐渐进行,这确实看起来是一个矛盾。
彼得斯试图解决道德教育方式上存在的矛盾,把习惯养成和理性发展统合起来。他认为:理性道德的发展是道德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但这种理性道德不能直接通过诉诸于理性教给孩子们,而只能通过一些间接的方式,在这些方式中,习惯形成是主要的方式:孩子们“能够并且必须穿越习惯与传统的后院而登上理性的殿堂”。
在彼得斯看来,对规则进行由低级到高级的分类恰恰体现了儿童认知和理性的逐渐发展的过程,儿童最初的认知结构决定了他还不能对规则进行深入的思考,而只能严格遵循规则,因此,在规则的第一级序的阶段,所进行的对儿童基础规则的传递,是通过行为习惯的训练来进行,“例如:在控制排便训练阶段,儿童也许会染上非常普遍而且常常是笨拙的习惯—如呆板地服从规则,不情愿放弃他们自己的任何东西……因此,我们来到托儿所的门口,这是通向道德教育的入口处。因为,很可能在这里,品格特征的类型和练习它们的方式被确定下来。”而父母对儿童所进行的行为训练,意在教给儿童保持整洁这一较为抽象的原则,随着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他们会逐渐理解并灵活地运用这个原则。这样,道德教育中的习惯培养与理性发展的矛盾似乎就消解了,而人们之所以会认为在理性的运用和习惯的形成之间存在矛盾,完全是出于对“出于习惯”的解释的不同。
通常人们对“出于习惯”的解释往往是指这种行为的自动性、刻板性的反映,而不是行为主体出于对行为的关注和自动性。尽管我们通常会错误地认为习惯是以一种未加思索的方式表现出来,因此得出一种错误的结论,那就是习惯与理性之间并不相容。但彼得斯认为“习惯无需由于习惯的力量而得到运作。”习惯不仅仅表示对之前所做的事情的重复的假设,它还“伴有‘自动’地完成这一行为的能力的假设。”而“自动地”或自发地完成一种行为,在彼得斯看来,是指出于一种乐趣来完成的,这与单纯地“出于习惯”或“出于习惯的力量”所完成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些行为有其内在的动机。而且,自发地或自动地完成一件事情,也有着外在的目标,也正是这些目标,使得这些行为成为明智的行为。这样,彼得斯所说的习惯,不仅是出自内在的乐趣的行为,而且也有着外在目标的行为,也就是说,习惯是伴随着理性的存在的而发生的。这也是他为什么认为儿童“被训练成或被迫根据规则行事”,与“学会依规则行事”是大相径庭的根本原因。
而在道德教育实践中习惯究竟该如何培养?Ryle曾做了一个经典的讨论,他把习惯分为两类:一类具有单向度气质,另一类具有多向度气质。单向度气质是在特定条件下按一定的方式去行动的倾向。而多向度气质则是在变化环境中仍然能恰当地遵循相应的规则。单向度的习惯可以被称为是一成不变的习惯或日常活动,它们一旦被获得,这些行为往往是无需要反思的。这些行为的塑造,大体上等同于技能的训练。对这两种类型的习惯的区分并不能排除它们在实践上的连续性,最初,儿童可能被训练养成饭前洗手的习惯,然而这种单向度的习惯在他进一步理解了保持卫生这个原则后可能会成为多向度的习惯,他会逐渐认识到这些原则的例外情况。在这些例外的情况下,这些一成不变的习惯可能被打破。但总体上来说,单向度习惯的获得有助于儿童参与日常生活,被认为是道德发展和教育的条件。
多向度习惯在早期道德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些习惯是早期道德品质或品格特征的表现,是正确的行为和恰当的情感的表达。一个小孩子可能被父母训练不要伤害别人,安慰处于困境中的人,归还玩具,适当地表达关怀、遗憾等情感。在这些情境中,父母的训练旨在产生Oakeshott所说的“情感或行为的道德习惯”。这些习惯所遵循的规则和原则都是社会成员所应该遵守的基本的规则和原则(不伤害、尊重财产、遵守诺言等),实际上,儿童最终都能够认识到这些规则的相互关系。
在彼得斯看来,关注他人的痛苦的习惯,并不是美德,但它有助于在一些具体情境中产生怜悯之心,这些习惯,可能被认为是多向度气质:不同的情感和行为反应被一种相同的基本原则所支撑。通过这些社会化的彼此牵连的道德习惯,儿童最终能达到我们的道德教育的目标。这样看来,儿童道德教育的方式是通过习惯的培养而逐渐发展理性,获得多向度气质习惯也成为道德教育的一个关键阶段。
(作者单位:徐州医学院社会科学部,泰山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学院)
【注释】
①⑧Carr, D. and Steutel,J.(eds): Virtue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9, p248, p5.
②③④⑤⑥⑦⑨⑩[德]彼得斯:《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邬冬星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0页,第21页,第24页,第23页,第100页,第104页,第46页,第28页,第67页,第66页,第28页,第72页,第29页,第51页,第71页,第72页,第27页,第27页,第73页,第28页,第29页,第31页,第43页,第51页,第57~59页,第59页。
Graham Haydon: Reason and Virtue: The Paradox of R.S.Peters on Moral Education,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10,S1, pp173-188.
Peters.R.S.: Ethics and Education, London: Allen&Unwin, 1966, pp73-74.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廖申白译注,2011年,第36页,第42页。
Ryle,G.: The Concept of Mind, London: Hutchinson, 1963, p43.
Ben Spiecker: Habituation and Training in Early Moral Upbringing.in: Carr, D. and Steutel, J.(eds), Virtue Ethics and Moral Education, London:Routledge, 1999, pp217-230.
责编/张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