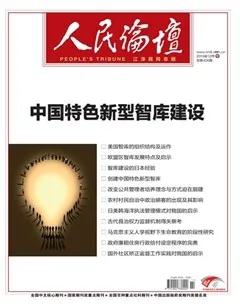现代罗马法体系到德国民法典体系化思想演变
【摘要】通过考证德国私法上“体系性思想”的谱系演变,文章厘清了自17世纪以来从古典自然法学家普芬道夫到19世纪后期潘得克吞学派温德沙伊德之“体系性思想”的内容实质及其相应的认识论基础。揭示出德国民法典并非以民事法律关系的要素为框架,而是以“权利”概念作为核心,完整地演绎出了涵盖整个民法制度内容的近代民法体系。
【关键词】法律关系 民法典体系 德国法 权利
回顾整个法学发展史,最早的成文法并没有遵循一个严格的逻辑体系,或者按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或者仅仅是简单的法条罗列。随着法学家活动的日益活跃和“立法者”命令,成文法开始以一定的逻辑结构进行排列。至少在优士丁尼法典时期,法学家的法和立法者的法律就已经在法典中特别运用了“体系化”的思考,在编、题的安排上有意识地把类似主题和相关主题安排在一起。罗马帝国后期的体系化、形式化的法律教育模式催生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高度体系化的结构,《法学阶梯》为这一体系的代表。作为法学家理论研究的产物,《法学阶梯》的体系构建自觉或不自觉受到法学家们哲学理念的影响。因此,文章论述的体系化应该包括两个层面:学说的体系化和法典的体系化。
法律关系的源始探究
萨维尼的法律关系理论。法律关系概念在1840年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教科书》中被第一次系统阐述,并由此成为一个专门的法学概念。原本不受法律规则约束的自由可以独立于任何一个自由的意思在道德的范围内展开。但现在为了使个人的自由能够和他人的自由并存,则需“法”给予必要的限制。通过规则将自由限定在一定空间,法律规则限定该行为的领域。基于这样的法律规则的规定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萨维尼称之为“法律关系”。
通过法律规则进行确定,在属于个人意思可以自由支配的领域,个人意志独立于他人意志而居于支配地位。这种个人意志所能独立支配的空间就是权利,萨维尼视其为法律关系的本质。在这里法律关系是(主观)权利之基础,且萨维尼将部分权利与法律关系同等看待。
“历史性”与“体系性”的统一。萨维尼学说的核心通常被归为“(有机的)历史性”和“(逻辑的)体系性”两点。他认为法只能是习惯法而非实证法,即“法是民族精神的产物”。法学对法律只能“有机的”历史地把握,也只有当法学能够有机的把握这些法律的素材时,法典化才有可能实现。要实现萨维尼之所谓“历史的”与“体系的”统一,“体系性”应建立在“历史性”的基础之上。
在体系的建构过程中,虽然萨维尼认为通过系统的加工即“历史性的观察”,可以把精选出来的素材综合成“指导性原理”(即抽象出法律规则),进而认识这些原理之间的相似点和内部联系。但作为法律规则与社会现实之间连接纽带的“法律制度”形成的法(制度)的秩序,正是通过法律关系这个媒介来完成的。
在萨维尼那里,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是一对没有办法截然分开的概念。在其倡m3fBUVg8BCyg6r4mp0W3TiMSW+ySJq/qAewdpceHJvg=导的内部体系中,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概念确实有作为体系化工具来使用的一面。他为实现和谐一体之法秩序(即构建内部体系)的需要,而创造的(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概念。在维亚克尔看来,萨维尼在其体系中创造了制度与法律关系的概念,虽然一直在强调他的“有机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它(们)作为构建秩序的工具使用,但事实上萨维尼并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们“制度”到底是什么,更没有明确讲述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与社会现实之间是怎样联系起来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之间又是怎样建立起“内部的关联”。
现代罗马法体系。受自然法学家沃尔夫学派理性主义体系建构的影响,萨维尼在其早期马堡大学的《法学方法论》的讲义中就已假定法律材料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认为形式主义(即体系化)的任务在于逻辑的处理安排法律规定之间的连续性与相关性。而《现代罗马法体系》借助于阐述法律素材内部相关性或相似性,指出“体系性”的本质就是能使抽象出来的法律概念与法律规则联系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从萨维尼《现代罗马法体系》可以看出,法律关系概念是一个存在于内部体系下的概念,和与其不能截然区分的法律制度作为连接社会现实与法律规则之间的纽带而存在。而这个内部体系只能做一个整体的理解,不能做科学的分类,因此并无逻辑性可言;由此,虽然维亚克尔也承认制度和法律关系作为体系构建之工具的作用,但其所言的体系只是“有机的”内部体系,而不是通常认为的“逻辑的”以法典化形式表现出来的外部体系。
潘得克吞学说体系与体系性思想谱系的形成
概念法学的形式逻辑体系。普赫塔通过对最高概念的演绎方法,创造了概念法学的金字塔体系,从而摆脱胡果和萨维尼学说中的不确定性。
普赫塔的概念法学是“理性法的遗赠”,其理论渊源于18世纪沃尔夫的唯理性法律思想。在方法论上,通过对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的发展,沃尔夫学派提倡一种更为纯粹的几何学方法来构建法学体系。但与沃尔夫基于普芬道夫的自然法理论不同,普赫塔追求与谢林在方法论基础上的一致,认为理性法只存在于实定法之中,法律的概念具有一种独立的“理智的存在”。在普赫塔那里,法律概念并非来自于社会现实,而只是一种逻辑演绎的产物。
普赫塔在其《制度概论》一书第一章至第六章中,首先导出的是“人”这种权利主体的概念,以及“人对于客体之法律上权利”这种“权利”的概念。其下,以权利的不同类型为基础继续演绎出整个的金字塔体系。这样,因为该演绎结构自身的逻辑自足和无矛盾性而对社会经验现实完全抛弃,法律概念因此从法律关系的经验现实中脱离出来。同时,概念法学的体系性思维被后来的潘得克吞学派接受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最终形成对德国《民法典》产生巨大影响的潘得克吞学说体系。
胡果对潘得克吞体系的贡献。在体系化问题上,胡果对潘得克吞体系构建的贡献,主要在于阐述了对物权与对人权的划分,这是区分物法与债法的基础,并把诉讼排除在私法的体系之外。但由于其对自然法批判之哲学基础在于康德的批判哲学,认为“根据凭借经验而得出的人类本性不可能对法律体系做符合理性的演绎推导”,即法律的体系从属于由理性的特性所决定的先验的形式,因此这种体系化不能按照法律材料本身的形式加以处理,以服从实践的需要。这也就意味着,在体系化问题上,胡果并没有完全摆脱自然法的影响,因此私法的体系化问题并未在他那里得到比较理想的解决。
但是,霍尔斯特·海因里希·雅科布斯教授在《十九世纪德国民法科学与方法》的后记里认为虽然德国在“罗马法的现代运用”中继受的是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但这主要是对罗马法具体规范的移植,侧重于法律规范本身,而不是对其体系的继承。因此实质上德国学者在私法体系化的过程中还是以《法学阶梯》为蓝本,并发展至后来潘得克吞学派最终形成并运用于德国《民法典》的体系的。其中胡果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法学阶梯》的三分法结构中,胡果认为这一体系的第三部分是程序法,应该把其排除于实体法之外,这样这个实体法就变成人—物的二分法结构。这个二分法的结果是把不属于人法的所有内容都划入“物法”的部分,包括物法、债法、继承法和家庭法中无法纳入人法的部分。但这造成第二部分明显的畸形。由此,胡果主张应在第二部分区分出有关对物的物法和对人的债法。胡果于1789年出版的有关当代罗马法的第一版教科书,当时这本书还叫做《法学阶梯》,早在这本书中,胡果就将“不涉及家庭关系和继承关系的物上关系与债权完全分开。”将家庭法从人法中分离出来,将继承法从物法中纯化出来,就如同将实体法与程序法分开一样容易理解,如是产生了四分法。因此雅科布斯认为,潘得克吞的分则体系最初就是由胡果这样构建起来的,只不过是由海瑟在其教科书中加以整理并被潘得克吞学派最终接受。
蒂堡对体系性思想的贡献。蒂堡是一个实证法学家,注重对社会实践性特征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他可以突破理性主义者从先验的角度看待私法体系化问题的模式。他认为,形式与内容的完全统一、逻辑顺序与现实之间完全的吻合,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实现。法典之中所包含的的规则并不来自于一个单一的原则,而是由不同的甚至相互冲突的原则组成,将它们组建成一个逻辑上的整体,可能导致现行法严重混乱。
在这样的方法论前提下,蒂堡首先在他的体系中设立一个总则,规定法的基本概念和原则,然后总则的内容在他的分则中得到具体的适用和阐释。在这里他和自然法学家的总则根本的不同在于,自然法学者那里的总则是对法的整个体系进行哲学导论的目的而设立,而在蒂堡的总则中,则倾向于对法律素材进行一般化处理,最终还是要服务于实践的需要。在蒂堡的体系中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则是构建体系的基础的转变。在此之前的体系构建强调法哲学的基础,但是到了蒂堡这里,客观法规范作为其体系的逻辑出发点,即以现实中实际存在的法规范作为构建法体系的基础。蒂堡这种以客观法为出发点的思想造成的结果是,权利义务不再是一种先验的范畴,而是法律规定的产物。因此蒂堡从实在法的角度看权利,认为权利不仅仅表现为一种行为的能力,更表现为一种要求他人履行自己义务的法律强制性能力。与这样的权利概念相联系,“财产权也不再被认为是自由的处理物的权力,而是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力”。
海瑟对体系化的贡献。海瑟认为实在法体系化的出发点是出于实践目的对法律材料的有机处理而非哲学。因此,体系的确立也要符合实践的需要。
海瑟1807年出版的《为了潘得克吞之讲授目的的普通民法体系的基础》明确了他在前述思想指导下形成的民法体系。该体系分为六个部分,即总则、物权、债权、家庭、继承和如何解除和撤销无效的法律关系。最后一部分,由于具有一般性特征,以及德国民法法律行为理论的完善,在后来的潘得克吞体系中被划分到总则部分有关法律行为的规定中。
就总则部分而言,在海瑟的体系中被完全赋予体系化的精神,从而使自然法理论发展而来的总则体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自然法的哲学导论的功能,并被后世的潘得克吞学派学者和立法者严格遵循。对物法和债法部分的处理则体现出胡果和蒂堡在此问题上的贡献。至于家庭法,在18世纪的德国学者中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到了18世纪,首先对家庭法作出个人主义的解释是由康德来完成的。海瑟在对家庭领域产生的权利进行分类时,直接采用了康德的理论,把其看作一种既区别于物权又不同于人权的一种混合的权利。由此,家庭法在海瑟的体系中作为一种单独的权利来看待。
温德沙伊德:潘得克吞学派的集大成者。在方法论上,温德沙伊德继承的是普赫塔概念法学抽象的逻辑体系模式并将其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他不承认存在一个普世的自然法,另一方面,受康德自由学说影响,他认为“民法的任务是为个人开创一个符合道德行为的自由的空间”,故在他那里“被理解为‘意志力’的主观权利被作为体系中的最高概念而予以保留”。这反映在他的《潘得克吞教科书》中,潘得克吞法的阐述顺序由以下六个部分构成:关于法的一般、关于权利的一般、物权法、债权法、亲属法和继承法。
首先温德沙伊德以康德哲学观为基础,从自由理念推导出在他的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权利”概念,然后对权利进行定义和分类。在对权利分类的过程中形成了分则中体现的各种权利:物权、债权、亲属关系中的权利、继承关系中的权利。在对各种权利具体分析的基础上,把每种权利中共同的部分概括出来作为“权利的一般”。他借鉴了萨维尼对法律关系概念的分析模式,不同的是,在概念法学式的逻辑结构中,由于其已经预先赋予了“权利”最高概念的地位,温德沙伊德的体系里已经完全没有“法律关系”存在的必要,因此他仅把法律关系作为一个工具使用—但不是体系构建的工具—指称的是人与人之间受法律规则规范的关系。
法律关系与德国民法典的体系构建
德国民法典体系之核心。梅迪库斯认为德国《民法典》的总则之内容是从其他各编中提取出来作为公因式的一般规则,主要论述了以下几个问题: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法律行为;其他规定(包括期间、时效、权利的行使、自卫、自助、提供的担保)。《德国民法典》的总则是按照最高概念的“权利”展开的,或者说在体系形成的过程中,先由作为哲学基础的“自由”导出“权利”这个最高概念,再由“权利”向下演绎各种不同的权利类型,具体到《德国民法典》就是分则四编标题。然后在这四编的基础上抽象出共同的规则作为总则编,由此产生的总则自然也是以权利为中心展开的。
潘得克吞学说中的“权利”来源于康德的自由,此处的自由是意志天赋的,因此是先验的无需证明的。权利义务成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而并不像萨维尼那样把权利与法律关系同等看待。所以,在温德沙伊德这里,权利是指作为法律关系内容的权利,而不是法律关系本身。换言之,德国《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权利”这个最高概念构建起来的,但“权利”不是“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同德国民法典体系。假使一般邦法典只粗略勾勒具体情况下的权利义务,德意志民法典则逻辑一贯地在两个总则部分处理了法律关系的共通概念要素。法律关系的(主要)要素是权利和义务,且法律关系的各种要素和法律关系本身具有相同的结构。
中文版的《德国民法典》中明确使用了法律关系一词的地方共有两处:一是第四编亲属法之第二章亲属之第四节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法律关系;二是第五编继承法之第二章继承人的法律地位之第四节多数继承人之第一目继承人相互之间的法律关系。通过上述德国《民法典》对法律关系概念的使用,我们可以推断出在现在的德国民法学说中,法律关系概念至少有两个特点:法律关系是法律规则所规定的关系;法律关系主要反映的是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综上,《德国民法典》的体系是由“权利”而非“法律关系”构建起来的。
结语
体系构建不应当仅仅是逻辑上的无矛盾性,还包括体系本身的科学性和合目的性。而法律关系作为一个私法上的工具,具有实现法律上效果意思的功能,但这并不等于承认法律关系是一个体系构建之工具。民法典的体系由法律关系的要素来构建的思路,既不能说明为什么法律关系本身是三要素,又不能说明总—分结构的合理性,关键不能明确体系构建之目的性和合逻辑性。
(作者单位:四川民族学院)
责编/丰家卫(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