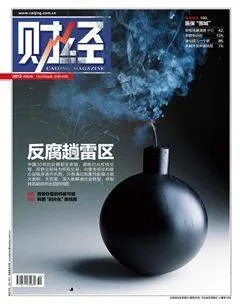问路高教改革
教育改革或将是中国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最近在上海发生的占海特争取异地中考、高考权,就反映出利益各方相应的诉求。
一方面是外来务工人员到所在地的教育主管部门申请放宽限制,另一方面是当地居民的激烈反应。一方强烈要求,一方强烈反对,高等教育改革注定不会是没有输家的改革。
高等教育碎片化生存
在2012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几位社会学的学者统计了北京大学的生源地信息,发现北京大学的学生中,真正来自农村的学生仅占12%-15%。复旦大学2012年的招生计划,其中四年制的本科生计划分配给上海的是111个指标,而与其相邻的江苏省获得的招生指标是61个,浙江省是63个,安徽省是66个。复旦大学分配给本地的招生指标是相邻省份的2倍左右。
这种本地化现象在所有的大学都存在,如果大学的地理分布是平均的,本地化倾向也不会造成太大问题,但中国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例如39所985大学,其中北京占了七所,上海占了三所,这两个大都市占了中国优质教育资源的26%,而其户籍人口却不到2%。
如果按照目前接近50%的城镇化率来计算,意味着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城市人口享有了85%以上的中国最好的大学资源。而实际情况应该更糟糕,因为户籍意义上的城镇人口还远低于50%,但高等教育却与户籍直接挂钩。
中国的高等教育呈现一种“碎片化”的特征。没有理由认为高校在地理上要平均分布,但其地方化的倾向却导致了严重的教育不公平。众所周知,教育公平是一种最基FbEAyD0gLetdTHjFXioSQA==本的起点公平,如果在起点上存在不公平,再完善的市场制度都无法纠正这种不公平,市场本身甚至还会放大起点不公平的效应。
大学为何歧视户籍?
大学之所以会歧视户籍有其绕不开的苦处,这就是属地化管理。大多数地方院校自然不用说,这些院校的财政几乎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因此其在招生政策上对本地倾斜也算是对本地纳税人的一种回报。
即使是中央部委直属的111所高校,虽然是由中央财政负责这些高校的行政教育经费,但高校本身在运行的过程中又不得不与地方的行政主管单位打交道,如税务、环保、交管、土地等,特别是很多高校在扩张的过程中要向所在地的土地主管部门申请用地指标,因此难以保持与地方政府完全独立。
实际上,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关联更为紧密,地方政府不仅与高校的日常运行相关,很多时候甚至还直接给高校投入资金,即使是部属院校,其很多建设资金与地方财政直接相关。例如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经费是26亿元,其中13亿元是要上海市进行配套,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主要的985高校。
在高校发展与地方政府投入直接相关的情况下,高校很难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再加上高校的运行又相对独立于中央政府,因此其相对较大的自主权和自身发展的诉求相结合,就必然会想方设法谋求地方政府的支持。由于高等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地方政府势必会要求这类资源向本地居民倾斜。
高教改革出路何在?
目前政策界和思想界最主流的改革方案有两种:一种与户籍相关,即“废户籍、立学籍”;另一种与户籍无关,即扩大高校自主招生的权限。第一种方案是国务院倡导的改革方案,也是目前唯一一种已经在多个省份试点的方案。这一方案的目标是要求高校逐渐放弃以户籍来分配招生指标的制度,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是要求进行渐进式的改革。
由于城市里存在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一部分随迁子女从小就生活在城市,他们也一直在城市里读小学和中学,突然要回到生源地参加高考,对其个人来说,不同地区教育内容的差异会使得随迁子女处于劣势地位;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会延缓城镇化的进程。实际生活中,农民工回流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子女教育的问题。
这种改革方案在不同地区的反响有巨大差别,那些人口流出的省份基本上都是持积极态度的,如山东、湖北、安徽等地都在第一时间制定了相应的细则,鼓励异地高考;相反,几乎所有人口流入地都是消极应对。在缺乏第二类型省市的支持下,单纯依赖第一类型省份是没有意义的,这些省份历来都是高考竞争压力最大的省份,开放与否不会缩小地区间的教育资源差距。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在户籍改革本来已经举步维艰的时候,再将高等教育改革与户籍绑定在一起,只会延缓本已进程很慢的户籍制度改革。
另一个方案是自主招生,这一制度在现阶段已经暴露出其弊端。首先,自主招生由于更加重视应用性的知识,实际上对农村生源是不利的。农村学生由于获取信息困难,无法与城市学生竞争,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起点不公平。其次,自主招生沦为高校竞争优质生源的一种手段,例如今年的几大联盟“北约”“华约”和“卓越”都将考试时间定在明年的3月2日,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其他相同高校的竞争,从而锁定了优质生源。最后,自主招生制度依然无法避免高校的本地化倾向,例如在2012年复旦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中,有587名上海生源的学生获得预录取资格,而与其相邻的江苏省和浙江省仅为88人和99人。
最彻底同时也可行的改革方案,应该是与户籍制度改革完全无关的,即在更高层面上统筹高等教育资源。一般来说,越是高等教育,越需要在更高政府层级上进行统筹,反而是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可以更加放权。同时,也没有理由认为完全放开户籍高考制度是可行的,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地方化的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后,各地的教育体系本质上还存在一些差别。放开户籍高考制度或会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大城市的学生入学率显著降低,二是多年提倡的素质教育会沦为一张废纸。
比较好的解决方案,是重新分配高校的招生指标,并将分配权限上收到中央政府。首先,中央政府不会有明显的地区歧视,能做到普世的相对公平;其次,这个政策也不会遭到发达城市的严厉抵制,因为招生指标是根据考生总数,具体的实施过程还可以是渐进式的,如五年内要从目前的状态下降30%,十年内要与全国保持平均等;再次,这个政策的执行效率会比较高,毕竟很多大学的校长是教育部直接任命的,但教育部是管不了地方政府的;最后,这能保留目前各地方的教育特色,素质教育不会受到明显冲击。
对于地方高校,还应允许其保留一部分本地化倾向,这减轻了中央的财政压力,并鼓励地方政府的投入,同时,中国最好的大学都是中央部委直属的,这部分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是能够并且也应该做到人人平等的。而居民“用脚投票”选择的就不是大学的入学资格,而是更加适合自己的教育方式,这更加符合教育的基本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