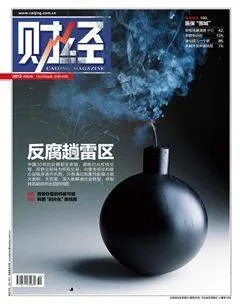徙戎论
中国古代的民族政策,可以粗略分为两种:民族融合与民族隔绝。人为地促进民族融合,可能增进民族和解,也可能引发族群摩擦;民族隔绝自然会导致民族隔阂,却也可能保持暂时的和平。
魏晋世道,北方少数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是后世史家所称道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惠帝元康年间,氐族首领齐万年自立为帝,战争打了四年,关中为之残破。太子洗马江统忧心之下,写了一篇《徙戎论》,建议将关中地区的异族全部迁回草原,实行民族隔离政策。西晋朝廷没有理睬江统的言论,结果不到十年就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司马王朝被迫南迁,偏安江南。
《徙戎论》的是非对错,历来看法不同,当然都跟彼时彼处的社会情势有关。到了清朝,在特殊政治文化的作用之下,它成了酝酿文字狱的材料。
乾隆四十五年,山东寿光县审理了一件诬陷他人盗卖民妻的案子,牵扯出一个代作呈词的读书人魏塾。从魏塾家中,搜出禁书一部以及抄录的《徙戎论》一纸。《徙戎论》记载在《晋书》里,并不是违碍文字,但魏塾抄完之后,又加了一段批语,慨叹晋惠帝不能采纳江统的宏谋大略,大臣们也都是“驽才猪眼”,可见西晋之亡,实有天命存焉。魏塾最后说,其实“乱华”的不仅仅是晋朝的五胡,“今之回教,又其后绪矣”。这最后一句要了魏塾的命。地方官审他,魏塾说因为看见历史上说晋惠帝容留五胡,结果酿成大乱,于是想到今天各处的回教都是外国来的,恐怕将来也会混闹,所以写了这么两句。山东巡抚国泰认为,魏塾评论《徙戎论》,竟将今天的回教妄为比拟,应当处死。
戎狄胡虏,这些字样在清朝都是敏感词汇。魏塾敢在这上面做文章,而且要搞极端的民族隔离政策,触犯满洲皇帝的忌讳是自然的。按理说他只在家中随手写下几句,没有传扬更没有出版,社会危害不大,但思想犯的真谛是,只要“作此想”,就须“服此罪”,他的结局可想而知。
清朝盛期的皇帝,也有不忌讳夷狄的,那就是雍正。在那本著名的《大义觉迷录》里,他就大谈华夷问题,中心思想是华夷之辨只是地理分布的不同,并无文明野蛮之分。可惜乾隆跟乃父不同。雍正刚刚驾崩,他就禁了《大义觉迷录》,这本书成了历史上唯一一部在本朝就被禁的御制书籍,儿子禁老子的书,大概也仅此一例。其中的原因,固然有掩盖宫斗内幕的因素,但雍正在民族问题上过于坦白的态度,也不合乾隆的政治理念。
清朝的民族政策,是在承认现状基础上的民族隔离,理想的状态是各民族“各安其地,各从其俗”,都在各自历史的延长线上发展,既无冲突,也不融合。所以直到清末以前,各民族间的移民、通婚都有严格限制,乾隆还经常为满洲人沾染了“汉人习气”而大发脾气,好几回宣谕要求八旗子弟保持“满洲特质”。魏塾同意江统的“徙戎论”,虽然实质上也同意民族隔离政策,但是他主张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是清廷不能容忍的。至于回教(那时尚无回族的概念)是民族通婚的结果,本来在中原就广泛分布,就更不是魏塾这个乡间老儒所能知道的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清朝民族政策在文化领域的投射,就是基本上禁止对民族问题的讨论。《四库全书》对有关民族问题的文字草木皆兵大肆删改,自不待言,就连大臣建议“满汉一体”,也会引起乾隆龙颜大怒,哪怕这句满汉一体本就是皇帝常说的。
魏塾的判决是斩立决,从案发到结案只用了一个来月,但民族隔阂的阴影,并没有淡出乾隆朝的文字狱。三年后,广西抓到一个游荡的回民,行李箱中搜出回教书籍多种,其中有《天方至圣实录年谱》一部,因为用了“至圣”两个字而被巡抚朱椿指为悖逆,请旨治罪。乾隆哭笑不得,这是人家的宗教,与僧道喇嘛一样“各奉其教”,用个“圣”字不是很正常嘛!朱椿如此矜张,“实属可鄙可笑”。乾隆不曾反思,这些地方官员的可笑举动,与他所奉行的民族隔离政策究竟有无关联。
皇帝对民族问题过分敏感,固然跟复杂的民族状况有关,既然议论可能造成问题,那干脆大家闭嘴;但隔离的结果是隔膜,是一般民众对民族问题的无知,是各民族对其他民族历史、风俗及社会结构的陌生感。魏塾的徙戎论、朱椿的不识回教经典,都是这种无知和隔膜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