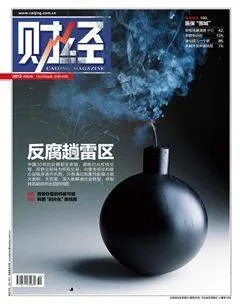科耶夫的世界
“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戴高乐收到一份名为《法国国是纲要》的建言书。此文洋洋3万多字,以罕见大手笔勾勒出战后世界秩序,并为刚刚光复的法国如何重塑大国地位画出深刻而极富想象力的蓝图。
文章作者是亚历山大·科耶夫——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原不是法国人,于1902年出生在沙皇俄国时代的一个莫斯科贵族之家。十月革命时,年仅十几岁的科耶夫看到机会,在黑市上倒卖肥皂,赚了一笔钱,旋即被“契卡”捕获。但聪明过人的科耶夫,居然从“契卡”手中逃脱。
离开布尔什维克政权后,科耶夫前往德国随雅斯贝尔斯钻研哲学,后迁居巴黎,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把他的财富一扫而空,生活陷入窘境,只得另寻生计。托朋友举荐,1933年到1939年,科耶夫到法国高等应用学院接手一个哲学讨论班,讲解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班上学生在“二战”后纷纷成为法国思想界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包括乔治·巴塔耶、雅克·拉康、莫里斯·梅洛-庞蒂、雷蒙·阿隆等。而科耶夫对黑格尔的解读,慑服了这些未来的大学者。
科耶夫宣称历史终结:法国大革命实现了自由、平等的目标,历史进化已经结束,哲学也面临终结,而实现“普遍共同国家”的目标变得可能。出于这一考虑,科耶夫在“二战”结束后,转身步入政界,担任法国经济部高参,成为欧共体最早的设计师,也是关贸总协定最早的设计者之一。对今天的世界有重大影响的这两个国际制度,构成了科耶夫对于世界秩序之构想的现实表达。
其实,早在《法国国是纲要》一文中,科耶夫就已勾勒出欧共体的模样。科耶夫开篇即提出,战后世界有两个危险正直逼法国:一是德国的再度崛起,会使法国沦为二流国家;二是美苏之间可能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法国卷入,并使其受到永难恢复的伤害。为此,科耶夫厘清了法国两个生死攸关的任务:在苏联人与英美人之间可能要爆发的战争到来之前,必须尽最大努力确保实现中立;在苏联之外的欧洲大陆,在和平期间,保证法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相对于德国的领先地位。
对刚刚光复、百废待兴的法国而言,要完成这两个任务难度可谓极大。科耶夫甚至认为,如仍囿于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这两个任务将不可能完成。“德国的例子表明,在如今,一个民族无论多么优秀,只要政治上顽固地坚持民族意义上的排他性,迟早都要结束其政治上的存在。”
因为民族主义的诉求无法动员其他国家的人来支持自己,法国在这一点上不会比德国做得更好。由于时代的变迁,“现代国家的基础必须是一种广阔的、由加盟的民族国家所构成的、‘帝国性的’联盟”。苏维埃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是超越民族国家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价值理念也是超越民族国家的,它们都可以组建成为这样一种帝国联盟;法国若不能寻找到一种超越于法兰西之上的理念,以此为基础吸引更多的国家来组建一个帝国性联盟的话,便注定衰亡。
在科耶夫看来,这样一种超民族的价值理念是存在的,那便是拉丁-天主教价值。拉丁世界对于生活、审美感的品位,对于政治与经济、生活之间均衡感的把握等,是南欧拉丁国家所共享的,并且有宏大的海外号召力。以此为基础,可以吸引众多力量,组建一个新拉丁帝国,它足以与斯拉夫-苏维埃帝国和新教-英美帝国成鼎足之势。
拉丁帝国会是“三国”当中最为弱小的一个,但由于它作为一个关键的平衡力量存在,便有可能抑制住另外两大帝国的战争冲动。法国毫无疑问会成为这个拉丁帝国的头领,于是便逆转了法德之间的态势。这种逆转以法国对自身民族主义的放弃与超越而实现,在此框架下甚至可能进一步吸收消化德国,令其也逐渐超越自身。
而人类的终极命运并不是伴随着三大帝国对峙到老,而是最终在现代性的消化下,形成一个普遍均质世界。该种世界将最终弭平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之间的差异,人类达到大同。达到普遍均质世界的途径之一便是超国界的普遍贸易秩序的建立。科耶夫再一次看得深远并投身实践。
欧洲与世界,并不是严格按照科耶夫的设想在发展。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再阅读他的著作,却不得不钦佩他当年的如炬目光。他的深刻思考,对于仍沉醉于民族主义的人,也有着重要的“解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