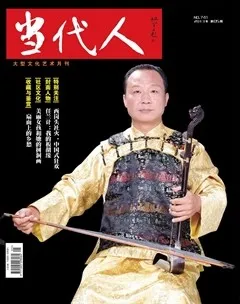柳林铺,太平河上说古今



柳林铺位于石家庄市区正北,村落北依太平河,南靠三环路,西临京广铁路,东至胜利北大街。村北太平河原为滹沱河干流。根据《石家庄市地名志》记载,村西原大同寺的碑文显示,唐太宗贞观年间已有“柳林屯”村名,因滹沱河边绿柳成荫而得名。真定府至获鹿城的驿道从这里通过,元末沿驿道设置急递铺,后来村名渐渐改称“柳林铺”。因濒临滹沱河,又是驿道经过处,明清时期这里发展为繁华的水陆码头。
我家就在岸上住
今天的太平河公园是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但很少有人知道,柳林铺村北这一段的太平河,并不是古太平河的河道,而是原滹沱河的南支流。翻开《石家庄市地名志》一书,里边一幅“石家庄市兴起前自然村落分布图”清晰显示:自西北方向而来的滹沱河,在流经今天的正定县西部时,分为两股向东南漫流,其中,南边一股从柳林铺村北经过。据何秋来、任春振、刘家妮、刘更深、李振华等老人回忆,从前南边这股水是主流,法国人修京汉铁路线时,在这里架设了18孔桥,日伪时期扩建为24孔桥,而北边现在的滹沱河主流,原来是支流,京汉铁路通过处最早只有5孔桥,后来修成18孔桥。主流和支流中间是漫漫河滩,但发大水时就分不出来了,“从柳林铺村往北一看,白茫茫一片,大水对面就是正定城。”
据刘更深老人回忆,1917年、1939年和1948年的三场大水,改变了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1948年那场大水,将北边河道彻底冲开,从此北边成为主流,南边成为支流。北边河堤(土堤)塌陷,现在成了河的中心。村民记得,那一年,有60余名解放军干部要坐船北上,柳林铺村民划两条小船,小心翼翼地向北摆渡,结果第一条船过去了,第二条船渡到河心,一个大浪打下来,船散人亡,有36人在那次渡河中遇难。
今天,面对已经断流多年的滹沱河,人们很难想像,原来的它是多么桀骜不驯。据柳林铺村民回忆,这里十年九灾,少有哪年不发大水。洪水来时,“一晚上靠南能滚二里地”,直奔东古城、北高营一带。清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的一次洪灾后,部分沿河居住的村民因房屋田地被冲毁而迁居南边,建一新村,名柳新庄(构成今天柳辛庄村的一部分)。不过自从修了京汉铁路以后,柳林铺村就极少挨水淹了,老人们记得一句传说:“柳林铺淹不了,是朝廷封了的。”这当然是夸张,但仿佛水涨村长,洪水再也进不了村。是建在河边的镇武庙镇住了大水?这当然不可信。现在人们分析,因京广铁路桥坚固的桥墩挡住了部分洪水,减缓了流速,再加上京广铁路以东河道宽广,所以洪水才不至于再淹村子。
以前,两条河道中间的河滩上没有村落,只有耕地,现在,这里有红旗、前进两个村子,有果树研究所、滹沱河化肥厂等众多单位,这都是上世纪以来新建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好岗南水库和黄壁庄水库后,滹沱河水流被彻底控制住,这一带河滩地上渐渐盖起众多楼房。
舟车往来不寂寞
靠水吃水,成为这里人们的生存之道。历史上,柳林铺人以货运、摆渡、搭私桥为三大主业。
在滹沱河边,柳林铺是一处重要的水路码头。同时,它亦是陆路交通要道。从山西经获鹿至正定的古驿道从这里通过,山西的煤、生铁,太行山区的大枣、核桃等山货,都先经驿道运至这里,再装船送到滹沱河下游,经藁城、深泽至沧州献县,在献县倒大帆船,顺子牙河至天津。而天津的“洋货”——洋布、洋油、洋面、白糖、钟表等,也是顺这条水路先到柳林铺,再走陆路到西部山区。曾经,在柳林铺村北、滹沱河南岸,货栈、码头绵延2华里,直至肖家营。前些年修太平河公园时,还从河道里挖出过煤以及一整船铸铁铁锅,这显然是河运时代的遗物。当时,除了驿道上送来的货物,本地盛产的棉花,也多从这里装船运至天津,再织成洋布返销回来。
历史上,柳林铺几乎家家有船,最多时全村达到96条。每次运货,都是几十条船搭伴走。艄公喊着整齐的号子,小船首尾相接连成一线,行驶在广阔的滹沱河上,场面蔚为壮观。何秋来的爷爷何洛用、刘更深的爷爷刘洛德,都曾经当过“大船头”。按现在的话说,这俩人都是掌握造船技术的“土工程师”。他们到周围各村采购大杨树,回来解成木板,做成平底船。船的长度取决于树的高度,因船底和船帮要用整条木板纵向拼接,中间不能断,否则不结实。一般柳林铺村的船长十几米,宽五六米,没有帆,用木竿撑着行驶,能装几千斤货。两条船绑在一起,可摆渡一辆解放牌大卡车。
滹沱河的水流随季节变化很大,但除了冬季,一般都能行船,因这些小船即使装满货,吃水也不过一尺来深。那时的船工掌握了技术要领,会看水深,会看哪里有漩涡,哪里有滩涂。往下游走叫“走顺水”,发大水时走的快,一下午就能到藁城,晚上到深泽,第二天到献县。但回来时就难走了,需要拉纤。
除了行船、摆渡,柳林铺人还搭私桥。所谓搭私桥,就是当冬天河水上冻无法摆渡时,在河面搭设简易桥。人从冰面上通过,安全没保障,从简易桥上过就保险许多。这种桥由各户凑木料、柴草等建成,需先划两条船到河水中间,在船上搭云梯,再由8个壮汉站在两边云梯上,抬起400斤重的大石头,喊着号子往下砸桩。据说砸一天桩下来,人累得连炕也爬不上去。木桩深深砸入河底后,再在上边搭木板、铺柴草、垫土、泼水、冻冰,一座临时性的草桥就搭成了。这种桥离河面约一人来高,能过马车。第二年春天解冻后就拆掉它,如果不拆,大水一来就冲没了。私桥顾名思义不是公益的,冬天柳林铺人靠守在桥边收费挣钱。
“柳太”铁路与“正太”铁路
因为柳林铺村是重要的水运码头,故在设计正太铁路时,曾考虑过把柳林铺作为东端起点。为什么筑路者相中了柳林铺?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地域文化研究所教授李惠民认为,缘由大致有两点:首先是距离因素。柳林铺属正定县,距正定府城15里。既然京汉路经过柳林铺,能够在此相接,何必舍近求远,花巨资架桥过滹沱河去正定府相接呢。其次是航运因素。柳林铺具备一定的水运条件,用当时华俄道胜银行副代办的话说:“原拟修路物料,可用轮船径运至滹沱河南岸之柳林堡。”或许不仅仅是修路物资,设计者可能还希望正太铁路的货物既可以在此转运芦汉铁路南下北上,又能够装船直奔天津,水陆并举,岂不更好?
到1902年,清政府督办铁路总公司大臣盛宣怀与华俄道胜银行废除原合同,签订《正太铁路借款合同》。此时,虽然铁路正式命名为“正太铁路”,但东起点并未变更。李惠民考证,变动发生在合同签订后的一年之间。1903年秋冬,当法国工程师埃士巴尼等人进行实地勘察时,发现在柳林铺建站实无必要。第一,设计者发现,滹沱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除雨季外,“唯查该河下游一带水浅,不能行使轮船。”(柳林铺人做的船属于小船,不是轮船),根本不可能实现正太车站、京汉车站与河运码头三者相交的设想,而筑路器材亦不可能用轮船运至柳林铺。第二,1903年京汉线铁轨已经铺过了石家庄,并建成了柳辛庄(紧邻柳林铺)和枕头(今振头村)两个车站可供选择。如果选在石家庄,可以使由获鹿方向而来的正太路垂直与南北走向的京汉路相交,这种方案线路最短,费用最省,如果选在北距石家庄十多华里的柳辛庄,则铁路将向北转向,无疑将增加建设费用,延缓修筑工期。因此,以埃士巴尼为首的设计人员坚定地选择了石家庄。
告别与转型
自从正太铁路与京汉铁路交汇于石家庄,大量物资通过更快捷、更稳妥的火车来运输,这改变了千百年来由驿道和水路构成的运输系统,使石家庄这个铁路交汇点崛起成为新的城市中心。古驿道从此衰落下去,但滹沱河还在。只要有水,柳林铺码头就有生意可做。事实上,这里的船运生意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达到最盛。不过,这也是它最后的辉煌。1940年石德铁路建成通车,从那以后,船运走向没落。
石德铁路西起石家庄,东到德州,而建成于1912年的老津浦路(从天津至江苏浦口,今为京沪铁路的一段)也从德州经过。两条铁路在德州交汇,来自山西的煤铁可经石家庄运至德州,再沿津浦路北上南下运至天津、江苏。就这样,新兴的铁路和公路,逐渐取代了速度慢、运量不稳定的水路运输系统。
柳林铺的船运生意少了以后,还能干摆渡和搭桥,真正让他们彻底告别吃水上饭的日子,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时,随着滹沱河上游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的兴建,滹沱河水被“掐”住了。同时,下游跨河大桥开始兴建。1962年,村北跨滹沱河南支流的柳林铺大桥修好,从此村民再也不用走私桥。
改革开放以后,这里兴起了众多鞋厂和编织厂,鞋厂和肖家营一带的几乎同时兴起,主要做布鞋销往南三条。编织厂做编织袋,另有配套的拔丝厂等。现在这些厂子所剩不多。2008年进行股份制改造时,村里将土地收回进行集约化管理。今天的柳林铺村虽然没有了古驿道,没有了水路运输,但仍处交通要道。它东临胜利北大街,南临三环路,视野开阔,行车方便。村里沿三环路盖了许多汽车门面出租,另有汽车配件城和花卉市场等。未来这里将利用交通区位优势,继续发展大型商业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