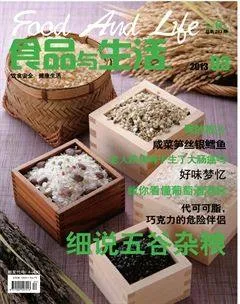好味梦忆(一)
奔七老猿,为寻找“正在消失的上海美食”不遗余力地捐出时间、空间,外加馋唾水的“食痴”。 蛋饺肉圆 幼时最爱看母亲做蛋饺。那时物资匮乏,什么都要凭票。春节供应略增,补充蛋票可买冰蛋(据说是提炼了什么好东西后,不能烧白蛋和煎荷包蛋),只能用来做蛋饺,因为它连炒着吃都不香。母亲做蛋饺时,先在用铁板压住旺火的煤球炉上“坐”一只稳定性强的铁勺子,用调羹舀一勺蛋液上去,用力精确地使蛋液扩散开,迅速摊成一张皮,另舀一勺肉馅上去,不失时机地将一半蛋皮摺过去,最终煎成蛋饺。正在做功课的我闻到蛋香,从二楼前楼到灶披间,眼睛馋馋地看着蛋饺,就想伸手“钳”一个尝尝。母亲用严厉的目光制止了我的妄想,见我还不死心,又加了一句:“里面是生的,吃了要发痴!”我当然不想做在电车站甩手的憨大,于是馋唾水立马被吓了回去,等待年夜饭餐桌上那最勾馋虫的“全家福”。 蛋饺的搭档是肉圆,那可不是狮子头,也不是北人所谓的“四喜丸子”,连小丸子都不是,没有面粉,只是小小摔打上劲的“斩肉”,除了瘦多肥少的猪肉,只有葱姜末和一点点盐。味精也配给,但不能乱用,也无需用,就已经够鲜。这“哼哈二将”上场,年的氤氲四处弥漫,如今忆及,梦里都会馋醒,枕头上一定是多多的馋唾水。 后来物资丰富了,但大家的注意力多在升学、就业、结婚、生子(女)上,没多少时间和精力花在蛋饺、肉圆上。等有了时间和精力,父母逝去,自己已失怙恃,并迅速垂垂老去。在食肆里尝到的蛋饺、肉圆也全然不是当年那个味道,只好梦忆、梦忆了。 榨菜 小时候还有一样好东西,就是榨菜。真正四川货,南货店里或酱园里原甏取出,用薄薄的“草纸”包好,有心的店员在天渐热近黄梅时还会关照:“抓紧吃掉,当心发白花。”那时科技欠发达,食品的保质期都不长,酱油和醋时间长了都会发白花。 后来知道,其实严格来说,榨菜主产地应是重庆附近的涪陵。结婚后得知岳母老家是重庆江津县白沙镇。老家曾有岳母的表妹来访,我们称年龄比我们略大的她为“表姨”。表姨也没带其他礼物,只有像“弥陀芥菜”般的整坨鲜榨菜来,我才知道榨菜的前世今生。 再后来,原甏的大块榨菜一夜之间人间蒸发,取而代之的是小包装“斜桥榨菜”。虽然更方便进食了,但代价却是全然不是那滋味,可能还有数不清的添加剂,有人形容其:“像撒胡椒粉似乱加阿二头!” 再后来,涪陵榨菜又回来了,向斜桥的赝品看齐的小包装细条状,也有片状的,还加上明星代言。我不知区区榨菜为啥一定要明星代言?那明星是涪陵人吗?他种过或制作过榨菜吗?他经营过榨菜吗?他演过同榨菜有关的戏吗? 依我“小人之心”度当地官员、企业家“君子之腹”,此举大约是为了“提升”榨菜的价值和地位。但他们其实错了。榨菜是涪陵,是重庆,也是中国食品的一张名片呐!中国榨菜(分渝产和浙产两种,但渝产远胜于浙产)是世界三大腌菜之一,另两大是德国甜酸甘蓝、意大利酸黄瓜。申遗还来不及,怎能让它在你们各位手中变味呢? 说起榨菜的历史,也超过100年。那是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当时的四川涪陵商人邱寿安在湖北宜昌开设“荣昌酱园”,兼营四川大头菜,因竞争激烈,生意清淡。幸亏四川资中县人氏邓炳成在老家将同样材料制成一种新品腌菜,滋味迥异。发往宜昌后,邱老板尝后觉得味道鲜美,经试吃推广,大打广告,遂在酱园畅销,使之名副其实地既荣且昌。 榨菜是十字花科植物,即茎用芥菜的瘤状地上茎加工而成,因在制作过程中需经压榨脱水至微干,故名。 榨菜可直接食用,多充作配料(也可作主料),宜于炒、烧、煮、拌等多种烹饪方法,也可用于汤、羹等菜式。常用的有麻油拌榨菜丝、榨菜肉丝汤、海带榨菜炖冬瓜、榨菜炒肉片等。还可用作面点馅料,甚至作调料。 随着时代的变迁,南货店没有了,酱园不存在了,超市、食品店要有货架期,产品或多或少要使用添加剂。不过我认为,一定有店专售“手工制作”的榨菜,贵点不要紧,东西一定要好。我曾从重庆来客那边获取老式的原块榨菜(说明还有人在做,或者还有人做了自食及馈赠亲友),当晚切一块成丝,与肉丝同炒,一半让家人做次日“粥菜”,一半汆汤(打一只蛋使之成“花”),真是味觉惊艳。“剩余物资”又吃了一周。不知梦忆之中的神品何时还能再尝。 记得明末小品家张岱有《陶庵梦忆》传世,前辈作家唐鲁孙文章多数也是“梦忆”。此二公均是亡国后的“回忆录”。我是失去好味即“亡味”后之“回忆录”。但愿梦想成真,从此常有吃,子孙后辈都有吃,使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地球略为美好一点。毕竟,在雾霾中有一点好东西吃吃也是享受呀!(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