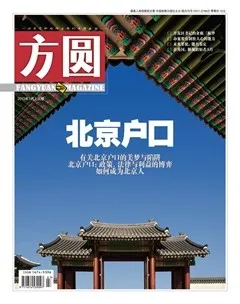铁盆里的豆子发芽了
原来一直以为重揭灾难是在“受访者”心灵的伤口上洒盐,而事实是,人人都不去触碰,伤口里的脓水就一直包裹在里边,你逼他打开,把脓水放出来,其实是对“受访者”的一次治疗
有一天,一位已经当上了家乡政府领导的朋友问辽宁女作家孙惠芬,回老家忙什么?她答,做自杀调查。朋友瞪着她问,谁自杀了?孙惠芬答,不是谁,而是很多。
与媒体报道的那些引人关注的自杀事件相比,绝大多数的自杀往往如秋天之叶,默然飘落然后归于沉寂。孙惠芬最近创作并在《人民文学》上连载的《生死十日谈》,即是针对农村最普通的自杀现象的“调查报告”。
对于长期以来关注乡土文化,执着于乡村叙事,并创作了大量优秀乡土文学作品的孙惠芬来说,她虽经常往返城乡之间,可她以前并不知道她的家乡会有这么多人自杀。直到她的朋友大连医科大学教授贾树华抛出了“农村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并动员她加入进去,她才知道,她的家乡有那么多人面临着生与死的艰难抉择。
做这个课题需要勇气,因为在很多地方,谈论死是一种忌讳,但剑走偏锋的“诱惑”以及现实力量的驱使,推动孙惠芬完成了这部作品。“我无法逃避。”孙惠芬这样解释。
为何要着眼于“死”
《方圆》:作家的生活造就作家的文学世界,你近两年自称“放逐乡村”,是在寻找新的写作资源吗?
孙惠芬:“放逐乡村”,应该说是整个身心的需要。当然这个身心,是已经被创作浸泡出来的身心,所以身心的需要也包含着创作的需要。
当时确有一部长篇的构思,想到故乡田野寻找灵感。但最真实的想法,却是远离写作,远离书斋,远离跟写作有关的文坛或文圈,好好地透透气。我的所谓放逐,就是这种让自己忘记一切,投入到另一世界的放松和忘我。
《方圆》:“放逐”乡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可以收获些什么?
孙惠芬:最初是有一个方式,在家乡农业发展局挂职,这也经过了层层作协组织的努力,目的是为解决一个吃住的地方。刚“挂”进去时,我把自己当成农发局的一员,跟各处、室的工作人员下乡,有畜牧、种植业、信访、扶贫等等方面的工作。
这些辐射了当代乡村方方面面的端口,就像一条条通向大地纵深的铁轨,让我进入此前无法想象的天地。虽然不一定接触到最幽微处,但我的身心是放松的、愉悦的,我放纵自己的感官,去感受,去面对,去倾听,去做深深的呼吸。
一些死鸡、死猪被二道贩子带入市场,如何进行污染处理并堵住非法贩卖?一些大棚菜农为蔬菜施过量农药,如何检查大棚蔬菜的用药成分?水源地农民为了城里人吃上干净水,不得不迁到故乡之外,可迁后土地补偿迟迟不给,如何安抚那些拿不到补偿就去北京上访的农民?住在偏僻大山里的村民动迁,可是人搬了土地挪不走,如何解决他们的种地困难?
这些事情,附着层层叠叠的社会问题进入我的视野。
在最初的日子里,它们之于我,仅仅是流动在乡村大地上的空气,它们除了让我陶醉,没有别的。因为我在城里的家呆得太久了,太需要这些信息在耳边眼前流动了。应该说,在刚刚下乡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对这些社会问题进行思考,我陶醉在拥有“新鲜空气”的喜悦当中。不但不思考,且连跟写作有关的笔记都不做,似乎因为写作而造成的敏感神经已经在这种自由的空气中休眠。我特别需要这种休眠,或者说,长期的思考已经让我对思考产生厌倦。那时在乡村,我最想成为的,就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呆傻者。
神经是怎么觉醒的,很难说清。大约是在半年以后,家乡的朋友在不断增多,随之我拥有了更大的游走空间,比如法院的审判庭、信访办的接待室,比如从市区通往村庄的每条道路。跟创作有关的愿望像捂在铁盆里的豆子,接受了某种适宜温度的孕育,一点点长出须芽。《生死十日谈》的写作,就是这样发生的。
《方圆》:在拿到乡村平民自杀现象这个课题后,你谈到过心里曾有矛盾,贾树华教授的课题显然不符合你“一心想在生活中寻找快乐”的状态,你的心态是如何调整的?
孙惠芬:青少年时期,我是一个忧愁多于快乐的人,常常无病呻吟。后来我拿起笔开始写作,便感到因时光流逝而生出的虚无感对我的写作在起着作用,因为午睡醒来和夜深人静时,我常能感到人跟现实世界的分离,常能体会这种分离带来的惊悸和不安,以至于我不得不企图用笔挽住什么。
可是快到五十岁的时候,我的虚无感陡然消失,惊悸和不安无踪而去,我活得殷实又现实,我愿意接触快乐的事物,我懂得快乐对生命的重要,而写作却不再是我生命的全部。或许,只要你不是过着二手的生活,只要你有着深度的生命体验,都会有经历这样的改变,在此之前,我根本无法知道有一天我会这样。
对于一个写作者而言,我确实曾觉得这是在堕落——一个总想远离痛苦的人怎么能写出好作品呢?可事实证明,只要你选择了一条路,这条路上的“风景”,总是你创作的源泉。
下乡半年,我的好朋友贾树华就向我抛出了这样的课题,作为一个写作者,不被吸引是不可能的。面对生者谈死者,这是文学因子最活跃最发达的区域,可是去揭一个个灾难的伤口,不太符合一心想在生活中寻找快乐的我。最后痛下决心,有树华的功劳,也有某种来自写作的的原动力。但因为种种原因,我只跟课题组走了五天。我爱人在电视台纪录片室做编导,他跟课题组拍了很多素材。了解更多的自杀故事,是因为我看了二十多天的录像带。
《方圆》:这场调查如你所说是要“更进一步揭开他们的伤口”,目睹伤口也是需要勇气的,这些难过和痛苦的案例,带给你何种感受?
孙惠芬:记得第一天在车上听一个十九岁小伙自杀的故事,我很快就晕车呕吐。而实际上,面对“被访者”和“目标人”,当时的感受并不比回家看录像时更痛苦,因为我在秋天的乡村大地上游走,满眼都是金灿灿的田野,情绪会得到释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书中不断写到人如何建立和自然的关系的原因,我发现了自然的力量。
而回到家里,情绪的阴霾包裹在一个屋子里,它们的重量才越发清晰而难以承受,尤其是看我爱人拍摄的素材带时,我差一点抑郁。或许正因为如此,写作的情绪才格外饱满。
不过,有一个现象是采访之前想不到的,原来一直以为重揭灾难是在“受访者”心灵的伤口上洒盐,而事实是,人人都不去触碰,伤口里的脓水就一直包裹在里边,你逼他打开,把脓水放出来,其实是对“受访者”的一次治疗,用心理学的术语,叫心理干预。
在跟踪的几天里,我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受访者”最后大都对倾听他们诉说的研究生们恋恋不舍。
自杀不过是一个篮子
《方圆》:你在书中不止一次写到城乡之间的对比与转换。城与乡二元对立的话题中,你持何种态度?
孙惠芬:城与乡,确实是我一直在书写的一个话题,最初写它,是我人在乡村而向往城市,后来写它,是我人在城市而向往乡村,但不管在哪里,城与乡都是冲突的。
在这本书里,我依旧表达冲突,不过这里的冲突更混沌、更深刻,我企图思考城与乡在生与死这个人类终极问题中的重量,以及城与乡互为理想时呈现的说不清的困顿。
现代化不可阻挡,如同乡村的城市化不可阻挡,这也正是引我思考和害怕的地方,因为看到了太多疯狂的不计后果的掠夺和拓展。
《方圆》:是否从这些思考中总结出了为什么会有如此庞大的农村自杀群体?你在书中多次提到现代化力量向乡间社会步步逼近,这是农村自杀群体悲剧故事的大背景吗?
孙惠芬:我经常往返在城乡之间,可我以前并不知道我的乡村会有这么多人自杀,中国的自杀率是万分之二十三,居世界第一。而后来树华教授告诉我,中国自杀百分之八十都发生在乡村。
实际上,自杀永远是一个世界性课题,无论亚洲还是欧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任何故事都离不开它发生发展的时代和环境,乡村的自杀,自然离不开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其实是写hUUjN6gcCnOeXeR+WNGQRQ==作的时候,我才发现,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进去,然后,如何出来。
《方圆》:现场调查本来是产生非虚构作品的直接途径,可你却通过这个基础进行小说创作,这种“非虚构基础上的虚构”有何优势?
孙惠芬:只有小说这种形式才能完成在我看来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调查确实让我亲历了一个个现场,但原始的讲述有闪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加上访谈问卷有它自成一体的套路,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这些积累为我的后期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应该说,是这些丰富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有如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象和书写。
我写的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这样既不拘泥,也更自由,并且能更好地表达我企图呈现给读者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不管怎样,在我心里,它就是一部小说。
当代乡下人的心灵救赎
《方圆》:《生死十日谈》写了庞大的农村自杀群体和他们的遗族,在你的叙述中,许多人最后都走向了“一种因社会文化发生巨变而衍生出的虚无之后的情感”——宗教。你如何看待这种寄托?
孙惠芬:我写了一个群体的死者和生者的故事,写了他们受难之后的各种生命状态,但我最想表达的是当代乡下人自我心灵救赎的过程。
当我看到一些受苦的人因为有了信仰而获救,内心会充满喜悦。这信仰不一定只是佛教、基督教,它还在于坚定的自我,在于与大自然建立的坚不可摧的关系。可以说,这是最初促使我写《生死十日谈》的动力所在。而这个发现,如果没有我的长时间“放逐”乡村,没有跟课题组的采访,根本无法做到。
实际上,我写的是乡下人,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而写完之后才发现,它投射出的是每一个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困难、苦难如影随形,在这个变革发展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走在自我救赎的道路上。
《方圆》:你在书中还提到一类逆城市化、反竞争潮的农人——耿春江,但在周围大环境的逼迫下,在血缘亲属“善意的关怀”下,耿春江最终因为他的懒惰性格而死。你之前也说过,你自身在城与乡游走的过程中,当你对人生有着虚无感的时候,你开始欣赏一个懒汉。对这类人,你是持肯定和理解的态度了?
孙惠芬:认同“懒汉”价值观,有这样一个前题,那就是他是不是觉得懒才幸福。耿春江的故事让我看到,一个懒惰的人,无法从奋斗中获得幸福,那么懒惰对于他来说就是一笔财富。因为一个喜欢懒惰的人能在静态的生活中感受到自然的存在、自我的存在。
现实中,大多数人只有通过奋斗才能找到自我的价值和存在。现代社会的压力太大,就是因为持这样价值观的人数实在众多。在这样的现状面前,呼吁“懒汉”价值观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我们应该尊重懒汉的选择。因为人与人之间有太多的不同,每个人都有独属于自己的对于世界的感受。
《方圆》:书中指出“关系的死亡是最后的死亡”。后来你也说过“人如何建立和自然的关系”很重要。你的作品中,有一个同自然建立关系的例子极美,就是那个失去女儿后,干活不要命,“让星月进家”的母亲。这算是一种暗含积极力量的自我救赎吗?
孙惠芬:你说得很好,是这样。那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在人的各种关系里边,和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最可靠、最牢固的关系。
我年少时,因为家乡洪水、旱灾、冰雹等自然灾害频繁,对大自然充满恐惧,所以我那段时间的生活,只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些和神灵之间的关系,没有和山、和树、和自然万物的关系。可有了一些经历之后,加上与自杀的遗族有了深入的接触之后,我看到这里边蕴含着深藏的取之不尽的力量。
《方圆》:陆扬在《死亡美学》一书中认为,自杀的思考是一种迷思,它可能是人生苦难的一种逃遁,是自我意志独一无二的实现方式。你写作《生死十日谈》,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是一致的,对这些案例也持一种理解和感悟的态度。通过这次调查,通过你的作品,你想传达什么样的思想呢?
孙惠芬:在那些自杀故事中,我看到了死者对尊严的捍卫,看到了乡村自杀者和他的遗族在乡村城市化进程中内心的演变。同时我想通过自杀者的死和受访者的生,见证当代乡下人的精神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