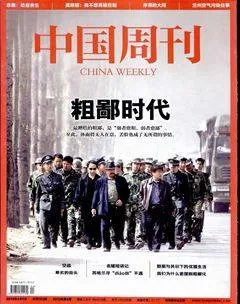“非典”与雾霾
要不是媒体开始隆重地报道,还真没想到,“突如其来”的“非典”竞已到了10周年的时候了。悲剧的是,隆重的10年“庆典”时,雾霾又在困扰着北京人的生活。想来,“非典”与雾霾竞有很多相似之处。
这俩倒霉玩意儿,都是通过呼吸系统侵害人们的健康。只是“非典”病毒直接些,雾霾间接些。
都算“突如其来”。“非典”的突如其来更直接;雾霾虽然是过去十年累积的问题,但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是个“突如其来”的加速度过程。
开始都不认。“非典”最初遮遮掩掩,到公布真相那天,还撤了些官员。PM2.5的普及,更一度被解读为干涉我国内政。
口罩都是这两个事件中重要的道具。“非典”让大街小巷的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雾霾让一部分人戴上了口罩。
都玩跨界。“非典”不是单一的公共卫生事件,雾霾也不是单一的环境问题。这一点就不解释了。
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最大的区别,还是认识的程度。
“非典”是急性传染病,认识不到位立马死人。所以,公众防范意识嗖地提高上去。公共场所,谁不戴口罩,大家恨不得拿眼神杀死他。雾霾问题再严重,对人的伤害也是慢性的。即使空气脏到爆表,街上绝大部分人不戴口罩,校园里小孩子照样上体育课。可是殊途同归,非要搞到发生类似伦敦大雾事件,人们才能正视空气污染,那咱们可真是白经历了一次“非典”。
——吴从龙/北京职员
记者手记
兰州削山引风之梦
去兰州采访前,当地朋友纷纷在微博上、QQ群里报告兰州正在刮沙尘暴。有一位朋友,据我所知至少已连续两年在冬春季躲到海南,就是为了避过雾霾和沙尘。
从北京出发时,雾霾严重,飞机在兰州降落时,再次钻进黑雾之中。我不禁想,也许有一天,当风都刮不走雾霾时,是不是会产生这样一个商机——憋坏了的人们,专门坐飞机到平流层欣赏蓝天,转一圈,过够了眼瘾,再下来。
去兰州市区,沿途满眼是黄土高原支离破碎的砂质土山,除了少部分南方梯田一样的人为植树外。土山没有什么植被覆盖,光秃秃地暴露着。偶尔散落在山脚的民居。瓦房顶上,无不盖着厚厚的一层土。
等走在兰州的大街上,灰蒙蒙的天,隐约能看到白日光,恰如当地人所说的“太阳像月亮一样”。
兰州干燥的空气里,隐约能闻到一股尘土味儿。当地人都受不了,我怎么如此不敏感?难道我已经在北京的雾露中练就了铜鼻子?
当地人告诉我,兰州的沙尘已经刮了整整一周了。我跟沙尘擦肩而过。
地处黄土高原上的黄河河谷盆地,海拔高,气候干燥,年降水少,蒸发量大;尤以南北丽山为主,群山环抱,除了春夏之交狂风带来沙尘外,常年风速小,逆温严重,导致低层空气上热下冷,大气污染难以扩散,冬季雾霾严重。
兰州有石油、天然气,也有煤。但石油、天然气都输送外地去了,当地多年烧煤发电、取暖,喊了几十年转变能源结构,成效微乎其微。
为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当地人打起了山的主意:有人提议将市区东部的大青山削平,让风吹进市区,吹走雾霾;有人提议在南北两山安装巨型电风扇,吹走污染;有人提议在城中的皋兰山山体斜面上,开凿多个深5米到20米、宽50米到150米的沟槽,形成“烟囱效应”抽走污染……
1999年,冯小刚的电影《不见不散》中,主演葛优和徐帆有一段对话。在徐帆抱怨葛优没什么大志向时,后者一本正经地提出“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五十公里宽的口子,引进印度洋的暖风,变青藏高原为鱼米之乡”的设想。
这个说法源自如今身陷囹圄的牟其中,他曾在90年代中期向中央献策。炸开喜马拉雅山,改变中国大西北的干燥气候。
牟其中的点子,现在听起来还是天方夜谭,可是兰州,罩在1996年底,就真刀真枪地实施了削平大青山,打开缺口,引进东风,缓解污染的工程。
不幸的是,政府与开发商的合作出现资金等问题,在进行了规模浩大的迁坟和部分土方工程后,“削山引风”项目演变为旷日持久的官司。
2012年《兰州市“十二五”环境保护规划》再次提出“试点研究实施削山通风工程”。
为了解决空气污染,人为制造沧海桑田。你看看,咱们自己把自己都逼成什么样了。
——焦东雨/本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