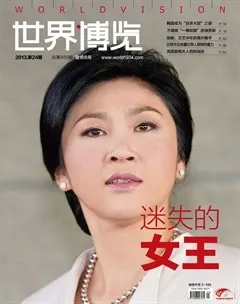张杨:文艺中年的海外推手
乌青色的天空下,伫立着红墙朱栏、飞檐翼角的钟鼓楼。地安门大街纵深外延的中轴线上,早点铺、麻将桌、修鞋匠、在后海滑冰的年轻人,还有开“松花江”给警察敬烟的小货司机。他们随着一位身穿长褂,戴圆框墨镜的老者指尖弹奏的三弦韵律,回环往复。镜头始终跟着何勇的步伐,从银锭桥游走到后海西沿中的每一条胡同。后来看到老人死了,棺木被从院门抬出时,何勇重新又戴上那副墨镜,四周砖墙灰飞烟灭间,他松了松肩膀,低着头,转身走向挖土机的深处。这是张杨在正式导演电影前,为《钟鼓楼》拍摄的音乐录影带。尽管剪辑略显生硬,场景刻板,但是很难想象,那种对家乡早已“心死”的悲悯情绪,早在一九九三年他初次执导自己的独立作品时,便已开始蔓延。
正文:
再次见到张杨,他又黑了不少。从法国戛纳、上海,再到云南,想等他回老家时当面聊一次,实属不易。除非有事要处理,平日里他已经很少再来北京,基本都扎在大理生活,那里令他着迷。这次刚下飞机,他便把我约到丽都饭店对面的一间酒吧里,当时很多人围着他坐着,他嫌太吵,我们就上了二楼去谈。
浓艳的夕阳照在张杨黝黑的脸上,几乎反射不出光晕。他把大眼睛紧紧一闭,用手在脸上捋了又捋后,告诉我,晒的。他看上去有点疲倦,就叫了一杯冰咖啡提神,然后拿出一盒烟,侍者告知二楼是无烟区,他一听就更颓了。我这时才想起拍《爱情麻辣烫》时,他那一头浓密长发,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还有给某矿泉水拍广告,让王力宏为了一个抓水瓶的动作,在片场反复折腾一整天的,也是他。时隔七年后再度面对面坐在一起,他一点没变,包括身上那件宽大的JEEP上衣,和因懒得打理而过长的发鬓,以及毫不世故的亲近感。这令我很容易有一种感觉,太过熟悉,话头一开,彼此就剩下“是是是”了。但当他说起话剧、剧本、摇滚乐和北京城,又实在收不住。很明显,他更适应活在美好的过去时光和纯净的自我内心中,不愿出来。话语和表情,都满是对朋友和身边故事的留恋。更可贵之处,在于他常以温和的姿态去应对各种纷至沓来的生意。对话中,几通电话打进来,能看出他很勉强,但仍是答应。唯一的要求就是“别太早,太早了起不来”,脸上还挂着对方不可能看到的歉意。聊到尾声,一哥们上来笑着催他:有点儿长了吧,下面一帮老板等着你呢,引来邻座几位男女侧目。这一幕又令我想起七年前,他同样说了好多,最后也是被人提醒注意时间,还有事情在等他。和那次一样,他这回知道后,也只是略微点了下头,没做回答,就继续跟我谈了下去,根本不着急。
后来在我离开的半路上,张杨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聊得有些匆忙,再多些时间就更好了。我不知道该回给他什么,也没想好是否要告诉他,七年前那是我的第一次专访,一个问题在嘴里绕了半天都没问出来。我想他能看出来,依旧注视着我聊了很久,根本不着急。
大约二十年前,中国第六代导演普遍开始蓄势发力的时候,张杨显得既不偏执,更不极端。彼时章明(《巫山云雨》)、王小帅(《冬春的日子》)、张元(《北京杂种》)、管虎(《头发乱了》)、贾樟柯(《小山回家》),包括同为北京人的娄烨,大都因为沾了各种“除名”、“封杀”、“地下”等标签事件,获得“先锋”的称号。而此时的张杨,仍在和同学施润玖一起组乐队,跟唐朝乐队的哥们儿张炬,以及张一白、孟京辉混在一起,依旧追着何勇的父亲买鼓,或者在中戏的宿舍安心听张楚弹琴唱歌。直到一九九七年,他才拍出了自己导演的第一部长片。有趣的是,那部作品的投资方是台湾滚石唱片旗下一家电影公司,来内地试水,与西安电影厂初次合作,张杨让他们赚到了三千万的票房。
相较而言,两年后《洗澡》的班底则更加彻底,所有主力演员几乎是一水儿的人艺演员,这使得该片先天就被赋予一种深沉的写实感。那种北京人艺所特有的语言和文学性,首先便如同一枚钢印深深刻在这部电影的剧本上。这也正是张杨最聪明的地方,朱旭、濮存昕和姜武的组合,堪称珠联璧合,丝丝入扣,加上何冰、李丁、封顺等新老演员的极力衬托(封顺先生在出演完这部电影后去世),做导演的自然省却不少力气,不用为表演分心太多。
《洗澡》在格局上,依旧延续了人艺戏剧舞台上《茶馆》、《王府井》这样的经典展现方式,用一家虚拟的“清水池”澡堂,描绘出世纪末的北京城,在古老的生活传统与当代都市节奏中的碰撞。其实就连这种母题,也都是人艺历史上,最为常见的一种选材,并不新鲜。但张杨竭尽所能将这种碰撞,表现得更为温润,并且用一个“傻子”,来勾兑各种暗自涌动的内部情绪和外在压力。显然,只从这部电影里,“清水池”之外的社会变动,观众是看不到的,全被导演砍了去,这也是他在取材时,最为机巧的一面。
从整体上看,《洗澡》也是张杨历年作品中,完成度最高、最为平衡的作品,甚至可以说,只论导演的作用,这部电影应该是他的一部顶峰之作。一个有趣的细节,朱旭扮演的父亲一角,是在影片进行到刚好一小时的地方去世,分毫不差,这个细节足以说明张杨在剪辑该片上,是多么地遵从商业规律。而正是该片,令他一举拿下第二年的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海外版权同样卖得非常漂亮,他配得上这个荣誉。但同时我们仍应该注意到站在影片幕后的功臣们,这部电影依旧由滚石集团总经理段钟潭掌控大局,而《洗澡》的策划Peter Loehr已经完全用上了自己的中文名罗异,他的身份也变成了CAA 的中国区总经理(Creative Artists Agency,创新艺人经纪公司,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人才经纪代理公司)。彼时他将这部电影带到多伦多、圣塞巴斯蒂安、德塞隆尼基、鹿特丹四个国际电影节,拿走五个奖项,并且卖了五十六个国家。
两年之后《昨天》上映,张杨同样在影片后半段,令主角被家人安排进一家精神病院。只是他没有再让贾宏声像姜武那样挣扎,相反,那是一种煎熬。精神病院对他只是一个反思本我的道具。张杨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将最意识化和先锋派的艺术形态,完美地糅合进寻常大众的认知范围与实际生活常识中,从未脱离。可见张杨对电影的整体掌控和技巧运用,要聪明许多。他将表现风格死死按在自己熟悉的电影语境中,每个人都能看到,小卖部的红字招牌、蓝色的空调公交车和绿色的警察制服,组成了这个城市最标志性的颜色。最令观者感同身受的,是那时候谁家都难免会有个六亲不认的青皮,只是没人愿意去过问,这个人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看过这三部电影的人,可以留意一下,张杨的演员在这些作品中,都有哭泣的场景。他们哭的理由和方式,不一而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真挚,打动人心。而《昨天》之后的一段时间,仿佛就是一道分水岭,如此残忍与温情相互糅杂、掺混的瞬间,似乎都难以再寻踪影。不论是五年后才问世的《向日葵》,还是赵本山又唱又吆喝的公路片《落叶归根》,包括后面再度回归都市题材的《无人驾驶》和《飞越老人院》,那股含在胸口的锐气,以及点到为止,却足以触及魂魄的力道,仿若完全被磨平了。这也造成此前一直追着张杨看过来的一批死忠,十年来有些发懵,那个平静中总会灵光乍现的北京摇滚范儿导演,他还会再回来么?
Q&A
黄小邪:你的父亲拍过《神秘的大佛》(张华勋导演),母亲是人大教师,你学中文、拍电影,受到家庭的影响有多大?
张杨:我爸拍《神秘的大佛》时是八十年代,我十三岁,暑假跟着去玩,在他电影里露了一个背影的镜头,后来拍《武林志》也跟着去玩。因为我们院都是北影的,北影院。上初中的时候,有一个电影叫《马可·波罗》,我爸的同事他们做副导演,就把我和他儿子都选上,里边演忽必烈的皇孙什么的。那次在剧组里待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拍了一个多月,而且是上学请假去的。演过电影,在学校里边还是挺出众的。所以实际上就是家庭的氛围使我从小接触到很多关于电影的东西,自己当然也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因为我爸妈他们经常在家里聊关于电影的事、聊剧本。他们的一些朋友来,我那时候小,初中、高中,也不会插话,但是隔一个房间也会听。但是我爸妈其实并不希望我从事电影,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在“文革”受迫害比较多,所以他们的概念是,基本上每次政治运动,文艺工作者都是最先受到冲击,而且也逃不掉,都是牺牲品,所以希望我学理工科、学医,即使是学文科,也该考政法大学或者新闻类学校。我上学的时候理科还不错,但是我自己在高二的时候就明确了,还是想奔电影去的。分文理科的时候,我选择了文科。
黄小邪:你的许多电影作品里,都有对父子关系的展现,虽然足够细腻而温和,但真实感极强。这与你儿时在片场的成长关系大么?父亲的导演形象对你是否有很强烈的冲击?或者你那时会幻想将来要做一个像他那样的导演么?
张杨:小时候作为一个小演员,更多是好玩,对导演没有那么强的概念,只是觉得剧组里是导演说了算,大家都听导演的。高三毕业,我明确了要去学电影,我们家倒也支持了。但是因为八七年那一年电影学院没有招生,只有中央戏剧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招生,所以我爸就带着我去找他的大学同学,空政话剧团的一个戏剧导演,让他给我辅导。大概准备了三五个月,主要就是诗歌朗诵、影片分析。以前我们住在电影厂的好处就是看过很多参考片、内部片。高中时就有机会看过苏联电影回顾展、西班牙电影回顾展、日本电影回顾展、瑞典电影回顾展,每一部电影我都会去写一篇影评,实际上当时可能也没有影评的概念,就是写一篇观后感。这些东西是考试必备的。然后就是讲故事、演小品。考试时,我觉得考得还可以,结果没被录取。后来我爸妈说你还是先报个中文系吧。将来你有文学基础,哪怕从编剧开始还是可以再转当电影导演。所以当时报中文系,也是为了将来有机会再回过头。当时还是分配制,想着也许将来能分到北影厂的编辑部,所以就上了中山大学的中文系。
黄小邪:当你真正接触到电影,具备独立导演的条件时,真正在这个领域里给你实质性帮助或者说给你启发的是谁?
张杨:在中大,因为不务正业所以我看了很多闲书,这是很好的基础,文学的基础。上中戏后,那时候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摇滚乐最活跃的时候,我们这拨年轻人实际上是最早受摇滚乐影响的。我和施润玖做乐队,都是从头学起,五音都不全,还天天在宿舍里乱弹,完全就是噪音一样。孟京辉、张一白、蔡尚君、刁亦男,他们在做诗社、文学社。原来互相看不上的两拨人,后来慢慢走到一起,互相发现其实都是有创造力、有想法的。到快毕业那一两年,这拨人成了中戏非常重要的力量,做了非常多的实验戏剧,也影响到周围其他人。大家每人排一到两个戏,形成一个演出季,学校实际上并不支持。但是这帮人就走得比较靠前,而且思路都比较荒诞派。今天,孟京辉已经走到戏剧的前列,我、张一白、蔡尚君、刁亦男、施润玖,都成了电影导演。对我来说,那个时期是很重要的一个成长部分。我爱上戏剧,觉得戏剧还是很有表现力,甚至有时候我觉得戏剧比电影的空间还要广阔、还要深入。它跟人灵魂接触的东西更紧密一点。然后又热爱摇滚乐,发现摇滚乐更接近自我内心的很多东西。
有一年,电影学院的老师来讲课,郑洞天、周传基、刘诗兵……这一年的电影课其实也很重要,通过电影分析课看了一些片子,通过录像带也看到很多老片,法国电影、德国电影、美国电影、日本电影。中戏时代让我学会了看电影,学会怎么去理解一部电影、怎么去评判一部电影的好坏。慢慢地,电影看多了,就会有一些自己的喜好,自己认同的东西。关于电影的很多观念,实际上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我们那批确实比较喜欢法国电影,包括特吕弗、戈达尔的;还有欧洲大师伯格曼、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的;然后就是日本黑泽明的;中国台湾侯孝贤、杨德昌的,包括蔡明亮的《爱情万岁》,其实都是在那个年代看到,受到的冲击还是非常大的。
黄小邪:一九九七年,你与Peter Loehr一起弄了《爱情麻辣烫》。这个过程还挺复杂的,当时跟滚石与西影厂下面的公司合作的,是吧?
张杨:那个年代论资排辈,比如在北影厂,先从场记开始,做几部片的场记、再几部片的副导演,然后才能做导演。等自己拍电影,至少得是十年以后的事了。所以我不想走他们那路,但是刚开始,别人不可能给你电影拍,那时候也没有社会的民营公司投资。于是我拍了两年的纪录片,那时候和一个台湾的电视台合作,拍一部片名叫《中国》的东西,还和凌峰跟他弟弟拍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全国各地地跑,在云南、青海、甘肃,拍很多这种我自己喜欢的选题。
只要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我就拿着仪器拍去了,非常自由而且也不存在什么审查的问题。只有自我审查,自己拍完自己弄完了看,再送到台湾那边去播。那两年对我非常有意义,我也拍了北京地下摇滚乐队的一些生活,后来就拍MV,何勇的、艾敬的,也有从中央台接的活。在这个过程里,我也给我爸当副导演,他有一部电影叫《铸剑》,我当的执行导演。差不多有五年时间,基本上我都在做这些杂的,拍MV、拍纪录片,当副导演,后来自己慢慢觉得,老这么一直拍下去吧,没有自己东西,没有作品,怎么办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自己写剧本。我花了一年时间写了一个剧本,九四年写完。然后就到处找钱,一直到九六年,
遇到这个Peter Loehr(罗异)。当时台湾滚石在内地成立一家公司,他从台湾来到内地,特别想做电影,在电影学院学了一年中文,学完了,就想开始做电影。但是那时候他也不认识人,他就满世界找有可能合作的导演。他在滚石那儿看到我给何勇拍的《钟鼓楼》,很喜欢,就约在一块见面了。我把我的剧本给他,那一年他看了很多剧本,我这剧本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他就觉得这个导演有很多想法,所传达的理念和概念和他非常接近,我们互相磨合了一段时间,就决定了他来做制片人,他投资,我们合作。
我一直觉得第一部电影,我原来写的那个故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在那个年代,那个结构非常新颖,三个不同身份的人的故事,一环扣一环,从一个故事进入另一个故事,而且三个人的名字都叫张杨。三个不同的张杨,每个都串在一起,很好玩,但是里面写到的摇滚青年的生活、专门卖盗版DVD的生活,没能过审。我当时想,电影必须得见观众,得在中国能放映,那么什么题材比较好过、有突破口?就从爱情故事开始,爱情故事基本上没什么社会批判,从这个角度进入会比较好一点。当然我又不太喜欢那种简单的偶像电影,所以就想了关于爱情年龄的几个小故事。当年帮我写故事的几个编剧都是我的大学同学、好朋友,今天这些人都成导演了,像刘奋斗、蔡尚君、刁亦男,这三个人现在都是导演,在那个时候我们是一个很固定的团队。
黄小邪:在这方面Peter似乎对你的题材把控得非常准确,你们两人的“张罗”组合在圈内一时被传为佳话。这么多年,他对你最实质性的帮助在哪?
张杨:最关键的其实就是商业运作,因为选什么题材、拍什么题材是我决定,Peter不会反对,他只是尽他的力量去帮助我。Peter最严谨的部分是,他是一个很好的制片人,他解决了外围很多的事。投资有了,剩下的就是怎么去制作一部电影,需要严谨的时间、严谨的制作过程,包括将来怎么卖片子、怎么去发行。这些我不清楚,他也是摸索,但是他就会拎着拷贝全中国到处跑,所以你看当时《爱情麻辣烫》发得非常好,《洗澡》在全世界也发得非常好。Peter在发行上亲力亲为,而且好多现在看很不稀奇的方法,在那个年代都是非常新的,实际上Peter在电影的宣传方面,引领了很多东西。他在《爱情麻辣烫》时尝试了很多东西,包括地铁里的广告、发QYSLSi1hwBJ1v8hRnoK16cn2LLGoxmC8/AYtlD5q7wo=行原声的同名音乐唱片、在情人节档期上映……在制作电影和发行电影方面,Peter给了我最大的帮助,我没有在这方面操多少心,我只是配合怎么去宣传而已,我更多的精力就是放在创作上,即弄剧本、拍电影、剪接电影。
黄小邪:他就完全不插手内容?
张杨:内容方面,我们更多是在剧本阶段讨论和在剪片阶段讨论,这是必须的。我俩经常剪片子时会吵得一塌糊涂,长点短点,或者哪个地方要干嘛,删或者留。比如《爱情麻辣烫》结束后,我最开始想的《洗澡》是另外一种,实际上有点类似于《爱情麻辣烫》的结构方式,是四个故事组成的一部电影,选择一个北京的洗澡的故事、一个西藏的洗澡的故事、一个陕北的洗澡的故事和一个哪的什么洗澡的故事。当时其实是把洗澡作为一个像论文一样的研究课题,想通过几个不同的故事去诠释洗澡这个概念。说到底是灵魂之间的某种概念,就是自己去洗清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是主题先行的。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它的问题就在于,都不扎实,可能都没落到实处,所以最后就慢慢落在一个真正实在的,我们最熟悉的故事上,就是一个在北京发生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小时候和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接触的澡堂子的故事。原来想的西藏的、陕北的,后来也都作为小故事搁在电影里边,但实际上最关键的就是,我心态的变化,我明白了要把电影落在更实在的人物关系上,更多细节,更踏踏实实去讲一个故事。
黄小邪:这是Peter给你的建议吗?
张杨:没有,我自己,我在过程里寻找。因为我们那几个编剧,实际上就是我基本上确定一个方向,但是我的这些朋友们,这些编剧的朋友们在这个过程里边也会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他们也会不断地帮我去修整,就说他会觉得哪些东西是好的、不好的,我们在过程当中也会进行很多这样的讨论。因为这东西一定是你自己生活的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熟悉,我觉得表现起来也会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