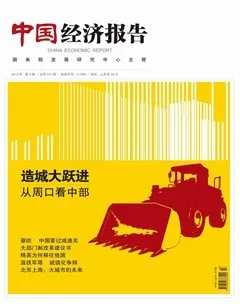国王的餐桌

餐桌既是国王拥有权力的象征,也是政治家展示手腕的场所。哪些人一起用餐、宾客的座位、宴席上的菜品,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寓意。
在《权力的餐桌》里,仔细研究“餐桌政治”的法国学者让-马克·阿尔贝说:“国王和属民建立关系要通过很多途径,其中之一就是饮食……今天的国家元首代表国家,他的行为必须与国家合拍。吃饭的时候,他既不能狼吞虎咽,逞一个饕餮的威风,也不能吃得过于简单,那样给人的感觉好像一个过于寒碜的糟老头子。”
吃什么,绝不是个人喜好那般简单。从人类漫长的关于吃的历史中,你能看到的不仅是美食,更有政治,或者说,权力的变迁。
古希腊的斯巴达和克里克岛,年轻人出席聚会,表明他具有了公民权;中世纪的骑士们在授衔后聚餐,以示群体之间的团结信任;巴士底狱的监狱长曾经邀请围攻监狱的群众代表一起进餐,以图给“革命”留有商量的余地;美国餐桌上的德国泡菜,曾被改名为“自由卷心菜”;萨科奇在20国峰会晚宴上迟到,成了一件国家大事;为赢得更多草根选民的支持,奥巴马在白宫的花园里畅饮啤酒……
餐桌既是国王拥有权力的象征,也是政治家展示手腕的场所。哪些人一起用餐、宾客的座位、宴席上的菜品,都有着强烈的政治寓意;在不那么奢华却气氛融洽的宴会上,两个著名的老饕——赫尔穆特·科尔和弗朗索瓦·密特朗,平息了法德这两个欧盟大国可能出现的紧张关系;乔治·布什用法国炸薯条、雅克·希拉克用加利福尼亚红酒,巧妙填平了美法之间的隔阂;英国农业大臣约翰·格默在“疯牛”闹得正欢之时,让女儿在摄像机前大嚼三明治……
当然,不是所有掌权者都对气派非凡的宫廷宴会感兴趣,比如拿破仑,这位矮个子的法兰西帝国统治者,就更愿意和士兵们一起分吃土豆。一个习惯于站着狼吞虎咽,随便擦手指头——不是在桌布上擦,就是往自己衣服上抹的人,肯定对繁琐的宴会礼仪深恶痛绝。约瑟芬皇后坚定地站在了丈夫一边,按照刻薄者的说法:“这个长着蛀牙的克里奥人,企望遮盖上她那口难看得可怕的坏牙齿。”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餐桌政治”的偏爱。
“把饭菜弄得像样一些,你们要挣一个花两个,不够了去借,我最后结账。”——他对自己的外交大臣塔列朗说。这恰恰是后者最擅长的事情。有人问塔列朗:怎么才能在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上,为法国争得更多的权利?这位谙熟“餐桌政治”的幕僚回答:需要更多炖锅。
在法国大革命时代的各种斗争中,塔列朗是独一无二的不倒翁。从路易十六的朝廷,到督政府时代、执政府时代、拿破仑帝国,一直到复辟后的波旁王朝和路易·菲力普的君主立宪政体,他都以各种宴请,换取了自己辉煌的政治生涯。
御厨安托南·卡莱姆需要适时登场了,他可是“餐桌政治”不可或缺的帮手。
英国演员兼作家伊恩·凯利,为我们讲述了这位第一名厨的故事。妙趣横生的《为国王们烹饪》,可以看作是《权力的餐桌》的典型案例和趣味解读。
尽管“政治变色龙”塔列朗并不讨人喜欢,不过,凯利说:“即使原先厌恶他的人,在见过他本人,尤其是享用了他家的厨师安托南的宴席之后,很少有人会再讨厌他。”
安托南服务过的君王包括法国皇帝、英国摄政王、俄国沙皇——他既是国王餐桌的缔造者,也是权力政治的见证人——甚至有人说,退位谈判前,他曾替塔列朗给俄罗斯外交官暗送照会。
支配国家命运的大事,就这样在餐桌上解决,连拿破仑退位也不例外——东征俄罗斯的失败,使得他不得不放弃统治权。那个改变法国政局的夜晚,使节们频繁进出外交大臣的官邸。拿破仑派来的秘使在二楼与沙皇谈判,为他的继承人罗马国王争取摄政权;塔列朗与代表波旁皇室的维托尔男爵在楼下会晤。进退维谷的沙皇迅速寻找着对策,他并没有把酒杯举向权力相争的任何一方,反倒建议为厨师之王——安托南敬酒。
两个大人物,一个台前,一个幕后,配合娴熟,相得益彰,共同演绎着美食与权力的共舞。
国王的餐桌上,美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吃。从古至今,不管是国王还是元首,都在通过饮食传达自己的政治信息。即使在健康备受关注的现代民主国家,如果哪个政治家不能喝酒,或者“吃不动”一桌丰盛好菜,依然不受选民喜欢。食品与权力的关系就这样密不可分。“欧洲选举中,布鲁塞尔成了所谓消毒厨艺的游说场所。同样,对于食品的恐惧,不管是事出有因,还是空穴来风,都经常成为政治家的工具……食品成为政治讨论的中心,在‘劣质食物’和转基因的问题上,或涉及桃红酒地位的时候,食品就是政治”。
不过美食的制造者——御厨们在意的只是他们的烹饪艺术,并且不惜为此献身。
安托南最终死于慢性一氧化碳中毒,被“他天才的火焰和烤肉的木炭烧成了灰烬”。摩根夫人说:“和厨师瓦泰尔一样,安托南由于巨大的精神焦虑和身体的极度疲乏,将死于荣誉战场上。”
在为路易十四烹制宴席时,瓦泰尔发现准备的海鲜数量不够,极度焦虑恐慌而自杀。那些让他“丢尽脸面”的鱼,在他拔剑自尽时,其实已经送到。
权力的餐桌依旧延续,美食也在代代相传。安托南烹饪书里的那些菜品,对于21世纪的美食爱好者过分奢侈。然而,“他的灵魂仍然在最简单的、最纯洁的沙司上徘徊,在巴黎糕点店布置精致高雅的玻璃窗里徘徊。”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