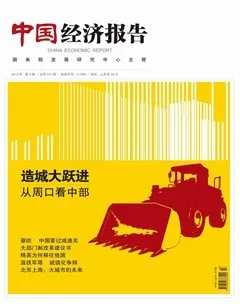学习印度人如何争鸣

“想让我们沉默不难,但那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说这话的,并不是哪位专家学者,也非哪位“意见领袖”,而是一位目不识丁的印度农民。印度人爱说话,爱争鸣,这是阿玛蒂亚·森在《惯于争鸣的印度人》一书中向读者展现的印度人。
半个多世纪以前,时任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的克里希纳·梅农在联合国滔滔不绝地演讲,创造了9小时不停顿的记录。这个记录本来是有希望被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打破的,可惜他一病不起躺在了古巴的医院,所以,只能指望话痨界再出一位旷世奇才来打破这个记录了。
不过,按阿玛蒂亚·森的说法,长篇大论并非印度人的新习惯,而是有悠久历史的老传统。古代梵语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总被人用来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相提并论,但就其长度而言,仅《摩诃婆罗多》就是后两者合在一起的7倍。由此可见,喜好争鸣和惯于争鸣,在印度有着厚重的历史传统。
争鸣的传统塑造了印度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特质,阿玛蒂亚·森用一双慧眼,发现并证明公众争鸣与印度民主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些人常常以“国情”、“特殊性”来否定和排斥普世价值,而作为印度的民主,虽然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和渗透,但它既不能被西方所遮蔽或者垄断,也不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民主就是让公众讲道理”,仅从争鸣而言,但凡一个民族有擅于争鸣的传统,这个传统都有可能孕育民主。
希腊和罗马的公众议事遗产当然久负盛名,但印度的公众审议(也可译为慎议、协商)也不遑多让,就连征服世界的亚历山大大帝,遇到一群耆那教哲学家后,也是束手无策,只能任凭教诲。阿玛蒂亚·森本意不在于炫耀他的祖国的光荣历史,而是试图说明,民主以及争鸣的传统,不仅西方人喜欢,东方人也喜欢,它不能被打上西方的标签,然后垄断其专利权。
当然,阿玛蒂亚·森所要展现的,也不是争鸣的技巧和论辩的成果,而是如何争鸣,如何在论辩中体现出宽容,如何为争鸣立规。他介绍了印度历史上四个伟大人物:阿育王、阿克巴、泰戈尔和甘地,以他们为例,梳理了这个国家自由表达与充分宽容的精神源流,这个精神财富如何对印度政治产生正面影响。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孔雀王朝的第三位国君阿育王,他通过弑兄而得到王位,并发动了残酷的征服羯陵伽国的战争,建立起古代印度的最大帝国。但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带给他沉重的精神负担,终于他幡然醒悟,决定改变国策,奉行“正法”,于是皈依了佛教。当时的印度,教派之争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阿育王虽然信奉佛教,但并没有将自己的信仰强加于国人,而是矢志确保公众议事能够在没有敌意和暴力的情况下进行,并以诏书的形式,为各教派的争鸣定下规矩。比如,他要求“言谈有节,不得于不当场合溢美自家教派或贬低其他教派,即令在恰当场合,言辞亦当适度,每一方均应充分尊重其他教派。”阿育王的“规矩”,不是压制言论表达,而是鼓励言论正常表达。他的这项议事规则,不仅比19世纪的“罗伯特议事规程”要早,而且更能体现出民主精神。
阿育王捍卫公众议事之举在后来的印度历史上一直产生回响。两千多年后的印度莫卧儿皇帝阿克巴,就倡导并支持不同信仰的人之间进行对话。作为一位穆斯林统治者,他诚恳邀请各派宗教学者到他的宫廷,倾听他们的说教。他还将不同教派的领袖人物召集在一起,辩论和研究各种宗教和社会问题,以辨明同异,消除误解,进而摆脱宗教矛盾,求得社会和谐。
印度人喜好争鸣,就意味着存在一个相对宽容的社会环境。正如葛维钧先生所言,多元社会存在的长远意义,即在保证了通向近现代世俗主义政体的道路可以畅通,允许表达不同诉求,乃是民主政治得以建立的基础。
《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只是这本同名论文集中的一篇,也许是最具有纲领性质的一篇。其他的论文,沿袭了作者的一贯风格,为我们了解印度人的历史、文化和身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作者为文史学者、深圳报业集团主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