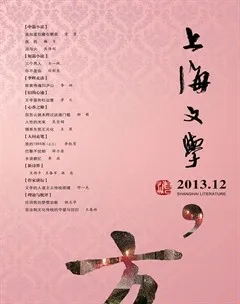宗法制文化传统的守望与回归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长篇小说的创作异常兴盛发达,尤其是从1993年“陕军东征”始,中国作家就已经把极大的创作热情投注到了长篇小说这种文体之上。正因为有着众多作家的积极参与,所以长篇小说之成为当下时代中国小说界的第一文体,就是无法被否认的一种创作现象。既然是最重要的小说文体,那么,长篇小说创作某种程度上也就具备着一种风向标的意义。许多时候,通过对于长篇小说创作的观察,我们可以洞悉中国文学界一些思想艺术变化迹象的发生。只要对一批透视表现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比如贾平凹的《秦腔》与《古炉》、铁凝的《笨花》、葛水平的《裸地》、马旭的《善居》等作品稍加留心,敏感者就不难从中发现一种旨在守望回归宗法制文化传统的创作趋向的出现与形成。
必须看到,长篇小说中对于宗法制文化传统的肯定回望式表现,经过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在更早一些时间出现的《秦腔》与《笨花》中,作家还只是凭借自己的艺术直觉意识到曾经被排斥的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尚且没有明确地为宗法制传统张目。先来看贾平凹的《秦腔》,这部曾获得过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直逼当前中国乡村现实生活。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当下中国乡村世界凋敝破败状况的真切再现,二是为日渐衰落的中国传统文化谱写了一曲饱含深情的挽歌。小说题名为“秦腔”,喻指的也正是第二层意思,也就是说文化挽歌这条线索贯穿了小说的全部。在文本中,我们可以从与秦腔密切相关的白雪和夏天智身上看到明显的痕迹。白雪是秦腔女演员,夏天智曾担任过学校校长,在乡村世界中,属于一位知识分子形象。而且,这两位与秦腔渊源颇深的人物形象,还曾经是公公与儿媳妇的关系,只不过白雪后来与夏天智的儿子夏风离婚了。
白雪对秦腔的喜爱,主要出于其所从事的职业,带有更多的感性色彩。相比而言,夏天智的整个生命都是与秦腔缠绕在一起的。他一生酷爱秦腔,对秦腔十分痴迷与投入。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夏天智对秦腔的一往情深,带来的却是一次次失望和败退。他虽迷恋秦腔,虽可以利用父亲的权威命令夏风,以便出版自己的秦腔脸谱集,但却既无法阻止白雪与夏风婚姻的最终失败,即便连王老师想出一盘唱腔盒带这样看似卑微的愿望,也无法满足,由此,秦腔最终的失落与衰败命运也自是不可避免了。
从象征层面上来看,贾平凹在小说中倾力描写的秦腔,无疑是隐喻着一种传统文化。而夏天智,这个秦腔所孕育出来的文化精灵,则是在中国乡村世界绵延日久的传统文化的化身。并且,他还无意中充当了乡村社会传统道德精神权威的角色。在清风街的日常生活中,夏天智的为人行事总是恪守体现着扶危济困的传统道义——他对秦安的关心匡扶,对那些贫困孩子的资助等善举,无一不是在强化着他作为传统道德精神载体所独具的人格魅力。
然而,夏天智对于传统道德精神的坚持与恪守并没有让清风街的乡村秩序朝向他所期望的方向。相反,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道德日益败坏,物质与金钱越来越成为人们追逐的对象。首先是夏家的下一代人,特别是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常常因赡养老人等家务事争得不可开交甚至大打出手。其次是为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丑恶现象开始在清风街上蔓延,并愈演愈烈。第三,则是夏家过春节时各家轮流吃饭的传统的最终消失。这个虽看起来无伤大雅的传统,却承载着夏家多年以来形成的家族和睦、尊老爱幼的家风。如果说秦腔的失落衰败象征着传统文化的崩溃,那么夏家的败落乃至分崩离析就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传统道德精神的崩溃。事实上,这两者本是不可分的,它们都从不同的向度上喻示着乡村社会的解体。而夏天智的死亡,便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标志。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不归,通过夏天智悲剧性人生的描写,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贾平凹内心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真诚向往,正因为如此,他才要在《秦腔》中为其消逝谱写一曲感人至深的文化挽歌。
铁凝的《笨花》也是如此。在小说中,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有着同样的认同与肯定。铁凝在小说题记中道:“笨花、洋花都是棉花。笨花产自本土,洋花由域外传来。”如果仅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铁凝是在说棉花,但若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所谓的笨花与洋花,未尝不可以被看作是中西不同的文化传统的隐喻式表达。尤其是在当下,西风强劲,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一步步蚕食,在这样一种情势下,铁凝之所以强调笨花、将笨花与洋花并举,显然意在凸显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价值的重要性。这一点,在向喜和向文成父子身上体现明显。
向喜是《笨花》中一位塑造相当成功的旧军人形象。他幼年时曾读过《孟子》、《论语》,尤其是《孟子》,对他的影响很大。儒家文化已深深地植根于向喜的人生观、价值观当中,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向喜的一生,所秉承遵循的也正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原则。比如他为自己特意选择的字号“中和”、“谦益”,比如他敢于违抗顶头上司的意志,拒绝执行监督枪杀一千二百余名士兵的命令,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抗战爆发后,向喜限于特定身份,被迫隐忍自保,无意介入这场战争。可无论他怎样低调,也不可能完全自避于时代风云之外。当日军士兵逼上门来,欲加害一位素不相识的卖艺者,向喜终于忍无可忍,毅然决然地将自己的枪口对准了残暴的日军士兵。
“是什么原因使向喜举起了粪勺?是他听见了玉鼎班和施玉蝉的名字,还是他听见日本兵骂了他‘八格牙路’,还是他又想起了保定那个小坂?也许这些都不是,也许就是因为日本人要修停车场,铲了他保定双彩五道庙的那块红萝卜地吧。”是的,向喜之所以反抗,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日军铲了他的萝卜地这一原因,却不得不令人深思。在这里,红萝卜地是中国人宁静的日常生活的象征,而日军铲除萝卜地,也就打破了这种宁静和安详,这恐怕是包括向喜在内的无数中国普通民众殊死反抗的真正原因所在。日本人铲掉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红萝卜地,而是他们的尊严和正常的凡俗生活。就这样,向喜由置身事外、明哲保身的旧军人最终转变定格为一位坚决的反抗者。由此,儒家文化所倡导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最高精神境界,在向喜这一人物身上得到了近乎于完满的艺术表现。
在《笨花》中,与向喜形象相映生辉的另一个人物是向文成。在小说中,向文成是一个朴实、聪慧而又厚道的、急公好义与扶危助困兼而有之的正义者形象。无论是在平素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战争爆发后紧张的非正常生活中都是如此。可以说,向文成是中国乡土社会所孕育出的一位集传统美德于一身的人物。向文成的一生中并没有什么可歌可泣、惊天动地的伟绩,有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累积起来的平常小事。然而,正所谓集腋成裘、聚水成河,正是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平常小事中,向文成秉承着民族道义与美德的那种仁者爱者形象,才愈发地清晰起来、愈发地真实可信起来。
某种意义上,正是因为有了贾平凹与铁凝他们最早在《秦腔》、《笨花》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性书写,才为后来一些长篇小说更加集中地思考表达宗法制传统的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可能。说到宗法制传统,就必须注意到,宗法制传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特别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关于中国宗法制长期存在的奥秘,曾经有学者进行过深入的描述研究:“群体组织首先是以血缘群体为主,因为这是最自然的群体,不需要刻意组织,它是自然而然地集合成为群体的。先是以母氏血缘为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是以父系血缘为主了。以父系血缘为主的家族,既是生产所依赖的,也是一种长幼有序的生活群体。它给人们组织更大的群体(氏族、部落直至国家)以启示。于是,这种家族制度便为统治者所取法,成为中国古代国家的组织原则,形成了中国数千年来家国同构的传统。”“文明史前,人们按照血缘组织与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好理解,为什么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统治者仍然保留甚至提倡宗法制度呢?这与古代中国统治者的专制欲望和经济发展有关。自先秦以后,中国是组织类型的社会,然而,它没有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没有从朝廷一直组织到个人,朝廷派官只派到县一级,县以下基本上是民间社会。因为组织社会的成本是很高的,也就是说要花许多钱,当时的经济发展的程度负担不了过高的成本。保留宗法制度,就是保留了民间自发的组织,而这种自发的组织又是与专制国家同构的,与专制国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而且占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恰恰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映”(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按照王学泰的分析描述,宗法制传统在中国有着可谓源远流长的漫长历史。正因为宗法制在中国乡村世界曾经存在传延多年,所以自然也就积淀形成为一种超稳定的社会文化结构。
需要看到的是,或许与古代中国乃是一种农耕文明特别发达的国度有关,这样一种宗法制传统主要存在于广大的乡村世界当中。尽管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性转型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使传统中国变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或许是因为城乡差异的缘故,如此一种强劲有力的现代性思潮却一直未能对乡村世界的宗法制生存秩序造成根本性的撼动与改变。这一点,在《古炉》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朱大柜是古炉村的村支书,自土改开始,他就在村里一言九鼎,他的话就是圣旨,他的行为永远正确。但在他成功的乡村统治背后,家族力量的存在与支撑恐怕是他所依恃的一个重要因素。设若没有了朱姓家族势力的强势存在,在古炉村,面对夜霸槽这样的挑衅者,单凭朱大柜的一人之力,要想巩固自己的地位,恐怕还是不大可能的。而朱姓家族势力的存在,正是宗法制传统的具象体现。
然而,尽管在《古炉》所具体描写的1960年代中期,在类似于古炉村这样的西部乡村,还残留着宗法制文化传统,但到了当下时代的中国乡村世界,如此一种带有强烈民间自治意味的宗法制社会传统,实际上却早已经荡然无存了。在这里,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如此一种已经进入超稳定状态的社会文化结构,在成功地抵制对抗所谓的现代性数十年之后,为什么到现在居然荡然无存了呢?从根本上说,真正摧毁了乡村世界中宗法制社会文化传统的,恐怕正是以执政党为主导的自从“土改”之后一波未止更强劲的一波又至的政治运动。当然,在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这些政治运动也可以被看做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被称之为“革命现代性”。但是,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毕竟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革命现代性”的暴力性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这里才更愿意把二者剥离开来,直截了当地把“革命现代性”称之为政治运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一部《古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上也正是“文革”这样一种极端的政治运动如何蚕食摧毁乡村世界宗法制社会的过程。
对于乡村世界宗法制文化传统的被摧毁,孙郁曾经进行过精辟的分析:“若说《古炉》与《阿Q正传》有什么可互证的篇幅,那就是都写到了乡下人荒凉心灵下的造反。这造反都是现代的,自上而下的选择。百姓不过被动地卷入其间。贾平凹笔下的夜霸槽与鲁迅作品的阿Q,震动了乡村的现实。当年鲁迅写阿Q,不过展示奴才的卑怯,而贾平凹在古炉村显现的‘文革’,则比阿Q的摧毁力大矣,真真是寇盗的洗劫。乡间文化因之蒙羞,往昔残存的一点灵光也一点点消失了。这里有对乡下古风流失的痛心疾首,看似热闹的地方却有泪光的闪现。中国乡土本来有一种心理制衡的文明形态,元代以后,战乱中尽毁于火海,到了民国,那只是微光一现了。《阿Q正传》里的土谷祠、尼姑庵与《古炉》里的窑神庙、窑场,乃乡土的精神湿地,可是在变动的时代已不复温润之调。到了1960年代末,只剩下了蛮荒之所。中国的悲哀在于,流行文化中主奴的因素增多,乡野的野性的文明向不得发达,精神之维日趋荒凉了。但那一点点慰藉百姓的古风也在‘文革’里毁于内讧,其状惨不忍睹。中国已经没有真正意义的民间,确乎不是耸人听闻。从鲁迅到贾平凹,已深味其间的苦态”(孙郁《从“未庄”到“古炉村”》,《读书》2011年6期)。很显然,孙郁这里所谈论的“古风”、“民间”云云,正与我们所强调的宗法制社会文化传统其义相同。因此,说到《古炉》开头处狗尿苔摔破那件青花瓷的具体象征寓意,恐怕就只会是孙郁所一再申说的“古风”与“民间”,只可能是我们所强调的宗法制社会文化传统。
阅读葛水平的《裸地》,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形象,就是那位出现在暴店镇的传教士米丘。在一部旨在书写表现20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为什么一定要在一个洋人身上耗费笔墨呢?我想这与小说想要表达的主题有关,也就是盖运昌最终没有子嗣的文化象征意味。《裸地》中故事所发生的时间,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这个历史阶段的暴店镇,实际上正处于我们前面已经强调过的现代性对于中国宗法制传统形成冲击的一个时期。一方面,以乡绅盖运昌们为代表的乡村自治传统还在有效地运转,并在实际上操控着暴店镇的社会存在局面。但在另一方面,这种立基于宗法制之上的乡村自治传统却也已经明显地受到了现代性的强烈冲击。在这个层面上,那个洋人米丘,显然就应该被看作是现代性的一种象征。小说中,女女遭外国人强暴本是偶然,却生下了聂大;与聂广庆也可以生下聂二。可是,一旦和盖运昌在一起,就好像失去了生育能力,这是为何?后来,女女让聂二改姓为盖也是出于无奈,盖运昌名义上总算有了子嗣,但他不得不面临内心的尴尬和煎熬。从文化层面上来解读,盖运昌的“断子绝孙”,其背后隐含着深刻的意蕴,即,以血缘关系为基本纽带的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的被迫瓦解。而导致这一切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就不得不归于米丘所代表的他者异己力量的冲击了。所以,单从这一点来看,葛水平的《裸地》与贾平凹的《古炉》,其取向是惊人相似的。只不过,前者强调的,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性对于宗法社会的冲击,而后者则是革命现代性也即社会政治运动对于宗法社会的瓦解。杰姆逊早就指出:“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很显然,葛水平的这部《裸地》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家族—国族”共有寓言的意义上,才能够得到很好的定位与理解。
对于宗法制文化传统在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乡村世界中的逐渐土崩瓦解进行着全面观照思考的,是山西作家马旭一部名为《善居》的长篇小说。善居是吕梁山深处一个村庄的名字:“同治年间,扇居附近的拐峁村敌下人命,县太爷微服私访,路过扇居,发现扇居虽然地处偏远,杂姓杂居,却民风拙朴,人性憨实,村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男女老幼安贫乐命,立身做人以德为先,令方圆几十里的人刮目相看。于是,征得村人同意,改扇居为善居,并欣然提笔,写下‘谨表德诚’四字,以示嘉勉。”《善居》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石心锤。天性老实善良而且还认死理一根筋的石心锤,幼承庭训,一心向善,终其一生都坚持恪守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从某种意义上说,“善居”之“善”,最突出地体现在石心锤身上。小说的故事起始点,是民国二十八年也即公元1939年。如前所言,这个时候,所谓的现代性业已对宗法制传统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很可能是因为天高皇帝远的缘故,尽管日本人已经全面侵华,但善居村人的基本生活秩序却并没有遭到严重的破坏,以“善”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规范依然得到了较好的延续保持。然而,这只是故事的开端。之后,举凡“土改”、“人民公社”、“大跃进”、“文革”,一直到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伴随着叙事时间的不断延长,数十年间发生在乡村世界中的重要事件,都在马旭的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艺术表现。但需要注意的是,时间越是向后推移,善居村石心锤所努力践行的以“善”为核心的宗法制传统就越是遭受颠覆与消解。某种意义上,一部《善居》所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正是乡村传统道德体系的溃败史,是宗法制传统不断被消解的一种历史过程。
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是,对于以上这些作家不约而同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中如此一种对于古老的宗法制传统大唱文化挽歌的精神价值立场,我们到底该作出怎样一种合理的评价呢?在这方面,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来自于黄平。在谈到贾平凹的《古炉》时,黄平指出:“退回到民国之前,崇尚道德的善人,依奉乡规的蚕婆,懵懵懂懂的不识字的村民,小国寡民,安贫乐道,恪守阴阳五行,礼俗人心。这是否也是‘乌托邦’?”“比较而言,《秦腔》召唤出的自我阉割了的引生,《古炉》召唤出的十二岁的孩子狗尿苔,他们身上都有一个悖论般的特征:早熟,又无法发育。这恰是贾平凹念兹在兹的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的倒影,贾平凹小说中的‘孩子’——狗尿苔之外,更典型的是《高老庄》里的石头——既幼稚,又苍老”(黄平《破碎如瓷:〈古炉〉与“文革”,或文学与历史》,《东吴学术》2012年第1期)。不难看出,黄平对于贾平凹包括《高老庄》、《秦腔》、《古炉》在内的一系列长篇小说中表现出的认同肯定传统道德价值的精神取向,从根本上说,是颇为怀疑的。其实,不只是黄平一位,据我所知,对于贾平凹的此种精神价值立场持怀疑态度的,也还有其他一些批评家。比如,山东理工大学的张艳梅教授,在与我的交谈争论中,就曾经多次表示过相类似的观点立场。在他们看来,一种现代启蒙精神的匮乏,恐怕正是这样一批作家的精神致命伤所在。首先应该承认,这些批评者的目光是敏锐的,某种意义上说,思想精神层面上的“去启蒙化”,确实是以上一批小说作品的共同思想特点。就当下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思想混乱状况而言,强调现代启蒙精神的传播,当然是一件现实针对性极强的事情,我不仅理解,而且也完全赞同。但这样的一种现代启蒙精神,是否应该成为衡量评价小说创作的一个必要标准,恐怕却是需要讨论的。我觉得,在一个多元宽容的现代社会中,能够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有效地渗入并充分张扬现代启蒙精神,比如像张承志、张炜、史铁生那样,固然难能可贵,但是,如同这批作家这样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对于宗法制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持有肯定姿态的文学创作,似乎也并不应该予以简单的否定。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我才特别认同孙郁对于《古炉》所作出的一种价值定位:“应该说,这是作者对于乡土文明丧失的一种诗意的拯救。鲁迅当年靠自己的呐喊独自歌咏,以生命的灿烂之躯对着荒凉,他自己就是一片绿洲。贾平凹不是斗士,他的绿洲是在自己与他者的对话里共同完成的。鲁迅在抉心自食里完成自我,贾平凹只有回到故土的神怪世界才伸展出自由。《古炉》还原了乡下革命的荒诞性,但念念不忘的是对失去灵魂的善意的寻找。近百年间,中国最缺失的是心性之学的训练,那些自塑己心的道德操守统统丧失了。马一浮当年就深感心性失落的可怖,强调内省的温情的训练。但流行的思潮后来与游民的破坏汇为潮流,中国的乡村不复有田园与牧歌了。革命是百年间的一个主题,其势滚滚而来,不可阻挡,那自然有历史的必然。但革命后的乡村却不及先前有人性的温存,则无论如何是件可哀的事。后来的‘文革’流于残酷的人性摧毁,是鲁迅也未曾料到的。《古炉》的杰出之处,乃写出了乡村的式微,革命如何涤荡了人性的绿地。在一个荒芜之所,贾平凹靠自己生命的温度,暖化了记忆的寒夜。”(孙郁《从“未庄”到“古炉村”》,《读书》2011年6期)现代启蒙精神的表现与传播诚然重要,但乡村世界的自我救赎就不重要么?答案必然是否定的。尽管说孙郁的具体谈论对象只是《古炉》,但我以为,他的这种说法,完全可以移用来评价我们这里所具体讨论的这样一种长篇小说创作思潮。
最后,有一点不容忽视的是,以上这批作家们的如此一种艺术书写,与当年“五四”时期鲁迅、巴金、曹禺们的作品,已然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对照。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在他的系列乡村题材小说中,巴金在《家》、《春》、《秋》中,曹禺在《北京人》中,都曾对中国传统宗法制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与否定。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作家似乎有意无意地又成为宗法制的卫道者,似乎为本来一去不返的宗法制招魂了,这的确令人备感惊异。然而,细细探究原因,还是会豁然开朗。比如《裸地》中的盖运昌,如果放在鲁迅和巴金笔下,很可能就是赵太爷、鲁四老爷、冯乐山、高老太爷等形象,他们都是作家要坚决批判和否定的宗法制代理人。但是,葛水平笔下的盖运昌,虽然也存在人性的弱点,但从总体的思想倾向和叙事立场上看,作家还是肯定这个人物的。小说意图通过盖运昌人生悲剧的描写,为传统宗法制社会谱一曲凄凉的文化挽歌。那么,为什么当下时代的这批作家,会与“五四”作家的思想艺术反差如此巨大呢?这个问题相当复杂,但不同时代所造就的文化语境的差别,却无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不同的文化语境,导致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而这种取向自然会流露在其创作中。在鲁迅这一代作家所处的时代,启蒙思想是主导,强烈的反传统精神让他们不无激烈地反对并颠覆着传统的宗法制社会。而新世纪的这批作家,置身于价值虚无、精神沦丧的工业化社会,急迫的压力,让他们本能地要为宗法制大唱文化挽歌。另外一方面,所谓“国学热”的兴起和甚嚣尘上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国学热”其突出的表征是文化保守主义,也就是固守中国的传统,而中国传统在乡村世界中,就具体体现为宗法制的文化秩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