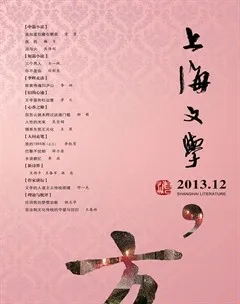乡谈摭忆
我的家乡在安徽中部的丘陵地区,除了漠漠田野、缓缓起伏的坡冈,似乎也就乏善可述。何况我生长的20世纪70年代,乡村还很贫穷。我的家乡连村落也是破旧的,当然那时还有清澈的河流、碧绿的丛林,其他能够给人留下美好回忆的,也就寥寥无几。
当然还有人。凡是有人,特别是有人群在的地方,多少总会有一些悲欢离合的故事,然而在我的记忆当中,这些故事也都非惊世骇俗、耸人听闻,只是微末得如同平静流淌的河水偶尔泛起的涟漪,很快就消逝了。然而,当今天我在城市清闲下来,或在案头兀坐,或凭窗点燃一支烟的顷刻,我那家乡还会从几千里外跑来,浮现在眼前的更多是乡亲们那一朵朵干枯半干枯的花瓣似的面孔,以及他们那平常的謦咳言笑。
“你知道么?地球是一个圆盘,太阳每天都绕着它转……”这样一句自相矛盾的话(既是“球”,怎么又是“盘”呢?)是我七八岁的时候,依在村前的篱笆边,一边吃着偷摘来的桑椹,一边听比我大一两岁的孩子随口道来,我却顿时睁大了眼睛望着他,似乎都停止了舌尖的运动,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脚踩的大地是什么,有多大,然而他随意一言,我顿时感觉到世界的广大。
“听说,我们这地上最多的还不是田地,是水,六水三山一分地么……”一个更大的孩子从篱笆边的树桠上跳下来,插言道,“你知道海有多大,长江有多深吗?江无底,海无边,江是探不到底的,大海没有尽头……”这更让我惊讶,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是如此的辽远、恢廓,我不禁生出几分神往。今天想来,这些孩童的稚言嫩语,恐怕正是我宇宙观的启蒙呢。
那些年,我们那里一度传言要地震,而且风声还很紧。村子里头儿为了防震,都劝导村民晚上不要住在家里,于是村人便纷纷把床铺、衣柜和坛坛罐罐等一些家什搬到了空场地上,过起了露天聚居的生活(后来才搭起了两座防震棚)。这样的生活却让孩子们觉得新奇,有得折腾更是让我们欣喜不已,可以尽情地在一家家床铺、衣柜和坛坛罐罐间穿梭,玩得不亦乐乎。玩累了,倚在干草垛边,将一根稻草衔在嘴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说着说着就说到了眼前即将发生的地震,一个大孩子忽然神情肃然,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地震吗?”大家面面相觑,这个大孩子见我们一片懵懂,便正色徐徐道来:“知道吗?我们的地下有一只老大的鳌鱼,是它在驮着我们;这鳌鱼平时是不睡觉的,但很多很多年过去了,它也会感觉到累了、困了,也要眨一13ea80d073f43400fa57c2333591dede96e6942ff6a4e7e902549eaed14776ae下眼的,于是就地震了。”原来如此,但我还是觉得费解,为什么眨一下眼就会地震,难道眨眨眼的动作有那么大吗?然而我怕他们说我无知,终于把到了嘴边的话缩回了肚里。
但是,疑问依然存在,长大了也想在书本里寻找答案。我只在《列子》中找到近似的说法:“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而五山之根无所连著,常随潮波上下往还,不得暂峙焉。仙圣毒之,诉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极,失群仙圣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鳌十五举首而戴之。六万岁一交焉。五山始峙而不动。”这里只说到巨鳌戴山,没有说到巨鳌“载地”呀,似乎也没有讲到何以地震,除非正如屈原在《天问》中所言:“鳌戴山抃,何以安之?”鳌鱼背负蓬莱,不以为苦,反以为乐,“而抃舞戏沧海之中”(王逸注《楚辞》引《列仙传》语)。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故事流传了几千年,仍在流传,虽然途中有些变异。
讲完了大地之事,自然是要叙述到人。而人是怎么来的呢?我们当然不会说是从猴子变来的,我们讲的是中国各地几乎都传说的女娲抟土造人。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大约正好是在抟土玩泥巴。甚至还讲到女娲娘娘一开始造人还很认真,用泥土捏得像模像样,后来烦了,就用绳子随意抽打,所造的人就丑陋下贱了。这与《风俗通》等中国古书上所说的一样。至于人类的繁衍也是“盘古兄妹结合说”——盘古是开天辟地的英雄,但是,他开天地没有开好,误凿了天,所以淫雨不止,终于导致了大洪水的爆发,把他的族人都淹死了,只剩下盘古和他的妹妹。没有人生孩子,人类可能就要断绝了。盘古一想,只有他兄妹俩结合,虽然这是违背伦理的事,但也没有办法。他们在结合前还卜问过上天的意旨。怎么去问呢?他们把一副石磨搬到了山顶,然后分别将石磨的上下两片往山下滚去,如果石磨能相合,他们就结合,反之则否。结果不用说,两片石磨竟然在山脚下合在了一起,这是天意允许他们兄妹通婚呀!于是才又有了人类。原来人类的来历竟是如此的曲折、艰辛、不凡。
现在我们知道这样的故事与各地的传说几乎一致。这讲的是人之“生”,那么人之“死”呢?人类暂时还没有灭亡的征兆,虽然总不断有“世界末日”的传言甚嚣尘上,但最终证明不过是无稽之谈。但是单个的人总是要死的,而远古时代的人跟现在的不同,我的母亲有时也跟我讲古,“他是有尾巴的呀”。她告诉我,古时候人要死是自己可以感知到的,因为他的尾巴届时是会自己就(烧)焦的,而且当他知道他快要死了,就自己砌一个“郭”——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大约是一个土砖砌的地穴之类的东西——住在里面,由他人送点饮食给他,直到死了,就将之封闭起来。这也是无稽之谈,但仍引起我对古人类乃至类人猿的一些怀想。
妈妈告诉我的当然不止这些,灯前纳鞋或月下乘凉,她总要打开话匣子,把她从前人那里听来的古经摆摆。她还讲了“七仙女”的一些轶闻,可惜我大多忘却了,只记得说:“七仙女下凡遇到董永后,曾一起到一大户家做佣工,那大户看上了美貌的七仙女,于是以种种难题刁难他们夫妇,可是都被七仙女一一化解了——你想想看,七仙女是谁呀,她是玉皇大帝的女儿呀!其中有一个难题就是那大户把一大堆乱丝交给董永夫妇,叫他们天亮前必须一根根理好,否则,七仙女就要留下来做大户的妻。这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可是七仙女不怕。她支走了董永,背地里点着了香,又燃了一张她六个姊妹的画像——这是她随身带的。结果那六个姊妹一起下凡来帮七仙女整理好乱丝,一大清早交给了居心不良的大户,叫他目瞪口呆。最后董永和七仙女就从劳役中脱身,真的夫妻双双把家还了。”这简直有点像我后来读到的格林童话中灰姑娘一类的故事。
这些故事当然都找不到准确的出处,都是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不知何时而起,也不知何时就风吹云散。即便有心做民间文学研究,恐怕也不能搜罗净尽。不过,常到我家来闲谈的一位堂姑父跟我们讲的几个故事,我后来多少知道了一些出处。
想起来,那还是一些令人值得回味的夜晚。农闲时节,尤其是冬天,每当天色黑定,我的那位堂姑父就会打着灯笼或手电,走过一道小巷,来我家的院墙边叩门。父亲正在家,便请他坐定,泡上茶来,于是在昏黄的油灯下,堂姑父总是能够很自然地找到话题,引出一个个故事。有几次话题是从目连救母开始谈起的,接着讲到五丁开山又讲到刘邦斩白蛇起义,其中许多就来源于中国历史故事,只是掺杂了许多道听途说。他常常提到目连深入地狱去救他的母亲,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他是何方神圣,后来才知道旧时乡村里常演目连戏,甚至远在唐代就有这个佛教题材的说唱文学。
“这人都是命数已定。”我的堂姑父往往先来这么一句开场白。接下来会说:“你譬如……”譬如什么呢?那就是他要讲的故事了。有一回,他跟我们讲起朱元璋,说朱元璋小时候就屡见“不凡”。他家里穷,为人做放牛娃。有一次,他和别的放牛娃一起去放牛,他们把牛散放在一边,就玩耍去了。到了晚上才想起来,而这时肚子正饿,要回去肯定是赶不上地主家的晚饭了,朱元璋于是就和小伙伴们商量,杀一头牛来充饥。别的小孩都不敢,只有朱元璋把他自己放牧的牛杀了,散给大伙儿吃。吃完以后怎么给地主交代?朱元璋说别急,他把牛头和牛尾分别埋进一座小山丘的两侧,然后回去对地主谎称牛是钻进了山岩里出不来了。那地主肯定不信呐,就揪着朱元璋一起实地察看,看见果然牛是钻入了山岩中,拽拽它的尾巴,你猜怎么着?就是拽不动。你说神奇不神奇——我的堂姑父啧啧叹息。他谈兴正隆,要继续讲下去:朱元璋成功以后,他那些当年的牧牛伙伴都来找他,想讨一份差事,有的跟他叙旧,就直不笼统地说当年我们在一起放牛如何如何,朱元璋一听,这不是揭他的老底吗?便把他们杀了。有的伙伴聪明,就含蓄多了,他说,当年,咱们骑个马,上朝山……他所谓的马,是牛;所谓的朝山就是“潮”山——早晨,刺草丛里都挂满露珠,可不就是“潮”山么?而“朝山”跟“朝廷”相似,也就一字之差,这样讲朱元璋当然高兴了,就给他封了官。
这样的故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当然是竖起两耳听得津津有味,也没有去想故事真实性如何,是怎样流传的。或者我本来就知是乡野杂谈,哪知道,连吴晗所著的《朱元璋传》里也提到朱元璋小时候牧牛杀牛、埋牛而诓人成功的事,可见这个传说渊源有自。
我的那位堂姑父还讲到朱元璋微服私访,于野外见到一个与他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放蜜蜂老头。按照中国古代的算命术,所谓八字相同,命运应该不相上下,但是同一时辰还分前后呢,朱元璋在前一点,所以贵为天子,有十三司为他理财,放蜂人稍后,所以贱为草民。朱元璋再回头看看他的蜂箱,不多不少,也正好是十三箱。“数量相同,其实天差地别,你说这不是命中注定是什么?”我的堂姑父再一次感叹。当我读到明代江盈科所作《雪涛小说》,才知道这并不仅仅出自田夫野老的口头,该书第一篇《蜂丈人》即述此事:
太祖微行至田舍,见一村翁,问其生庚。翁告之某年月日时,皆同上。太祖曰:“尔有子乎?”答曰:“否。”“有田产乎?”曰:“否。”“然则何以自给?”曰:“吾恃养蜂耳。”曰:“尔蜂几何?”曰:“十五桶。”太祖默念曰:“我有两京十三省,渠有蜂十五桶。此年月日相合之符。”太祖又问曰:“尔于蜂,岁割蜜,凡几次?”翁曰:“夏春花多,蜂易采,蜜不难结,我逐月割之。秋以后花减少,故菊花蜜不尽割,割十之三,留其七,听蜂自啖为卒岁计。我乃即春夏所割蜜易钱帛米粟,量入为出,以糊其口;而蜂亦有余蜜,得不馁。明岁,又复酿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饱,盖若此。他养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尽割之,无余蜜,故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无蜜,皆莫我若也。”太祖叹曰:“民犹蜂也,君人者不务休养,竭泽取之,民安得不贫以死?民死,而国无其民,税安从出?是亦不留余蜜之类也。蜂丈人之言,可以传矣,可为养民者法矣。”
一看就知道,这也不过是文人杜撰的“寓言”,意在告诫统治阶级对小民的盘剥要有限度,如果“竭泽而渔”则“无鱼”矣。不知怎么一传,传到田夫野老那里就成了“命定说”的“佐证”了,倒是说明乡村里“信命”是信到了骨髓。
堂姑父在我们乡村也算得上是有学问的人,他读过几年私塾,上《孟》还能够背诵一些,但他一生都在穷苦和疾病中挣扎,所以照样把一切归结到“命”。他讲的黄巢的故事,照样不出“命数”说之限,只是它更具有“奇幻”效果,还是值得一记,大意如下:
人家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在数者难逃。此话不假。传说黄巢不堪官府的压迫,准备造反了。黄巢知道造反就要杀人,而且杀多少人,杀谁,天数已定。甚至有知天命的人已为他造了花名册,他只要照着花名册,一一杀去即可。他在起义的前一天就得到了这个花名册。没想到,那花名册上的第一人就是他的一位好友。他实在不想杀自己的好朋友,就叫他等到(起义)那一天躲到马厩里——因为马厩里脏呀,他黄巢肯定不会跑到那个地方去杀人,他的朋友听了这话就躲进了马厩,但他很快就感觉那里气味实在难闻,再也不想躲在那里。他忽然看到破庙前的一棵柳树是中空的,心想,躲到那树洞里肯定不会被发现,于是他就这么做了。终于到了造反的那一天,黄巢备了酒,叫人列好阵,要杀人祭旗了,按照花名册,叫他的好友,没有人应,他也不追究,只是说,既然他不在,就拿这棵柳树开刀吧,随即一刀下去,刷——没有想到喷溅出来的是人血……所以说,黄巢杀人无数都是有“数”的。黄巢起义,死了多少人,最后黄巢杀人杀得自己都害怕了,就放下了杀人刀,做了一名屠夫(也有说他转世做了屠夫)——杀猪。他开了一家肉铺,每天杀猪卖肉。他的隔壁是一座寺庙,寺庙里的和尚与黄巢相熟,黄巢有时也到和尚那里谈闲天。有一天谈到深夜,黄巢要回家,说明天还要早起杀猪呢,然而和尚还是坚留他再坐一会儿,说是你自家里不是有两口猪吗?不用起早准备,就可以赶上早市。黄巢想想也是,就在和尚那里多留了一会儿。第二天一早,他赶到自家猪圈准备把猪撵出来宰杀,哪知道那猪一见到他就吓得哆嗦,紧缩在一角不肯出来。黄巢正急得手足无措,昨晚谈天的那和尚却踱步过来,说不用急,他可以叫猪出来。那和尚站在猪圈口喊了两个名字——正是黄巢已逝的父母的名字,你猜怎么着?那两头猪就乖乖地走了出来。黄巢这下明白了,就扔掉屠刀,扑通一声跪地求和尚收下他做弟子,他要修行成佛。和尚不答应,黄巢仍不松懈,最后和尚被他纠缠不过,就收了他做弟子。不久,和尚要出外化缘云游,黄巢也跟着他去,走出村子不远,遇到了黄巢的妻弟,他听说黄巢出家当了和尚,便也缠着要走,和尚不答应,最后被缠不过,就答应了。于是他们师徒三人一起登途远行。走了不久,就在丛山间看见一座深宅大院,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他们当夜就借宿于此。夜里,宅院后厢灯火辉煌,笙歌细细,还传来仕女喧哗,女主人衣着光鲜,雍容高雅,并且向和尚传下话来,她的两个女儿二八年华,姿容妙曼,正在择婿,她见和尚的两个徒弟气质不凡,想招他们为婿呢!和尚问二徒愿否,黄巢愿心甚坚,毫不为动,他那小舅子已露钦羡之意,和尚劝他留下,他便就坡下驴,留在了这豪宅里。和尚与黄巢再次上道。走了半天,师父忽然对黄巢说他的拂尘还挂在昨夜借宿人家的墙上,要他返回取来。黄巢沿原路返回,找到昨夜的地方一看,哪里还有什么深宅大院、雕梁画栋,只有一个巨大的老虎洞,洞里正伏着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师父的拂尘正挂在虎耳上,一旁还有一堆白骨。黄巢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他匍匐在地,叩头对虎说,如果要吃他,就请来吃;若留他一命,就点点头,让他取走拂尘。那虎果然点点头,黄巢就取下拂尘返身追赶师父去了……
这样一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式的故事,毫无疑问是佛门人物编造出来以“度化”人的,当然是荒诞不经,故作奇幻以动视听。我怀疑出自中国的哪本佛教经书或者释家的讲法也未可知,可是我读书少,到底是找不到它的来源。不过,即使那时我少不更事,对于黄巢这样的英雄如此“末路”,心里也是颇为失落的。
我所听到的乡谈,听到的带有迷信色彩的颇不雅驯的故事,似乎还有一些,择要写在这里,除了为民间文学研究者所做的田野调查提供些可能的材料,还仿佛可以从此略窥当年村人的精神和生活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