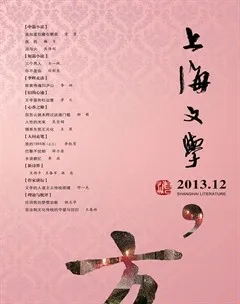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困境
一
没有人会质疑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我们这个看起来充满活力的时代,人的情感和本质的某些基础正在发生不可思议的异化,人们既不满意当下琳琅满目的多元生活,也不对明天可能井然有序的新秩序寄予希望,同时对古老的道德传统避之莫及,宗教的或世俗的人道主义受到广泛质疑,它们被悬置在人们的脚后跟上,不再加以理会。人们正在努力挖掘一道深不可测的自我鸿沟,与世界分裂,进入“衰老期”。
这个时代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胜利与奴役共存的时代?经济革命的胜利和商品化范式的建立使意识形态政治淡出人们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的非人格化机械法则;数字革命的胜利以置换的方式重新创造和规定了人类生活的空间和时间,取而代之的是信息化时间和网络空间的全新维度;生物学革命的胜利使人的谱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改变从基础上动摇了生物定义的关系,以及人类与自己内质的关系。时隔一个世纪之后,“革命”这个词汇再一次成为这个世界的主流词汇,形形色色的革命从根本上创造出一批新型的革命者,同时塑造出一代被革命切割成碎片,然后再以复制品的方式重新组合起来的新人类,这一切,都在引发传统人道主义的危机。
这个时代日益庞大的技术潮流和政治社会体系的极端极权主义对于个人肉体和精神的独立性、内在性的全面专制,对人们的苦难和恐惧置若罔闻,对敏感而脆弱的人性正在遭受的暴虐无动于衷,这是时代众多病理的主要病症。
个人和时代互为镜像,同样是扭曲的,不真实的。在实证主义和现实主张的科学面前,人不再是一个完全的主体,而是基因自我繁殖的载体,对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求证成了人类唯一的目的,在这一目的下,人的生存被无情地抛弃在知识的范畴之外,远离人类的生存现实,也远离人类追求的真理,正经历着从未有过的冷漠命运。这种对科学狂热的追求和崇拜证明着苏格拉底对人类的教谕,这个教谕是,不要去追问现实生活的不幸,不要去在意那些普遍性和必然性多么违反人的意愿,安于现实,因为“人的最高幸福莫过于在谈论美德中度日”。人这个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
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化导致了人自身的异化。人从事科学研究,以洞悉自然的奥秘,同时发明各种技术驾驭自然,这种关系改变了自然界,创造出新的环境,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人本身。19世纪工业化革命出现了机器对人的胜利,20世纪信息化革命出现了数字对人的胜利,21世纪生物工程革命出现了基因对人的胜利,人在这些新物种的不断胜利中深化和稳固了对自然的主宰力,同时也与自然本质上地隔离开,陷入被自己的创造力和创造物奴役的客体化境地,失去了自己这个目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精神对自然的交合与交融,而是征服、战胜和消耗自然力,视自然力为人类谋取利益与幸福的工具的施力关系。当人日益客体化,并在客体化中丧失个体人格,被自己的造物所奴役时,反人道主义势必取代人道主义。
希腊罗马文化时代,马可·奥勒留·安托尼努斯皇帝在他的《沉思录》中宣称:“不能使他成为一个人的那些东西,根本就不能称为人的东西。它们无权自称为是属于人的东西;人的本性与它们无涉,它们不是那种本性的完成。因此,置身于这些东西之中,既不是人生活的目的,也不是目的的亦即善的完成。而且,如果任何这种东西确曾与人相关,蔑视它们和反对它们则不是人的事。”“一个人越是从容不迫地使自己排斥这些和其他这样的东西,他也就越善。”他还说,“那不能使一个人本身变得比从前更坏的东西,既不可能使他的生活变得更坏,也不可能从外部或内部伤害它。”
事实上,安托尼努斯大帝否认的那些伤害始终存在,并且主导着人类的改变。
现在,我可以回到我的题目了: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的困境——我可以做一点类似于修辞学的工作——它是人道主义传统的困境,简而言之,它是人的困境。
二
人的尊严注定了一件事会在终极点上得以成立,即人的尊贵不会建立在对任何他人的崇拜之上,不会最终接受他人赐予的天国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人最关心的问题不是上帝的意志,不是上帝说了什么,而是自己的理性原则,并且按照那个原则塑造自己和建立社会。
那个理性原则在哪儿?看起来,我们都会同意苏格拉底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是人能对理性的问题给予理性的回答,因而人是一个有责任的道德主体。人道主义最初的解释,让我们在一开始对人类的自我觉悟——这是东方宗教的一个关键词语——抱有朴素的希望。但是非常遗憾,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人对自己的生活,包括大多数理性问题给予的是非理性的回答。
这个世界的精英,以及政治家们,无一不是人性的主张者和鼓吹者,他们的一只手上握着他们创造出的真理,而另一只手上,不管握有多少面旗帜,肯定有一面写着人道主义这个符号。可我们都看到了,对和他们同时生活在一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苦难和无助中的人,他们从来不屑一顾。
道德价值并非宇宙的现实,并非自然现象,亦非造物主的规定,而是人为了人的目的创造出来的。正如无法举证人在偷吃禁果而堕落之前完美无瑕的天国生活,无论是自然法则还是有神论,都无法从客体意义上给予真实的证明,以确认普泛意义上的道德价值的存在。
我们既不能过高地信任我们的精神,把自己当成分裂的天使,约束甚至灭绝肉体冲动,也不能过高地相信我们把握物质世界的能力,使我们变成有脑子的野兽。良心和神的启示不能帮助我们解决所有的问题,甚至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基本的现实生活的问题。
指望人用理性精神战胜和超越自己的本性是无效的,但是,我们不可以永远聆听关于人的原罪和人的堕落的晦涩和忧伤的故事,不可以默认它世世代代提供给我们的那些个人生命体验和整个人类历史的论据,不可以不做出任何理性的解释和反抗。至关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想像人在受到自然本原支配,受到人所在的自然界支配的时候,不寻求与神性力量的联系,并且得到它的支持。
内心的善只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人这样要求我们,因为商品世界只会要求我们不断建立和强化自怜自爱,强化欲望力的特质,让我们大言不惭地提出第一和原始的要求,同时指导我们不惜任何手段去有效地满足于这一要求。
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中这样说到:“人们赞赏巍峨的群山,浩淼的大海,宽阔的河流,蜿蜒的海岸,旋转的星体,却把自己置之脑后。”问题恐怕不是这样,不是人在忽略自己,而是人在认识自己的问题上不断受挫。人被认识自己这个命题弄得疲惫不堪。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是具有人类外表的神吗?真的以为由于自我的选择,我们可以在转瞬即逝和永恒之间游刃有余吗?有关我们自己,我们能说什么呢?那是我们最大的盲区。我们在这个盲区里行走了几千年,无数火把和明灯点亮了黑暗,它们如今仍然高悬在那里,但我们却看不到走出盲区的方向。身处天使与野兽之间,除了肉体和肉体冲动之外,我们对自己所知不多。
人类始终没有走出但丁的《神曲》,始终在痛苦地漫游着,穿过地狱和炼狱,死了,再以新的肉身形式活回来,继续穿过地狱和炼狱。代表理性精神的维吉尔并不永远都钟情于人类,那个天国中的天堂,它在哪儿,人类始终没有找到。
三
文学关注什么?之于人类,文学这片羽毛是假以为翅,引导人类超越现实,飞往别尔嘉耶夫所说的“天穹的故乡”,还是假以为掸,抚却人类恶和虚伪的尘土,还人类以对神性自我的相信?
无数了不起的文学家用神性的语言揭示和分析了人类的各种品质和品德,以及这些品质和品德的演化,并试图对这些品质和品德的性质作出规定,善、仁慈、公正、正义、节制、慷慨、谨慎、勇敢、智慧、理性和悲悯情怀。当然,还有那些与之相反的人类的品质和品德。如今,神性的语言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施暴——认知世界维度的混乱导致语言的零碎和遮蔽,对前文化的清算和割裂导致语言的烂根和缺乏连贯,强制性制度化导致语言具有可管理性和标准性,商品流通导致语言具有流通能力和广告效果。语言谱系的崩溃,使前文学创造出的曾经令我们为之倾倒和自由向往的那些偶像,一个个泥牛入海,面目全非;披在人的生命目的和意义身上的粉饰霓裳和掩盖帷幕纷纷坠地,人类无以遮体,却得到了一大堆不复所用的华丽造物。
很难看到简单而彻底的文学放逐,随声附和的话语和随波逐流的生活成为普世生活的文本。在这样的文本中,我们不是看到了我们的世界和我们自己的生活有多么荒唐,而是看到了那些荒唐有多么的严肃和深刻,以及作为文明形态之一种,它将怎样载入人类历史。
我要提到20世纪中国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批判现实主义大师鲁迅,这位无所畏惧的人道主义战士视文学为一柄决不宽恕的青铜剑,剑指向处,是民族人格的异化、社会道德的沦丧、导向卑下的恐惧、导向驯服的妥协和导向奴役的权力。道德人性的泯灭、精神的萎顿、日益削弱的国民气质始终是鲁迅先生的最痛,对缺乏神性追问、不断分裂的民族品格痛心疾首的批判和对善和怜悯的觉醒的呼唤始终是鲁迅先生的生命姿态,他就像一道可贵的闪电,划过建立在虚幻的人类之善、自然自善、历史之善的中国特有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灰色天空,划过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世俗生活的黑暗天空。
另一个困惑来自文学的本源。一体化大潮汹涌,民族文化遗产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解构。它的悖论是,任何一个人类文明形态都建立在前文明形态之上,如果没有对于历史前景的描述,人类就无法理性地前进,如果无视自己的过去,人类就不可能建设一个清晰RvcSbpq2pBu7c/tBEkmHrw==可见的未来观。
感谢我们的前人,他们留下了那么多的人类宝贵财富,我们当然有可能比人类任何时期的人们都看得更远,但这并不说明我们就有多么的了不起。事实上,我们的确不过是一群矮子,因为我们站得不矮,而我们脚下的那些肩膀,它们的主人是一些巨人。
遗憾的是,文化遗产本身并不会使人变得聪明和智慧,哪怕这个时代的人们在文化遗产面前并非是无知的,哪怕人们有这个福分,让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复活,成为人们的同时代人,成为时代精英分子的楷模,芸芸大众的力量源泉。
假使我们只是专注于欣赏和复制古人灿烂的文明生活,而忽略了自己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病态的;假使我们只是沉湎于古代神话英雄的创世纪诗篇,而不去聆听我们父母和孩子的哭泣声,我们就将失去我们的家庭、邻居、民族和同时代人;假使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人类的过去,不曾考究人类的现在,不曾弄清楚我们是谁、从哪儿来、要去哪儿,我们根本就不算活着。
继承和扬弃不是问题,继承和扬弃什么也不是问题,为什么继承和扬弃同样不是问题,问题仍然是那个最简单的提问:文学是什么?
文学是一种自由,自由是一种可能而非必然,从这个角度讲,文学是理想的,但归根结底是悲剧的,它所关心的是人在悲剧现实中的罪恶、痛苦、反抗和救赎。
说到自由,我要提到另一位生活在19世纪俄罗斯的伟大作家费奥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以他天才的思辨性和对人性罕见的抵达程度揭示了人类自由的两难境地,这位差点儿被沙皇枪毙掉、为苦难深重的人民折磨得精神失常的杰出的人道主义思想家在他的《死屋手记》、《被欺凌与被侮辱》、《罪与罚》、《白痴》、《恶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塑造了一个个令人惊讶的充满了人道主义探究的鲜活人物,这些具有复合和复杂人性的人物不仅从文学的角度,而且从哲学的高度告诉我们,自由是人的属性中最为重要的元素,这一元素指向天堂和地狱两个向度,而地狱的向度,正是人性转化为非人性的向度。自由的属性不是天然的,自由是一孔双眼泉,它既是善之源,也是恶之源,以这眼泉水为生命的人类由此善恶双生,人类的罪恶和苦难正产生于这里,它要求人类寻求一种和人类自由相适应的限制性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至今仍在引起广泛争论同时让人们惊恐不安的形而上学经验。
简单扼要,删繁就简,回归神性的语言——爱是人性的,同时也是神性的。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恶使我们分裂,使世界气急败坏。人生的目的不是超越死亡,而是建立善的德行和品格,完成道德实践。人应该把人当做人来对待,这个人包括自己以及他人。
保护好我们的人性,那是我们较之客观世界更为重要的理性世界,我们正是从那里起身,前往理想之地。我们的确需要活得更具有主宰力——但那不是任何形式的权力主宰,而是与善的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