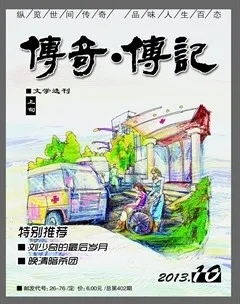晚清暗杀团
在推翻清政府的武装力量里,既有经过正统训练的新军、民军;也有作战团队如敢死队、暗杀团、飞机团、商团;更不乏秘密的会党组织如洪门、哥老会、铁血会等。在这些作战组织的带领下,反清之士前赴后继,舍生取义。无论是民间组织还是正统的军队,都纷纷变成了清政府的“掘墓人”。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是1910年一位名叫汪兆铭的人在谋炸摄政王载沣失败后留下的豪言,如今,世人记住的则是他另外一个名字——汪精卫。
历史功过任评说,多少烈士前仆后继。
从史坚如刺德寿开始,到吴樾刺五大臣,徐锡麟刺恩铭,再到彭家珍炸良弼,在清王朝最后的十年里,在北京、天津,在上海、广州,这种近乎“献身成仁”的作战风潮,无疑是夹在众多失败的武装起义中,最令人热血沸腾的革命手段了。
他们,拥有共同的名字——刺客,短短十年间实行了50次暗杀行动。
他们,依靠共同的团体——暗杀团。由革命党人筹组的暗杀团前后就达16个之多。
炸弹、匕首、子弹,如惊雷贯耳,惊醒沉睡国人。
暗杀,最省钱的革命方式
1911年4月27日,广州城内刀光剑影,这场事后被称为“碧血黄花”的起义最后以失败告终,革命军伤亡惨重。幸存党人逃亡蛰伏在河南(现海珠一带)郊区,除了养伤,革命者在等待一个机会,等待反扑复仇。这在一个月后胡汉民致孙中山信中可见一斑,“现时克强伤大愈,愤恨张、李二贼,欲以个人对待之”(胡汉民致孙中山、冯自由函《1911年5月31日》)。信中所讲“克强”便是革命敢死队首领黄兴,而“个人对待之”所指便是暗杀。
从革命“经济”考虑,暗杀是最省俭的一种方式,只需一两条人命和炸弹,便可收获广泛的社会效应,但也体现革命消极的一面。有人统计过,作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中鼓吹暗杀的内容,占了全部图文20%以上。一声巨响,暗杀团风起云涌,在辛亥年间,“欲以个人对待之”不在少数。在众多有组织的暗杀团中,拥有徐锡麟、秋瑾等的光复会最为后人所知,而在广东,则活跃着令两广高官闻风丧胆的“支那暗杀团”。
作为“支那暗杀团”缔造者,刘思复1905年加入同盟会,在留学东京时从一名沙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学到了自制炸弹的技术。第二年春天,带着绝活的刘思复在广州旧仓巷凤翔书院自制炸弹,准备暗杀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不料事泄被捕囚禁,但因此也名噪一时。1909年出狱后,刘思复便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目标锁定广东高级官吏,而暗杀团的副团长,便是大名鼎鼎的岭南画派先驱高剑父。成员中还包括有日后炮轰总统府的陈炯明,1910年2月新军失败后,陈炯明潜回海丰家中,途经香港时秘密加入暗杀团。
制“毒弹”炸死广州将军
在广州海珠区宝岗路的西边,在一片绿荫下,一个叫“龙导尾”的地方显得格外幽静。关于“龙导尾”,当地流传着一个有趣的说法:广州城龙头位于越秀山,龙身自北逶迤而南,到了现宝岗大道西一带便是龙尾,故该处也称“龙导尾”。此说看起来似乎有穿凿附会之嫌。但这个现在看来有些市井味的地方,一百年前却聚集过一群热血青年,他们曾如龙尾般搅动过当年的历史。这帮热血青年,便是“支那暗杀团”成员。
龙导尾七间直街9号老宅外观看起来和普通民宅无两异,但在广州彩瓷历史上同样有特殊地位,为“河南彩”的发源地,老宅主人则是广彩大师刘群兴,他另外一个身份便是“支那暗杀团”的成员。刘群兴与高剑父、高其峰自小便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原本只闷声搞艺术的他,在高剑父回国担任广州同盟会分会会长后,加入到革命起义的队伍中。
离刘群兴所住的七间直街9号不远处,便是“广东博物商会”彩瓷工场,如今旧址虽已淹没在一片建筑中无迹可寻,但据刘群兴之子刘致祥介绍,当年在这个工场内,刘群兴白天主持彩瓷工作,晚上则在外面望风放哨,高剑父等人则在其中制作炸弹。“常常是睡在工地,床底下就藏着炸弹。”
1911年8月13日,“支那暗杀团”团员林冠慈在双门底(现北京路北段)炸伤李准。仅仅两个月后,暗杀团成员李沛基在南关仓前直街位置炸死新任广州将军凤山,一时名声大震。据记载,由于在暗杀李准中仅仅是炸伤对方,所以暗杀团在对付凤山的炸药上进行了“加工”,改用更重的七磅毒药炸弹,血一见药便自动凝结。为试验炸弹效果,高剑父在制造炸药的龙洞婆髻岭炸伤一头小牛和两只小狗,结果“小狗即死,小牛虽只腿上伤二小孔,但因药性发作,挣扎半个钟头,也即死去”。
作为活动联络和会议之用,支那暗杀团在广州河南(即广州珠江以南地区,现为海珠区一带)设立了三个据点,其一为南华西鳌洲内街的裱画店“守真阁”,其二为位于河南尾的“源利木店”,其三则为河南金华庙“信安颜料店”。其中“守真阁”为同盟会广东分会旧址,以开设何钜裱画店为名,在二楼设立通讯社。
入团须练胆 先看骷髅头
在广州海珠区昌岗中路怀德大街3号,一座典型的岭南建筑特别引人瞩目,满洲窗、长廊相绕,花草丛生,这便是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十香园,也是高剑父早年学画的地方。日前,在十香园举办的《岭南画派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书画展》中,展馆中央一幅《骷髅头骨图》引来许多人的关注。该画主题为三个滚在青草地上的骷髅,用浓墨表现出来后,虽形态各异却阴森撼人,据十香园纪念馆馆长刘志辉介绍,这幅高剑父真迹画为首次公开展出,画中内容反映的正是“支那暗杀团”神秘的入会仪式。
作为一名刺客,必须具备充分的胆识和面对恐怖气氛时的绝对淡定,所以“支那暗杀团”一般会选择在夜晚举行入会仪式,大厅四周用黑布围蔽起来,正中则摆着一张铺着白布的圆桌,桌子上放着一个骷髅头,旁边点起一支白蜡烛。这些摆设,多半是从俄国虚无党那里模仿过来的。等到灯熄灭后,在摇曳的烛光中,主盟人走到会场中间,举起右手宣读暗杀团宗旨和方略,一次仪式下来已令人毛骨悚然,入会新人终生难忘。“《骷髅头骨图》正是高剑父根据当时的情形所绘制。
入会人员经历了仪式后,还要进行其他的技能训练,其中便包括进入暗室,由训练者扔人体骸骨或其他物件进行持续适应,反复锻炼暗杀团员胆量。而训练出来的队员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为执行员,负责执行最后暗杀任务,一类则是补助员,负责后勤供给和联络掩护等,暗杀团用“同心同德”四字为团的小章。
据介绍,“支那暗杀团”的历史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后,团员才“初志已遂,议决自行解散,且耻于求名,遂将团章盟书与年来会议函札等文件,悉皆烧毁”。
暗杀女杰宋铭黄
制炸弹,埋伏炸官吏,不成功便成仁。在许多人看来,这种铁血而近乎悲壮的行为应属革命年代的男人所为。其实不然,辛亥革命前后,一批女性革命者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宋铭黄的历史,你们应该好好写一写,关于她革命的资料太少了。”作为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的曾应枫,最早接触宋铭黄这个名字,还仅仅了解其为西关刺绣名手,但当她细读这段历史,才惊讶地发现宋不仅是民间工艺大师,还是位不折不扣的革命先行者。
据曾应枫介绍,宋铭黄早年由父母做主嫁给了西关一富家公子为妻,婚后因感情不和而离异,这在当时已算是件轰动的事情。由于她从小喜欢女红,所绣的花鸟虫鱼都栩栩如生、形神兼备,在当地小有名头。
光绪末年,宋铭黄被聘为广州洁芳女校刺绣教师,结识了同在该校担任图画教员的高剑父和潘达微。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她与高剑父擦出爱情火花,俩人同结连理。在高剑父担任“支那暗杀团”副团长的日子里,作为妻子的宋铭黄用其女性身份为暗杀行动做掩护。那时内地很难买到炸药,所以暗杀团在香港购买了炸药和军火后,便由宋铭黄组织承担运输任务。宋铭黄有时化装为香港的豪门贵妇,将军火藏在贵重行李中带回广州“省亲”;有时又假扮是医生、护士,带着医疗器械护送病人来广州求医,而瓶瓶罐罐的医疗器械中便暗藏情报和炸药引线等。
孙中山“姐妹保镖”深谙武当派绝学
在辛亥年间的暗杀行动中,最让人记住的女性无疑是“鉴湖女侠”秋瑾。但在革命年代中,还有一对姐妹花也格外引人注目,她们便是曾任孙中山贴身保镖的“尹氏姐妹”尹锐志、尹维俊。
这对亲姐妹深谙“内家”武当派绝技——“五毒殛手”,格斗时可以一当十克敌制胜。在担任孙中山的保镖时,孙中山称姐妹俩为“革命女侠”,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说她们“十余次救过自己的性命”。辛亥革命中,尹氏姐妹主持光复会工作,积极响应武昌起义。
1909年,尹锐志、尹维俊姐妹曾携带炸弹,潜伏北京一年,企图炸死清廷要员,终因清军防守严密,未能得手。其时,姐姐尹锐志年仅18岁,妹妹尹维俊才14岁,后人也将姐妹俩与秋瑾共称为“中国近代史中女界之三杰”。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大洋网—信息时报》2013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