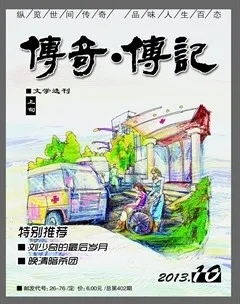FBI追缉国家宝藏
别再被好莱坞电影迷惑了。那些FBI与艺术品大盗暗战周旋的桥段,惠特曼是最不以为然的。他总是在培训新探员时,要求他们将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统统忘光。
仅就阵势来说,FBI追缉国家宝藏的真实主角——2005年成立的艺术犯罪组,其实不超过10个人。在此之前,追缉艺术品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专属部门。这略显寒酸,要知道,FBI拥有将近13000名探员。
而作为高级调查员的惠特曼,来到FBI之前既不是警察出身,也没有接受过专业艺术训练,只是一个跑农业新闻的记者。他每周花四小时在博物馆学习,好让卖家与自己交易时,能感受到他散发出的老练气息。
一些FBI主管,最开始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追缉这些艺术品。多年前,惠特曼想为一幅寻回的失窃画作开场记者会,一位主管讥笑说:“就为了这张小小的画?”在FBI,与杀人放火的人硬碰硬才是受尊敬的。结果,隔天的记者会被围得水泄不通。
总之,一切看起来都不在状态。
就这么勉力维持运转,惠特曼在20年间追缉回了慈禧太后赏玩过的水晶球——它的个头全世界第二大;秘鲁印加帝国的黄金甲——秘鲁总统亲自为他颁发勋章;美国《权利法案》原本——所有的美国公职人员就职时,都要宣誓保护《美国宪法》,以及《权利法案》……这些艺术品,总价超过两亿五千万美元。
在化妆台上发现慈禧的水晶球
水晶球是在一个女管家的化妆台上被追回的。当时,它的上面还盖着一顶棒球帽。
它失窃于1988年的宾州大学博物馆,同时被盗的还有一具有5000年历史的埃及死神铜像。惠特曼接到线报,在一家杂货店发现了铜像。
追踪盗窃链条是如此荒诞:铜像是杂货店老板从一个推着购物推车的流浪汉那里买来的,30美元成交。惠特曼找到流浪汉,流浪汉说是从一个名叫艾尔的男子手上拿来的。艾尔的回答是:“不知道,那东西就在几年前突然出现在我的储藏室里。”
那个铜像至少值50万美元。艾尔说铜像旁边还有一个玻璃球,看起来很丑,把它丢在车库里放了一年多,然后送给了他的女管家。
在女管家惊讶的神色中,这个来自北京紫禁城的水晶球被还给了博物馆。没有人被捕定罪,因为确实找不出窃贼。
惠特曼并不奇怪。因为卖掉失窃艺术品的难度,远远大于去偷艺术品的难度。在黑市,窃取的艺术品通常只能卖到其十分之一的价钱,越出名越难卖。这也让窃贼很焦虑。随着时光流逝,有的艺术品被随意丢弃,有的窃贼越来越沉不住气。
伦勃朗一幅价值100万美元的画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以23000美元的价值出售,卖家被卧底FBI探员抓个正着;挪威画家蒙克的一幅名作失窃之后,挪威卧底警探与窃贼接头,窃贼要价75万美元。如果在正规拍卖行,这个价格只能买到这幅画的一个角——它的公开报价是7500万美元。
所以在某些时刻,追缉艺术品犯罪特别像是在和窃贼比谁更“淡定”。
而且,艺术品追缉也有自己的“时间窗口”。一旦追缉计划暴露,那些名贵的失窃艺术品通常会再次销声匿迹很长时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才会又出现。
引诱卖家自证其罪尤为重要
有时候,惠特曼假扮买家与卖家接触时,卖家怕惠特曼不相信这是被盗窃的艺术品,还会寄来法律条文,我确实违法了,这些违法盗窃来的艺术品,货真价实。
卧底追缉秘鲁印加帝国的黄金甲时,惠特曼就收到了来自卖家的“证明材料”:两本登载有这副黄金甲被盗新闻的《国家地理杂志》。卖家还贴心地在报道页面粘上了一张便利贴。“如果需要其他信息,欢迎随时与我联络。”
在另一起卧底案件中,惠特曼要“买”一件带有老鹰羽毛的头饰。卖家提醒惠特曼,“你得小心,在美国贩卖老鹰羽毛是违法的。”惠特曼故作惊讶,说:“你确定吗?”
后来卖家专门寄来了一份法律条文:《美国联邦法典》第16章第668条,1940年的《白头鹰与金鹏保护法》,其中明文禁止贩卖老鹰羽毛。
让卖家向执行卧底任务的惠特曼证实自己在做违法的事,对FBI来说很重要——引诱卖家自证其罪才能逮捕他们。对于不带枪的艺术品犯罪卧底来说,这一点尤为重要。
卧底诀窍:能不说谎,就不说谎
但大多数卖家满口谎言。面对谎言,惠特曼保证身份不暴露的诀窍是——能不说谎,就不说谎。“别想演戏,你绝对做不到。同一幕,演员可以重演好多次,你只有一次。”比如,使用化名时,姓最好用最常见的,不然用网络一查就会被轻易查到;名最好不改,这样就算在路上碰到熟人叫你的名字,也不会穿帮。
这是有教训的。就在卧底追缉黄金甲一案时,惠特曼随口跟卖家说他是律师,结果几天之后卖家打来电话说:“我查过了,你不是律师。”惠特曼努力编造了一个新的谎言来应付——他对着电话大吼:“我和太太发生争执,出现了一点暴力场面,就这样,他们就把我的执照吊销了!”电话线另一端陷入沉默,卖家还向惠特曼道了歉。
这算是劫后余生。惠特曼也不喜欢这样,因为说的谎越多,就越要花脑筋记住自己的谎言。
还有一次,惠特曼向卖家展示他想要的画作,卖家仔细看着打印出来的照片。“这是FBI的东西。”
惠特曼屏住了呼吸。这些照片的确是从FBI的公开网站上摘下来的。惠特曼把照片剪了下来,贴在白纸上,以为不过就是照片而已,而卖家显然很注意搜集FBI的“情报”。
他掩饰住心里的惊慌,尽量贴近事实说:“你认得这些照片啊?FBI网站,没错。我只有在FBI的网站上才找得到这整批画作。”卖家大笑:“没错,FBI的图片质量最好了。”
又是一头冷汗。
谎可以不撒,局不能不设。在圈套设计方面,FBI艺术犯罪组能动用的“道具”,包括好莱坞女星。这好理解——在某个社交场合,让惠特曼带着卖家“巧遇”一位好莱坞女星,在30秒的时间里,女星会“感谢”惠特曼“上次”在一起艺术品交易中的参谋贡献,然后迅速离开。这也是那些查办贩毒、暴力事件的FBI卧底无法享受的“福利”,因为没有哪位公众人物会愿意与毒品交易沾上边。
FBI卧底必须有三重身份
卧底时间久了,难免会与那些卖家产生感情。
简单来说,惠特曼认为艺术犯罪组的FBI卧底须有三重身份——侦探、艺术鉴赏家,以及推销员。惠特曼在艺术犯罪组的上司,进入FBI之前就是推销员。
这很重要。在惠特曼看来,做艺术犯罪组的卧底,其实就是在和黑道做生意。做生意就要洞悉人性、搞关系——没有一个人是彻底邪恶的,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对方不法及不道德的方面,永远找不到彼此真正的共通之处。这都是推销员必须具备的心理状态。
赢得卖家信任后将其成功逮捕,甚至会引发俩人的复杂情绪。
有一天早上,惠特曼就收到了一封特别的电子邮件,邮件主题写着:“向过去的美好时光敬一杯。”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干得好?你真行?你把我骗得团团转,我们现在心力交瘁,我想你们要的也正是这样的结果。不过,尽管我们现在身败名裂,当初和你相处的时光还是非常愉快。谢谢你善待我们,并且陪伴我们度过了愉快的圣诞和新年假期……这封信不是恶作剧,不是诈骗,不是陈情,也没有任何弦外之音……”
惠特曼读完之后感到一阵内疚,在第二天回复了他的信。“这是我办过最难受的一件案子,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你和你的家人。随时都欢迎你打电话给我。”惠特曼认为,自己说的是真心话。
而在一场跨国追缉艺术品的行动中,惠特曼的推销员气质也帮了大忙。
2001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惠特曼要求一名巴西生意人交出他购买的一幅失窃油画。这次不是卧底任务,而是谈判。身为FBI探员,惠特曼毫不讳言自己在谈判的时候,什么都能承诺,反正不算数。“我可以撒谎、扭曲事实,也可以威胁恐吓,只要不殴打嫌犯就可以了。于是,我又扮了一回推销员。”
惠特曼先将这件案子说成是地缘政治问题,它不是犯罪,但可能会影响美国与巴西的关系。接着,又在巴西人与失窃画作的博物馆负责人之间周旋。
价格压到10万美元之后,他开始努力说服双方接受这项条件。对博物馆那边的说法是,他们可以用10万美元买回价值100万美元的画作;对巴西人则说,这笔钱够让他还清债务和欠税,而且还可以安然脱身。惠特曼向两方都提出忠告:“这已经是最好的条件了。10万美元,你就是赢家。”
成交。
内讧削弱FBI追缉国家宝藏实力
也就是这幅画作的回归,令FBI灵光一闪——追缉国家宝藏,真是绝妙的公关。
从巴西送回的画作名为《76精神》,作者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洛克威尔。画面右下角,世贸双塔隐约可见。对刚刚经历“9·11”悲剧的美国人来说,如果这幅画能顺利回归,足够鼓舞人心。
所以当FBI的一位主管向新任联邦检察官的头号副手报告行动方案时,只花了五分钟,这位官员就笑了。他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公关潜力,他的顶头上司不久之后就能站在电视镜头前,身后摆着这幅能看到世贸中心的画作。
在这之前,FBI地方主管也越来越乐意核准惠特曼去办自己想办的案子。因为记者相当热衷报道这些艺术犯罪案例,写得跟肥皂剧似的,让地方主管相当有面子。这种行动要比那些充满血腥的FBI常规案子讨巧得多,也安全得多。
于是,当秘鲁印加帝国的黄金甲案子结束后,FBI扭转了长期以来不断恶化的公众形象。
惠特曼追回一面曾在南北战争中,由北军第一个非洲裔连队打出的星条旗时,FBI局长、两名陆军将领亲自出席了旗帜归还仪式,并且硬生生地将这个仪式安插进了FBI一年一度的“黑人历史月”活动中。现在,它比世界上现存最大的蓝色钻石“希望之钻”,以及阿波罗11号登月艇都值钱。
当《权利法案》原件被追缉归案,FBI局长动用自己的座机来运送。
艺术犯罪组带回价值4000万美元的伦勃朗失窃画作后,也一下子登上世界各地的新闻头条,这个组在FBI的声望也达到最高点。
惠特曼知道如何在不到10个人的团队,与大众对艺术犯罪“夺宝奇兵”式的夸张印象当中,制造各取所需的神秘感。他们一度仿照FBI十大通缉要犯的格式,拟出了一份十大艺术犯罪通缉单,效果不错。
一旦每个FBI部门都希望能像艺术犯罪组一样受人瞩目时,矛盾就来了。
在2007年一场有望追缉回70幅画作的跨国追缉中,卖家在FBI的内讧中从容逃脱。
当时法国警方向FBI提供了一条线报:有两个旅居美国的法国人似乎正在中介销售两幅失窃的大师巨作,其中就有一幅来自波士顿,而画可能就藏在法国境内。
这起案件历史久远,在1990年代是交给波士顿的FBI银行劫案及暴力犯罪组办理的。因为涉及到追缉艺术品犯罪,所以严格来说,由艺术犯罪组来执行这项任务更合适。但艺术犯罪组刚成立不久,又归FBI总部管辖,就爆发了一场FBI总部与地方办公室“争”案子的内讧。
FBI的目标不在于找回失窃的艺术品,而是要算获得法院定罪的案件数目,因为这就是FBI评绩效的标准。
惠特曼说:“我们局里有些人很尖酸,甚至把案子和法院的定罪叫做数字。我们常常争论这些数字应该归属于哪个FBI的地方办公室。”
内讧不久,FBI进行了内部重组,艺术犯罪组随即成为“冷门衙门”——那些侦探里的艺术鉴赏家们,大多数又回去做起了街头枪战的案子。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原载《壹读》2013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