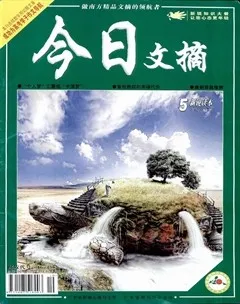尼泊尔同学的中国梦
第一次见到古马尔是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旅行时,一位中国驴友的生日派对上。这个清瘦的尼泊尔年轻人一口流利的中文让我不禁咂舌。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层理解。一番攀谈,我了解到古马尔只有22岁,90后,正在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Tribhuvan University,尼泊尔排名第一的大学,设于加德满都),读硕士一年级,但是,他已有五年的高山向导经验。一年前,他因为身体原因离开雪山,现在一边读研一边经营一家旅行公司。
我对古马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听一听他的故事。凌晨5点的泰米尔区尚未恢复白天的喧嚣,我与古马尔会面。他整洁的西装外面套了一件橙色的冲锋衣,以抵御冬季清晨的寒冷——这是出团时的标准装束。
穿过泰米尔区迷宫一般曲折的幽暗小巷,古马尔的“中国尼泊尔国际旅行公司”标志掩映在纷繁的各式标牌之中。这次业务是一个来自中国重庆的摄影团,他们操着带有重庆口音的普通话向古马尔问好,其间夹杂着对食宿等一些琐碎的抱怨,比如,热水供应。古马尔以纯熟的中文应对自如。
穿校服的高山向导
尼泊尔被誉为“徒步者的天堂”,这个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国度坐落着全球14座8000米雪山中的8座,其间散布着世界上最多、最壮美、最完善的徒步路线。数不尽的背包客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为当地人提供了绝好的工作机会。
古马尔的兼职高山向导生涯从15岁那年开始。
古马尔出生在距离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约80公里的一座小镇,在15岁之前从未走出过加德满都山谷。虽然从小学到高中都享受着免费教育,家境普通的古马尔像众多尼泊尔少年一样,早早开始为未来做打算,筹备大学阶段需要的学费。选择高山向导这个行业,一部分是因为相对丰厚的收入(15~20美金/天),一部分是出于对冰雪巅峰的向往。
成为一名高山向导并不容易,在空气稀薄的喜马拉雅山区,天气以及路线变幻莫测,而徒步者的身体与心理状况也千差万别。古马尔说向导必须是冷静的领导者和组织者,需要在各种重要的时刻做出正确的判断。在独立带队进山之前,古马尔经历了漫长的实习期,从帮厨和队医助理开始,一点一滴积攒这个行业所需要的经验与胆识。
17岁那年,他获得了尼泊尔旅游管理局的向导资格。
每逢学校假期,徒步旺季,年轻的古马尔就带领来自世界各地的徒步者,奔波在世界屋脊的峰峦之间。在兼职高山向导的5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布了尼泊尔和印度北部几乎所有知名的徒步路线,看遍8000米雪山的雄奇,也涉足过穆斯塘秘境探寻失落王朝的遗迹。后来,他终于不满足于在雪山脚下仰望,作为一支登山队的协作,登顶了印度境内一座6000米级的雪山Stok Kangri,他形容登临巅峰的快意:“就仿佛自己是一只雪豹!”
五年间,古马尔接触到形形色色的徒步者,不同的语言,千差万别的文化背景,怀着各自的动机与抱负——
最多的是来自欧美的年轻人,每个毛孔都蒸腾着冒险的冲动;
古马尔曾经和一群来自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在冰封的高山湖泊游泳,比拼谁能够在水下支撑更久;
也曾遇见过80岁高龄的老者,虽然步伐缓慢,却具有非同常人的耐力和隐忍,最终走完整个珠峰环线,让他肃然起敬;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徒步者,徒步开始时他的体重重达140多公斤,臃肿到每迈一步都会摇晃,不得不靠登山杖勉强支撑,在十多天行走中,他不仅完成了自我设定的目标,还减去了30多公斤体重。
喜马拉雅山区入夜之后彻骨寒冷,客栈的火塘周围就仿佛一个人生秀场,来自不同角落的背包客们依次分享自己的故事,那些野心、梦想、与自我的角力,抑或是逃避与落寞。古马尔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他也喜欢听抵达珠峰大本营,或者徒步终点时,徒步者们击掌欢呼,那是梦想实现的声音——这个在雪山脚下长大的年轻人觉得整个世界都向自己敞开了。每一次十多天漫步雪山荒野结下的友谊,不会轻易消逝,有很多徒步者至今依旧与古马尔保持着联系。
有些时候,这样的情谊是生死与共的。
在2009年一次环安娜普纳徒步途中,一名年轻的徒步者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高原反应,使用抗高反药物也不见好转,并逐渐出现肺水肿的体征。古马尔决定立刻带他下山,一方面迅速降低海拔,一方面尽快就医。其时是深夜,天气极端恶劣,大雨倾盆,这名徒步者已虚弱到不能行走,古马尔背起他,咬牙冲进雨里。雨下了一夜,古马尔在泥泞的山路上一直走到天明。“回头想想,真的记不起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大脑好像麻木了,一片空白。”到达山下的医院时,古马尔感觉全身的力量被抽空了,瘫坐在地上,很久很久没法站起来,那年他刚刚19岁。经过两周的治疗,徒步者最终康复出院。“这就是山,一念之差,可能就是生与死的差别。”
五年间,古马尔被尼泊尔名校特里布文大学经济学系录取,并凭着高山向导这份职业赚了大学期间的全部学费。顺利完成本科学位之后,他选择在经济系继续硕士的学习,主攻旅游经济学。
今儿不懂中文就out了
古马尔学习中文已经有三年时间了。“我爷爷那辈,不懂梵文不行;我爸爸那辈,不懂英文不行;到了我这一辈,不懂中文就out了。”
古马尔说,五年的高山向导生涯告诉他,只精通英语和尼语是远远不够的,他将目光瞄准了新兴的中文学习热。特里布文大学的中文学校每天早晨七点至八点上课,以错开学生们兼职与专业学习的时间。
这样早起学习中文的生活,古马尔坚持了三年。
除了去中文学校修读课程,古马尔最感兴趣的是结交中国朋友,用中文向他们介绍尼泊尔的历史和文化。“古马尔和很多尼泊尔年轻人不一样,走在泰米尔街头,时刻会有人用蹩脚的中文搭讪,但是你知道这大多数是出于某些目的,比如兜售商品或是要求做收费导游。可是他交朋友就是为了交朋友,很纯粹很有诚意的人。”古马尔的一个中国朋友如是说。
古马尔不时会用qq和远在中国的朋友聊天,空间的中文日志也经常更新。在最近一篇描写巴德岗的日志下面,有网友批注:“古马尔,你的中文又进步了!”
2011年,古马尔没有想到,他会在高山向导这份做得轻车熟路的工作上遭遇挫折。那天,他带队徒步至之前曾无数次到访的安娜普纳大本营,突然感到无法抵御的疲惫与虚弱,随队的医生测量血压吓了一大跳:“75/40!”“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能睡着,一旦睡过去就无法醒来了。”后来,古马尔侥幸脱险,但是,医生说,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不适合再去高海拔地区工作。这就是喜马拉雅山区,神秘中掩藏着危险,你永远想不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离开雪山的古马尔有些低落,他频频出现在泰米尔区的青年旅社做义工,与天南海北的背包客交流,把陌生人变成朋友总能使他开心起来。古马尔擅长讲故事,周围总是吸引了众多的中国朋友。他能够用易于中国人接受的表达方式,将尼泊尔陌生的宗教与历史,融合在一个个有意思的故事里。比如,他坚持称印度教中的婆罗门祭司为“老师”,因为他很清楚师长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新结识的朋友无意闲谈中,新的机会不期而至。
在泰米尔街头,古马尔辨认出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中国旅行者正逐渐成为尼泊尔旅游市场的主力。“之前,尼泊尔旅游业的支柱是来自于欧美的徒步者。现在,中国旅行者增长得特别快,几乎超过了欧美背包客。”与寻求惊险刺激的欧美背包客不同,中国旅行者往往被尼泊尔独特的宗教文化与喜马拉雅风光吸引,但是,语言往往成了他们体验雪山之国文化的障碍。
一次偶然的机会,古马尔向一位中国朋友聊起自己创业的想法。他想创立一家全中文服务的旅行公司,向中国旅行者提供十天左右的尼泊尔摄影之旅。这位在中国从事旅游行业的朋友与他一拍即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