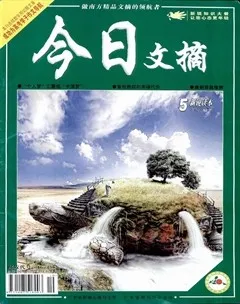1933年的中国强盛梦
一封征稿信
1932年10月16日,著名作家、出版家胡愈之接手主编《东方杂志》。《东方杂志》是发表过鲁迅著名小说《祝福》的阵地。胡愈之深知其中的分量,接手后便开始绞尽脑汁筹划1933年的新年特刊。
半个月后,一场前所未有、规模空前的中国知识界“新年问梦”活动,在胡愈之的导演下正式拉开了序幕。胡愈之在征稿信中说:“在这昏黑的年头,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下活受罪,便是我们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沦陷在苦海之中。沉闷的空气窒塞住每一个人,大家只是皱眉叹气挨磨自己的生命。先生,你也应该有同样的感觉吧?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了吗?我们绝不作如此想。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诅咒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二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接着,他为1933年的新年之梦设计了两个问题: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
这封信于11月1日由上海寄往全国各地,共计400多份。到规定的截止日期12月5日,共收到回信160多份。
244个“梦想”
经过近一个月的来信整理,1933年元旦出版的《东方杂志》(总第三十卷第一号)以83页的篇幅刊出142人的244个“梦想”。
这142个“回梦人”中包括柳亚子、徐悲鸿、巴金、茅盾、郁达夫、冰心、周作人、林语堂、叶圣陶、施蛰存等大批文化名人。在这244个梦中,“有甜梦,又有苦梦;有好梦,又有恶梦;有吉梦,又有噩梦;有奇梦,又有妖梦;有夜梦,又有白日梦”(胡愈之语)。
冰心做的是“世界大同梦”:“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
林语堂的梦则寄托了战乱时期对和平的向往:“我不希望有全国太平的天下,只希望国中有小小一片的不打仗,无苛捐,换门牌不要钱,人民不必跑入租界而可以安居乐业。”
施蛰存做的是“强盛中国梦”:“中国人走到外国去不被轻视,外国人走到中国来,让我们敢骂一声‘洋鬼子’——现在是不敢骂的。”
巴金与老舍的梦则充满了黯淡与失望。巴金说:“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只能够使我做噩梦……那一切所谓中国的古旧文化遮住了我的眼睛,使我看不见中国的未来。”老舍则说:“我对中国将来的希望不大,在梦里也不常见着玫瑰色的国家。”
画中的“梦想”
由于“回梦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知识分子,胡愈之在兴奋的同时又倍感失落,他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工人及商店职员,应该不至于没有幻想。可是现实对于他们的压迫太大了,整天的体力的疲劳,使他们只能有梦魇,而不能有梦想。”
在142位“回梦人”之外,漫画家丰子恺以漫画的形式为此次“问梦”活动增添了一丝亮色。他一共画了五幅漫画,分别是《母亲的梦》《黄包车夫的梦》《建筑家之梦》《老师之梦》《投稿者的梦》。
在漫画《母亲的梦》中,丰子恺画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手拿管子往孩子的肚脐喂食,孩子养得白白胖胖;在《黄包车夫的梦》中,辛劳的黄包车夫突然长出了四条腿,一路飞奔。而这次《东方杂志》特刊封面也是出自丰子恺之手,画了一个儿童在水盆里洗刷地球仪上中国的污垢,无疑是大有深意的。
没有寄出的“梦想”
这些“回梦人”中没有鲁迅,因为身为胡愈之老师的他拒绝“痴人说梦”。但作为新文化运动导师的胡适并没有拒绝,他的梦是这样的:“我梦想一个理想的牢狱,我在那里面受十年或十五年的监禁。可是我可以读书,可以把我自己的藏书搬一部分进来用……”但胡适最后没有寄出自己的文章。
也许是为了纪念自己曾经的梦想,也许是渴望为当时暗淡的现实照进一丝理想的光亮,1935年和1937年,胡适曾两次以《新年的梦想》为话题发表专栏文章。但此时,胡愈之已不再是“梦”的导演了。
1933年3月,编完《东方杂志》第30卷第4号,胡愈之便被迫离开了。他因“梦想”而接手《东方杂志》,又因“梦想”而丢失这块有影响的言论阵地。晚年时,当他想起陶孟和在其征文中所说的“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一语,不禁长叹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