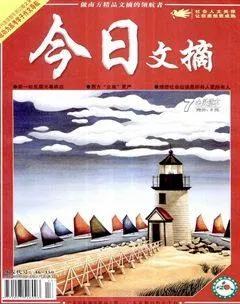青菜
青菜是故乡写给我的第一封信。这信读来怀有柔软的忧伤。就像清明前的刀鱼,那鱼刺虽可以下咽,下咽时也挠了挠喉咙,痒痒的。我的房间有幅小尺水墨,这画画的人还算高明,虽比不上白石老人的雅趣,那几笔淡墨却还能让你感受到小家碧玉的骨感(我一直觉得青菜是有骨头的)。想起风轻云淡的日子,故乡的田野像一张印有清新底纹的稿件,一垄一垄的平整底线,让一个孩子的笔迹那么整齐。我写着青菜青菜青菜,偶尔一朵野花就成了标点。
再次想起青菜的时候,我们都在聊着她。有的人叫白菜,有的人叫油菜,还有的人叫牛菜。我最不明白北方人为何叫青菜为白菜,我见北方的白菜,叶为淡翠色、茎为白玉色,我们南方叫黄芽菜。后来方知白菜有大白菜和小白菜之分,北方人称青菜为小白菜,大白菜就是可做韩国泡菜的那种。我喜欢青菜一直那么青着。我认识不少叫小青的人,以前觉得小青这样的名字很普通,现在觉得小情趣里有大意境。就像诗人大草的一句诗“白菜顶着雪”,这就是大意境。可青菜长大了也会开花,那花也很好看。我不吃开了花的青菜,因为我不吃花。想到有人用茉莉花沏茶、栀子花炒菜,一沏一炒真有点水深火热,就没了兴致。
以前我把茄子叫做米饭的情人,再想想米饭和青菜更门当户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配得上南方第一蔬这个称号。所有南方人的记忆里,都有她的倩影,她是南方妈妈平生做的最多的菜。我说不上是苦孩子出身,但八十年代的饭桌上不可能天天鱼肉。小时候放学回家盛好米饭一看桌子,免不了嘟哝一句“又是萝卜青菜”,可不管你愿不愿意,青菜几乎是常有的。倒是秋冬之际,有一种大头青,虽然矮墩墩、胖乎乎的模样有些“愣头青”,但它经过霜打后,稍微多煮一会儿就能吃出肉的味道。我还喜欢青菜配脂油渣炒。青菜油亮油亮的,渗透了脂油的香。
宋人朱敦儒有“自种畦中白菜,腌成瓮里黄齑”。南方人以米饭与粥为主食,青菜下饭,咸菜就粥(虽然我后来也喜欢吃点辣,但只能是偶尔,如果连续吃几餐,就很不舒适。我的肠胃已经习惯了稻米和清淡的苏锡菜)。由于那个年代冬季蔬菜的匮乏,每逢腌菜之时就准备越冬了。南方人腌菜,一取大青菜一取雪里蕻。在陶缸内铺层青菜撒层粗盐,盐放多少,看主妇的分寸,小孩子洗干净脚踩在青菜上将它一层层踏透,最后加一块石头压实,经过十多天的浸渍,就可取食。如今在餐桌上,期待一道青菜的到来是那么漫长,它不再委屈于我儿时的埋怨,于山珍海味间再次显示了江南第一蔬的地位。我周围的人,还老是对我好奇,为何最爱喝的汤是咸菜汤。
你我的居所,早已相邻住着蔬菜的大棚。曾经各住天南地北,吃不同的五谷杂粮,现在仿佛只住在一个叫城市的地方,喝同一杯牛奶。我的房间常年摆着一盘水果,偶尔发呆望着它们时突然惊觉到一种妖娆,它们仿佛不是水果本身,而是一些伪劣的花瓶。草莓、香蕉、芒果、西瓜、蜜橘、甜橙……它们同时出场,就像新疆挨着台湾,就像春分挨着秋分,版图和季节显得有点凌乱。这个农业智慧泛滥的年代,我再没有守侯季节的热情,比如对我来说,春天是韭菜炒竹笋的清新之气,初夏的明媚在于红草莓的香甜之感。
当那些美丽的昆虫仅因最低的生存之需被类而分之为益虫与害虫的生命形式时,我对这个家园充满了不安全感。我信任那些被虫子噬咬过的青菜,与卑劣的农药无关。农药,源于人类的仇恨情绪与不自信,为了对付小小的昆虫,绞尽脑汁搭起了“积木”,这积木一坍塌,会压死搭积木的人(在核爆炸中所释放的锶90,会随着雨水和飘尘争先恐后地降落到地面,停驻在土壤里,然后进入其生长的草、谷物或小麦里,并不断进入到人类的骨头里,它将一直保留在那儿,直到完全衰亡。同样地,被撒向农田、森林和菜园里的化学药品也长期地存在于土壤里,然后进入生物的组织中,并在一个引起中毒和死亡的环链中不断传递迁移——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我为什么在写一棵青菜的时候,记录一段如此惊心动魄的沉重文字?我想,如果能遇到一位守旧而憨厚的农民,一瞥见他沉甸甸的担子里是那亲切的大头青,我会被一棵进城的餐霜饮露的青菜的内心打倒。
青菜是故乡写给我的第一封信。我炒青菜,从不用刀将她切段,而是一叶一叶地掰开,那是一句句耐读的信。暇间还可想想故乡那一畦畦惹人喜爱的碧绿,想起母亲们在筛子里和竹竿上铺放、晾晒青菜的状景,那里有她们勤俭的一生和储备的忧患……而此刻,还未学会发音的孩子,听我喊到青菜,他却也能对着墙壁上《幼儿识水果蔬菜图》的二十种图片,欢跃地用小手准确地拍了两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