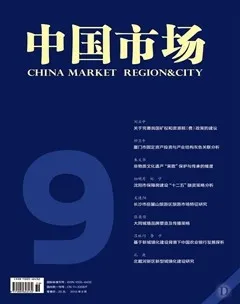传统与现代:农民工制度性支持网络研究
[摘 要]农民工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对其社会关系网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民工进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重新构建新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的过程。对于一个刚步入城市的农民工,他的对外沟通主要是通过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关系网络来实现的,而这种“关系网络”又贯穿于农民工的再流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仅仅维持在传统的社会支持这一层面,而现代性的社会支持严重缺乏,制度性支持网络的失衡现象以及目前传统性社会支持网络的局限性都为农民工今后的城市生活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农民工;制度性支持;社会支持网络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6-0080-03
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农民工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群体,这一群体的出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他们在工业和城市社区中的作用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并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要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最现实、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对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系统。这个社会支持系统是为农民工全面发展服务的手段,它必将有助于全面改善农民工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提高农民工的心理素质,发挥农民工的发展潜力。同时,它还必将有利于城市管理,稳定社会公共秩序。考虑到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建立一个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事业单位为基础,以街道、社区为纽带,以血缘、地缘等初级关系为依托的农民工社会支持系统是比较理想的选择模式。也就是说制度性支持网络(包括社会政策、社会组织、社会服务等)的建设将成为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 农民工制度性支持网络的现状描述
2.1 非正式组织资源的匮乏
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可以利用的非正式组织的网络资源十分有限。从一个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和作用看,正式组织本应当是农民工寻求帮助的最好资源,而且是首要选择。然而,经笔者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工可以利用的组织资源并不多。大部分企业未建立劳动争议委员会,许多农民工甚至不知道劳动争议委员会为何物,许多企业也未建立工会组织,即使有些企业建立了工会组织,也可能没有向农民工敞开服务的大门,真正得到过工会组织帮助的农民工很少。甚至有些组织不但没有帮助农民工,反而还常常侵害了他们的权益,使他们时刻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求助无门的情况下,少数农民工则尝试寻求其他非正式组织的帮助,而绝大部分农民工只能依靠自身的初级网络资源来寻求保护。农民工的初级网络资源主要是他曾经的工友、现在的工友、朋友或者是亲戚老乡等,这一网络的特点是内部信任度比较高。
为何非正式组织在为农民工提供支持与帮助的环节显得如此薄弱呢?关键是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城镇政府往往只把解决本地居民的工作问题作为重点,农民工进入城镇后,很难享受到当地政府提供的服务;而市场运作化的服务网络体系虽然较之正式组织有一定的改善,但是高昂的服务价格让广大农民工们望而却步,也使农民工对市场失去了信心,最终只能依靠自身的社会网络体系寻找工作。经以往的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就业求职信息都是通过已经在城里或正打算去城镇工作的老乡或朋友获得的,通过这样发散的传播,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深圳市的出租车司机大都是来自湖南省郴州市。这种由亲缘或地缘关系所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对于农民工来说更亲近,也更容易被接受。
2.2 制度性支持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中国的特殊国情导致了在就业制度和户籍制度上的缺陷。由此衍生的相关制度如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等,都受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理应享受同等待遇的农民工却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社会公共资源无法享受,正常权益遭到无视与损害。
其次,以户籍制度为依据的城市管理体制使农民工成为无城市归属感的群体,这样便使得社会融入尤其困难。城市政府的行政化管理对农民工这一特殊人群也采取了特别对待的处理。诸如在治安管理等方面,农民工群体往往被排在重要防范人群的首位,而在社区管理和福利方面,农民工群体却无法真正得到一个居民理应具有的权利,是政府的政策将把农民工从城镇居民中分离了出来。
最后,户籍制度的历史永久性形成一种不良的社会意识形态。户籍的城乡分别加深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身份区别和自我认同。两种不同户籍身份产生了一定的标签效应。上述众多制度上的缺陷不仅仅在造成了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在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更造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社区的困难以及沉重的心理压力。
2.3 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与维权渠道
农民工群体中不少人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年,却并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报酬,但是却由于诉苦无门,只得将苦果子往自己肚子里咽。农民工这一群体虽然仍还称为新兴群体,但是其存在的事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政府部门却并没有将这一类群体加以重视与关怀,在政策的制定与修改上,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已经远远落后了,大多数农民工都无法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维护他们自身的权益不受侵害。而且即便有一定的政策支持,农民工也很难获得真正维权的机会,因为农民工消受不起这高额的维权费用,政府政策的滞后性和维权渠道的不完善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农民工拿不到工资集体上访,劳动工伤问题、社会保险等,这一切都需要详细斟酌后加以解决,政府必须给农民工们一份满意的答卷,因为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我们现在优越的生活条件。
3 农民工制度性支持网络产生的影响
3.1 社会排斥和社会权益侵害
由于农民工是外来者,他们除了面临生存困难、工作状况恶劣之外,还常常面临种种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排斥主要表现为针对外来人口的办证、收容遣送和与之相伴生的罚款等。经相关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农民工都曾有过被排斥或被歧视的经历,诸如人口流动频繁的火车站汽车站检查、社区活动的参与等,农民工最起码的人格尊严都无法得到保证。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还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来限制、排斥农民工进城就业,其做法主要有清退、收费和行业限制。清退是指辞退没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外来农民工,将其岗位转让给本地劳动者。收费是通过向雇用农民工的单位或向农民工个人征收就业管理费、暂住人口管理费、就业调节金等,人为提高他们的就业成本,最终达到限制农民工就业的目的。各种证件的办理实际上是加大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难度。
除了社会排斥之外,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还常常得不到保障。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侵害情况主要包括: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克扣或无故拖欠工资;收取押金、扣押农民工有效证件;强行加班加点却不付给延长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不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具和劳动保护设备、女工和未成年工得不到特殊劳动服务;务工者患职业病、因工伤伤残甚至死后,用人单位逃避责任、随意辞退或开除务工者等。从调查情况来看,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侵害还是比较严重的。27.3%在找工作者使用了押金。47%的用人单位没有和农民工签订合同,有47.3%的拿不到加班工资。如何更好地利用非政府组织去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显得迫在眉睫。
3.2 现代城市制度性支持网络的低效
农民工进城后,他们的血亲关系基本上都在农村,同时由于工作时间普遍很长,工作稳定性不高,经常处于漂泊的状态,他们与其他邻近的城市居民既没有业缘关系也没有相同的身份地位,因此很难建立密切的地域关系,邻里关系对他们的意义不大。他们在城里工作时,也会因为地缘和业缘的关系而结识一些同事。但正如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个人从来都不能自由地选择他们希望交往的对象。社会生活对他们施加的限制影响了其交往对象的选择。这些在城市中社会地位低下的农民工所交往的对象基本上是与他们一样的农民或相似的社会阶层的成员。交往地位的同样低下使得农民工很难从这些社会支持网络中获得诸如找工作、升迁、遇到不公正待遇时给予帮助或合伙创业等工具性的实际帮助。可见,农民工进城后所结交的同事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同事,并不能为其城市生活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3.3 社会保障的缺失和等待
“社会保障是作为社会运行的稳定机制而发生作用的,是为解决工业化以来现代社会结构变动中的一些具体突出的社会问题而提出的对策性措施”。社会结构的转型促使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而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也推动着社会结构的转型,二者是相互促进的。现有的社会保障网络,是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主要面对城市居民;而农村主要以家庭保障为主,并未建立以社会保险为核心的社会保障网络,因此,城乡社会保障具有明显的二元化特征,农民工被排除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仅享有留在农村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问卷中,当问到城市生活中的主要困难时,排在前列的分别是工资太低(44.5%)、找不到好工作(29.7%)、不能和城里人享有同等待遇(29.5%)、看不起病(19.4%);而在回到农村的理由中,年龄偏大不好找工作是一个重要原因。
3.4 非法维权的“自救式犯罪”
所谓农民工的“自救式犯罪”,是指当农民工的生存、发展受到威胁或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他们以犯罪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或权益,属于非法维权。关于农民工“自救式犯罪”的原因,刘雯等(2004)作出以下解释:第一,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视性做法,“门槛”过高,加重其“相对挫折感”;第二,对农民工工作和生活过程中合法权益保护的缺失,这是主要的、客观层面上的原因,使不少农民工的人身权利受到非法侵害;第三,农民工寻求合法权益保护的体系不完善,立法、执法过程都有缺陷,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于是,犯罪往往成为自我救助的最后手段和唯一办法。
4 结 论
一般而论,受地域条件和职业的限制,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主要是在亲缘、地缘、业缘范围内建构的,并呈按亲缘、地缘关系逐渐外推的趋势。并且,农民进城前后的社会支持网虽然有所变化,但变异不大。也就是说,农民工在进城前后生活世界的构成过程中,以信任为基础的强关系始终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当然,在原有初级关系网络基础上,再逐步建构以工具理性为取向的次级关系网络,这是农民工力图获取更多资源的必然性选择。政府除了要注重制定有利于农民进镇的就业政策及其他社会政策外,还应发挥工具性支持的作用,即在就业方面对农民工多加指导,推动市场组织和就业服务机构的建设,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和渠道的支持,同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必须得到妥善解决。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李树茁,杨绪松,杜海峰,等.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刘豪兴.农村社会学[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4]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6]李迎生.社会保障与社会结构转型——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7]林南.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8]曹子玮.农民工的再建构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J].社会学研究,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