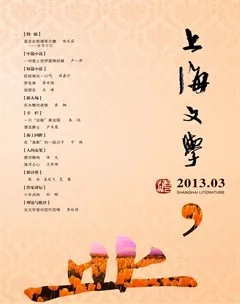在“海影”的一段日子
淮海路上有个海影摄影图片社,以售买八角五分一卷的120胶卷而闻名。它位于淮海路雁荡路附近,与培丽土产商店相邻。“培丽”在“文革”时改名全国土产商店,以出售上海及江浙土产闻名,而“海影”则以出售明星图片和廉价胶卷闻名。两者知名度不相上下,只是顾客群有所不同而已。
上世纪60年代某年秋,我因休学在家,由街道组织去参加劳动。可能因我曾替居委主任王韵兰(漫画家丁浩的太太)印放过照片,承她的情,被安排到“海影”,每月约有十元左右的劳动津贴。
“海影”是家合作企业,即由过去的照相馆小业主、雇员和若干个体摄影工作者等混杂在一起组成的一家小店,属于服务公司。那时上海有商业一局和二局,统管各区百业,其中粮油店由粮食局另管不计,其余行业便各自划块组成公司,如小菜场属副食品公司;各类酒家属饮食公司;食品店、烟纸店、老虎灶等属烟杂公司,还有果品公司、服装公司、五金交电公司等,具体我也搞不大清楚,而清扫垃圾、倒马桶还有沐浴理发则归服务公司,属最低档的工种。我不明白为何图片社也会属于服务公司,又没地方去问,问一下人家还会嫌你多事。总之当时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块,也有党委、支部等一系列的组织。
“海影”是家前店后工场的向北单开间门面小铺。大门是弹簧门,设在左侧,右面则是一个大橱窗,里面陈列着一些明星照片和胶卷相纸等。进门可见一“L”形柜台,长边在西墙,贴靠对外橱窗,短边则在尽头有块翻板,下面有扇小门。翻板翻起,职员便可推开小门进入柜台后;翻板搁上,又变为柜台一部分。从短柜台上方开始,有一个阁楼。长柜台后空间仅容一人站立,约莫二尺不到,短柜台后,有一个写字台打直贴墙放置,两边都可坐人,写字台右则是后门和上阁楼的扶梯。出了后门,通过一个小天井便可进入工场。
去报到那天,见到了“海影”的经理。他叫徐方尧,四十多岁样子,白白胖胖,理一个小平头,一只眼斜吊着,看起人来似乎在斜视着你。他操一口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见到我倒很客气,简短地讲了一下他们的工作范围,说是以前他们只是做图片生意,50年代,明星辈出,什么白杨、张瑞芳、王丹凤、王晓棠、舒绣文、赵丹、王心刚,顾也鲁、金焰等;唱绍兴戏的毕春芳、戚雅仙、尹桂芳、范瑞娟、徐玉兰、王文娟等等,也挺八卦的。徐经理说他们的三吋照片很受欢迎,除了门售外,更多的是批发给小贩,但近年都要讲革命,转了做江姐、青春之歌,但销量不好,所以生意差了好多。现在主要做相片冲放,售卖电影胶卷零头,外接修底、修相机等业务(那时他忽然改口,不说“生意”而称“业务”)。我当时想,倒底是合作企业,心心热热还是旧的一套做生意,须知当时政治空气已很严峻,能这样说的人已不多了,我顿时觉得这个经理虽是个党员,倒很有个性。
接着他便给我介绍各位职工,使我有点受宠若惊。有一个叫张志岳的,行内小有名气,是专门搞外拍的。那时工厂企业有什么大会或纪念活动,都要叫照相店或图片社外拍,当然冲放的生意也一并算上了。因张有点名气,而这业务又是一大收入来源:拍摄是一笔收入,更多的是稍后的印放,数量很大。所以张老师算是“海影”的台柱——照相行业不称师傅而称老师,大概是心理上他们以为师傅都是手作工,不像他们带点“艺术”吧。
接着介绍翁老师,说是专门修花点兼着色老师。翁老师性格和善,慢吞吞的,做什么事总要先说一句“慢慢来”。他在阁楼上有个写字台,台面上安了一块乳白色玻璃,下面有柔和的灯光打上来,他就常坐在桌旁修底片或拼接印图片用的大底片。修底可是一项精细技术,将2B至4B的铅笔磨尖后,把底片人像上的皱纹、斑点等都能修得光洁,犹如如今的做Facial,当然放大后的照片或报名照上的花点也归他修。徐经理又说,我们“海影”因店堂小,没办法搞人像摄影,像翁老师那样精堪的技术,现在行内已不多,年轻人没他这份耐心,所以许多照相店都外发给我们修底和着色。
又介绍了营业员顾老师,顾老师约三十多岁,我一看有点惊诧,活脱脱就是个赵丹,十分俊朗。徐经理也笑着说,这是阿拉店里明星赵丹,一个人在陕西路分店做。“海影”在淮海路近陕西路原卖湖北点心的江汉食品店旁,有一家豆腐干大小的铺头,仅一米五宽,也只能一个人撑市面了。据说有不少女顾客特意来帮衬,可见即使在最严峻的政治形势下,俊男永远是受欢迎的。不过小顾的摄影技术也相当好,对相机行情也十分熟悉,出身大人家,有钱朋友不少,常有名贵相机傍身,到“海影”也只属玩票。
最后介绍一个缩在角落的老郭,叫他老郭是因为他是小业主。这老郭下巴特长,戴副圆边眼镜,似30年代文人。原来他也只是摆个小摊档,专替人修相机,公私合营后进了服务公司,定为小业主。后来时间稍长,同他熟稔后,才发觉小小“海影”,真是卧虎藏龙。他学识渊博,修相机技术高超,实是个人才,我也向他学到了不少本事。他教我如何修叶片快门,如何排好快门片,特别在安放最后一片叶片时,要插入第一块叶片之下,很容易整个翻盘,他教了我一个土办法,即用胶姆糖搓成细条,轻轻把已装好的叶片黏成一体,这样就不怕散开了。他尽心传授他的实际经验,我也拚命学习。他有的是土办法,例如有一位顾客在镜头前安了块中黄滤色镜,但问了几家店都取不下来,因边太窄用不到力。到了老郭手中,只见他取出一块干净的塑料人字拖鞋底,吹了吹尘,整块按上滤色镜,一转就转松了出来。我不禁呆了一呆,这样也行?他又教我如何设计折合一个皮老虎,以替换旧的破损的皮老虎。那时大多相机是快门置镜头上,镜头至机身用皮老虎连结,后来我自制一个放大机,镜头上下移动也是用自折的皮老虎连结的。他还教我如何修理卷帘式快门,我自己也曾修过好几个135相机,有58Ⅱ型,也有德国康泰克斯等。58Ⅱ型听编号就是大跃进产物,照Leica做的,镜头是f3.5,当然性能还不错,但镜头质素同Leica没法相比,对光晕简直无扼制,高光部分常会产生一大堆光晕,做工也粗糙点,但对中国当时的疲弱工业来说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了。它的一个致命伤就是牵引帘幕的一段丝带易断,可能材料没有测试抗疲劳性就用上了,这同德国工业严谨的选料、制作和检验还有一大段距离。牵引帘幕的丝带脱落故障,需拆开机身,用虫胶液黏牢——那时502快干胶还没有发明出来,虫胶液是用阿拉伯虫胶片浸酒精溶化而成,强度较高也快干。后来即便离开了“海影”,我和老郭依旧是忘年之交。
到得后面工场,徐经理又唤出一个叫边海华的老师,说是“海影”的冲晒全靠这位老师领军。我一听竟有人姓边,印象深刻。他戴了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人很小样,一听经理这样介绍,也客气了一番,说都是老徐指导的。我想徐经理也真会做人,借给我介绍认识,也对属下笼络了一番、鼓动了一番。
还介绍了一位江大姐,白白嫩嫩,丰丰满满,像个贵妇,也是三十多岁样子,说是专门冲软片的,见到我也很客气。还有个学徒叫朱国强的,个子蛮大,暗室里有了他,空间似乎也逼仄了一些。
通过一番介绍,我觉得“海影”像个大家庭,大家十分和睦,经理深得大家爱戴。我第一次进入社会工作,虽说是临时性质的劳动,但也感到有幸进入一个温韾的集体,从经理给我逐个介绍员工,我觉得受到了尊重,也很想尽力报效。
第一天的工作是切照片,手边一大叠十二吋相纸,整张相纸印满了三吋明星或戏曲剧照的相片,每张相片都要留下约一分的白边,切一二大张当然没问题,但整整一天都是在切这种相片,切得手也酸了,头晕脑胀,切好还得归类叠齐装袋,这个时候才算是放松一下。我很卖力,顺便将暗房送来上好光的顾客照片也一并切好。有的顾客还指定花边照,那就要换一把七吋刀刃的花边切刀来切,那时似乎还很流行。
其实看各式顾客照片也充满乐趣,常会见到一些十分趣怪的表情。但大多数照片还是十分“土气”的,衣着不外中山装、白衬衫,女士则以绒线开衫为多,来来去去没几个式样,没什么出格的照片,基本上很朴素。
切大图片并不着急,因这些都是以前印好了没来得及处理,现由我来清理存货罢了。做了好几天,经理也很满意我这个勤奋的廉价劳动力,由于平时也不是天天要切照片,空的时候便叫我站柜台。
站柜台可以见识各色人等,有些常客有事无事都要来转几圈,有些天真可爱的小学生初学摄影,也有些骄横不可一世的小开,当然也有嗲滴滴的小姑娘,她们正在最爱被人拍照的年纪,还有些斤斤计较的小市民……真可谓见尽了人生百态,是别的工种不易碰到的。
站柜台是真的一天到晚要站的,因顾客络绎不绝,难得有空闲。主要是开单:接一卷软片,注明是单冲还是冲印。那时冲一卷软片大约一角五分,印一张135豆腐干大小的花边照片要三分,连冲带印约莫一元出头。当然也有6×6或4×6公分的120底片冲放,价钱稍大点。而放一张三吋大小的照片则要一角七分,两倍大小的五吋照片(俗称PostCard)要四角上下,也不成倍数。通常是隔天可取。取照时顾客盯牢豆腐干看半天,还会挑几张来放大。所以服侍一个顾客也要花不少时间。
另一主要工作是免费替顾客装软片。“海影”常年供应由保定电影制片厂的21定全色片片头裁剪的软片,只卖一元五角一分一卷,比正品要便宜一元多,而且质素不错(那时一元钱可派大用场,这也是徐经理去搞来的),当然是不连软片盒的。顾客通常会带来自备的软片盒,但因没暗袋,就需要我把黑纸包的软片在暗袋里拆开装入软片盒,门槛精的还要求我摸黑把软片装上相机。啥道理呢?因为一卷软片的长度可拍三十六张,但因片头有两张长短会在装机时曝光掉,在暗袋里装时,要有点技术才能“偷”到这两张,卷片时牵引软片,不免要按快门才能移动,但还可等“牙齿”上妥后再倒片,要凭感觉倒到正好位置,否则会脱掉。这也是熟练工,做得多了,凭倒片时的力度可感觉到。经我安装后,通常一卷软片可拍三十八张,有时长度富裕点,甚至可拍到三十九张,这对顾客而言,无疑是一件捂心的事。
说起卖软片,“海影”一大卖点是不时会供应八角五分一卷的120等外品胶卷。120相机当时为多数人拥有,因为它印一张面积大,只要六分钱,不用另外再去放大,但一卷软片只能拍十二或十六张,故软片的成本较大。精打细算的上海人哪会放过这价廉物美的等外品呢,所以这成为热销货,卖的时候队伍有时会排到几个门面外的春江生煎馒头店。
当时社会上流行“走后门”,有此奇货,自然成为“开后门”的强大武器。隔壁“培丽”明天会卖桂圆了,小李一定会过来带个口信;有外国电影放了,对面淮海电影院小张也一早每人两张送到;对面益民百货店有搪瓷烧锅卖了,老陈立刻过来登记,谁要买快讲一声。自然这些人几时要“八角五”,也是一句话。通过卖“八角五”,我也搞熟了周围商户的关系,自然我的小兄弟无一例外都有照顾。这“开后门”的事,经理也眼开眼闭,反正大家银货清爽就无事,那也是当时的风气。
再有一件有意思的事,便是有不少“老克勒”常会来店里闲聊。当时淮海电影院旁边还有一家“大美”,也出售摄影器材,“文革”中因明显是崇美的招牌,故改名叫“红艺”;另一家新光光学仪器商店是以前的“万金记”,在康绥公寓东侧,不到“燎原”的地方,大概是中华烟行西侧,现在的上海钟表行其中的一个铺面;还有一家分店是在光明邨前面,有幢尖劈型的建筑的铺面,旁边有一小弄可通成都路,都是净卖二手相机及附件。“老克勒”们往往手持林哈夫、M3、罗莱来卖弄,从解放前讲到解放后,口沫横飞十分有劲,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知识,对当时各类王牌相机也认识了不少,有时同小兄弟吹起牛皮来,多了不少资本。哈苏那时是江青专用相机,单镜120反光很威的,市面不会直接进口,如有也只能是二手货,由港澳带入,“大美”不会出售,“万金记”倒有可能。1980年代前期已有进口货卖,但要外汇券,80年代后期则开放多了,外汇券渐渐退出市场,故市面上有时会有哈苏Hasselblad出售也不出奇。
别把“海影”店门口贴的“精冲软片”当回事,有时我到后面工场帮忙,见到珠圆玉润的江大姐冲软片。江大姐一眼看上去还算漂亮,但看到她的手指,便不免倒胃口,手指根根像萝卜头,粗粗的,且是暗褐色的。原来所谓精冲软片,便是把十几卷软片,两头用木夹夹起,用一个大搪瓷盆,这些软片便如带鱼般浮在显影液里,江大姐就用手不断翻打,搅拌,也不戴手套,天天受显影液的浸润,难怪变成棕褐色的“萝卜头”了。有盏微暗的红灯照着,像汆油条似的,哪一条颜色够深了,便捞起来过一过水丢到定影水里,其中也没过急停液冰醋酸,定影液干脆放在一个大缸里,上面横架着一条条铁枝,木夹上有个钩,软片就挂在上面浸入水缸。而显影液也只是用最蹩脚的D-72来冲120,用很普通的D-76来冲135,有时也不大分。显影液成分就是米吐儿、几奴尼、亚硫酸钠和溴化钾等,D-72中米吐儿用量较少,比较经济,冲片、显相纸都可用,用得较广泛。所以,不要说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商业噱头就不大可信,比我自己家中冲软片不知要粗疏多少了。
那未印照片又是如何呢?未去“海影”之前,我自己家中也有放大机和印相机,印相机是一个密闭灯箱,上面有一块二折翻板,底片和印相纸叠齐,放上有遮挡格的灯箱磨砂玻璃,先翻下一折,看看有无歪斜,然后再压下第二折,开灯关灯便成。这种速度在店里是不能应付的。“海影”的印相机没有翻板,但有个脚踏开关,一手把底片和相纸叠好放在遮格上,抽手后另一个手掌便直接压上去,接着灯一闪便成。因手势熟练,绝对没有印歪的事。曝光时间允差很大,但他们掌握得很好,即使偶而有不足或过头,或选用相纸软硬不当也不怕,因为后面有徐经理处理。
而大型图片经技术革新之后,是反过来印的,一整张预先做好的大底片用玻璃胶纸贴在平板磨砂玻璃上,玻璃上方装了几只灯泡,还用块奶白玻璃隔开,以使灯光均匀,整个装置装在一个箱子里,可以拎上压下,但有条弹簧平衡,使拎上时省力。下面就是一个托盘,可以定位放下一大叠印相纸。有个微动开关,压下灯室时,就有延时电路自动曝光,所以调整好时间后,阿狗阿猫都可以操作,我也印过多次。
徐经理在行内以暗室技术一流而享名,“海影”的放大照片,特別是大幅照片,如十二吋的人像或龙友的二十四吋风景,都由他操刀,经验很丰富,往往做一次试条便能取得合适的曝光。“海影”的一个放大机是斜臂式的,很扎实,记得大概是Wella牌的。徐经理放大照片时通常会把镜头光圈收得很小,这样便可延长曝光时间,但要求放大机够稳重,台子也要够沉,这样才可在曝光阶段不受震动。行内都用默念数字来记时,他们都能在一分钟内误差不超过一两个字,可见心态控制得很好。徐经理在曝光时会视照片的意境,用天女散花、高深莫测的手势来使高光部分层次尽显,阴暗部分又曝光适度,手法熟练但又看不出道理,然而最后的结果总是很完美。这也是长年浸淫此道的造诣,所以那个边老师遇到重要照片时,常会请徐经理出马。
在显影定影后,他们都有一个法宝就是“山埃水”。曝光过头,照片太深色了,就用山埃水减薄一下;曝光不够点,便要显影时间长点以逼出点黑度来,但此时白边会发灰,也可用山埃水来消去。山埃水有个好处就是不大会影响层次,不像铁氰化钾(赤血盐)那样会露底。我想这山埃可是奇毒,他们直接用手涂沫,不怕转头吃食中毒?但见他们活得好好的,也不敢去问。现在想想那时代人们对各种化学品禁忌似乎不大在意,很随意,对长期接触化学品是否会造成不良后果也并不大清楚,有时“无知者无畏”真说对了。
放好的照片经水洗后,除了绸纹纸、绒面纸、亚光纸等厚底相纸外都要上光,这样出来的照片光可鉴人,特別挺括。我以前在家只是用块玻璃,照片药膜面贴在玻璃上,再盖上一张厚吸水纸,用橡胶滚筒滚几下,然后放在阴凉地方让其自然风干,最后,有时照片会自己落下,有时需用刀片轻轻揭起。但经常会有难看的水泡痕,有时玻璃没用熟或不干净,照片还会僵黏在上面,这时甚至用水浸也不能浸开,只能报废。而“海影”则用电上光机,照片贴在一块镜面镀镍的圆凸铜片上,上面用块帆布拉紧,一通电,水蒸汽逼出,几分钟便可取下。当然大量生产的十二吋图片就不用电上光机了。
有次我搞到个镀镍铜皮,就自己用白铁皮敲了个弧形的支架,装上龙头细布,放在煤气上烘,也一样行,那时还很得意,但毕竟要在旁小心伺候,所以只能应急或阴雨天用用,大批的照片还是用玻璃上光的。
“海影”的批量图片上光也是用玻璃,那个上光工场是在金陵路重庆路口一幢朝南街面房的假三层上,我也去那里历练过一番。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搬玻璃,每一块玻璃40×60厘米见方,一黄鱼车有多少块搞不清,一共搬了两车。起初两块一搬,要搬到三楼,好像太慢了。那时我才二十岁不到,真是年轻力壮,一身蛮力,于是一口气搬四块,噔噔噔搬上三楼,只是觉得,既然叫我做了,快点做完才好。那时人单纯,一点也不惜身,谁知第二天,腰痛得不得了,立也立不起,去地段医院看了看,说是腰肌劳损。医生问我,这么年轻怎么会劳损的?我只能苦笑一声。劳损很难痊愈,一直拖了半年多才好转,后来间中也会发作。
那个上光房由一个状似巫婆般的老女人独自负责,据说是外包工,不属“海影”编制,她的任务便是把浸在水里的照片贴在玻璃上,刮一刮,再把玻璃放到架上。为什么这些图片上光后永远那么光,一点气泡也没有,而且风干后自动掉下,绝无黏牢之虞呢?原来照相业有个秘诀,那就是用猪苦胆——我只知他们叫猪苦胆,有股腥臭味,还真是到菜场收集苦胆汁,再加上一些酒精等调制出来的。这在以前的摄影小册子上从没提起过,也不知谁发明的,我讨了点猪苦胆,回家去试一下,也不需用什么滚筒压,只要轻轻用把尺刮一刮就成,真是个好办法。只是过了不久,家中就有股奇臭,赶紧倒掉算数。
上好光的照片切好后,都要经翁老师过目,他约莫五十开外,一副老光眼镜吊挂在颈上,很和善。他收到照片后,会架起眼镜,逐张看一看,有白色花点,就用支极细的狼毫笔点一下。他有块白色瓷砖,磨了墨,拖开后,墨迹会有不同深浅,他点的时候会选择适当的浓度,有时还会用唾沫再把墨迹擦开,唾沫留在人家照片上他也若无其事,笑说唾沫最干净了,哈哈!他的拿手功夫是着色,分水彩和油彩,水彩着色快,但难度大,而油彩着色很费功夫。通常他先上肉色,点红唇,画眉毛,用的是油画颜料,工具是竹签,上绕一小团棉花来擦匀,大面积就用棉花团和拇指下的那团大肥肉,用起来得心应手,要抹何处就何处,特別是上胭脂时更见功夫。我也跟他学了几招,回家自己试着着色,看看也挺满意,后来拍拖时,这也是个讨女朋友欢心的绝招。
据网友老爷叔说,1986年,他和香港的中国广告公司摄影部有过业务往来,认识他们一个部门负责人叫翁安宁,原在“上海照相馆”(万象)做着色技师,自称其技术上海第一,很多明星都专门找他做。翁安宁对赌马很有心得,老爷叔跟他买过一次,赢了一千四百三十二元,哇,一世生意!自己再买,次次输,把“一世生意”全输光再不买了。翁安宁1980年代初到香港,90年代离开“中广”,自立门户开画廊,他曾为很多香港名人画过油画肖像,办过画展,属于非科班出身,只是画得“像”但技巧不入流那种。过了好几年,听说他患癌症,脑癌还是什么的,总之很严重,大约90年代末去世。
我觉得老爷叔所说的翁安宁,不像我认识的翁老师。翁老师为人谨慎胆小且很谦虚,不大会自称技术上海第一,还自立门户开画廊。1980年代中至少要六十开外了,要出外谋生也不合他的性格,短短几年成为赌马专家更不像他。不过时代变迁大,这种事也很难讲。
张志岳同我也很合得来,不去外拍时,同我一起站柜台,一起同那些“老克勒”吹牛皮,很是投机。我父亲以前也玩摄影,认得不少“龙友”,常有来往,我有时也介绍张志岳认识,他们早已认得的,那个圈子也不大。
每逢有外拍,他常叫我一起去,当跟班,帮他拎三脚架,背闪光灯。那时闪光灯不像现在那么轻巧,闪光灯盆有五吋直径,下面有个手柄,像大号手电筒,有根弹簧电线同下面电箱连接,光电箱中两个大电容就大得吓人,如加上一个蓄电池,同一只LV行李箱大小差不多,但要重很多。去客户单位拍照,照例有餐食堂饭吃,有红烧大排、油炸小黄鱼、青菜狮子头等招待,也算不错了。拍照时人人一套工作服或一套中山装,一本正经,照例是书记坐第一排中间,闪光一亮走人。有时要求用大底片,那就需借部黄鱼车,把架木制摄影机搬上去,镜头是一百八十毫米的大光圈长焦镜,镜片像小饭碗那样大,可以把头发丝拍得根根分明,用的是四吋或六吋玻璃底片,有专门的底片盒,还有个磨砂玻璃对焦盒,对焦之后便换上底片盒,一、二、三、笑!快门是用一个橡胶气球,按一下,“咔嚓”一声,同步闪光灯一亮就完成了。
我在“海影”劳动只短短几个月,过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海影”阁楼上也挂满了大字报,具体內容我也没有看到,想来也是对小顾的小开派头或者暗室中难免的风流逸事等大揭大批之类。后来风向变了,北京“红卫兵”开始“破四旧”,“海影”不知是被迫还是自觉,把大量积存的才子佳人戏照和男女明星相片当街烧去,一时火光熊熊,路人围观,我想徐经理一定心痛不已,不过为了革命需要,也不得不表现出对“红卫兵”的行动的拥护。
在“海影”这段日子可说是我第一次接触社会,竟是那么丰富多彩,那么记忆犹新,想想那时的人际关系还是很简单,也很融洽,人也朴素,不贪心,不攀比,大家相处愉快。现在想来,“海影”的一段日子还真使我受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