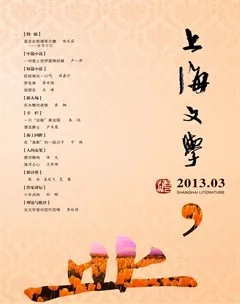一只“法眼”看法
老李博士毕业时,因为选择不少,何去何从倒也让我们踌躇一番。最终他痛下决心去法国,是因为他完全相信,我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所谓好地段的上海女孩,对于欧洲,对于法国,必然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怀。不能用虚荣心去解释,但是崇洋是肯定的。不是吗?我的大部分朋友听说我们要去法国,都说是个好选择,比去美国强。
但是,五年来的经历让我不得不重新来看这个国家。从法国的媒介,和那些到过或者没有到过中国的法国人嘴里,看不出和听不到中国的任何好,比较例外的只有那些商会的生意人。曾经和不同阶层的人就这个问题交流过,他们习以为常,因为法兰西民族就是个喜欢抱怨的民族,法国人喜欢批评,是为了使人进步。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幢房子,高高在上的法国几乎只是看到了厨房的垃圾桶。这就是法国人的眼睛。今天,我就想用一只这样的眼睛来看看法国,且让另一只眼睛暂时休息吧。
我们到法国的时候,小孩两岁三个月。一直不认为给小孩找学校是个问题,只是想着,最多去那些私人办的收费贵的。倒不是钱多得没地方用,而是一般来说,私人学校看在钱的份上,学期中间也比较肯收。这样,寒假以后我就可以去大学注册,先把法语攻下来。等到第二年的九月份,小孩正好三岁,可以入读不花钱的公立幼儿园,我再选专业拿学位。
家附近就有两家托儿所,一家挂着市政府的牌子,另一家在一幢小别墅里面,应该是私人办的。我自己比较倾向第二家,因为好几天我都带着女儿偷偷在底楼的窗口张望,里面的布置很居家,小孩也比较安静,看上去守规矩。市政府那家,很多时候只看到小孩拖着鼻涕在沙堆上疯玩。
打定主意后,把女儿和自己都打扮得清清爽爽,就去按门铃了。出来开门的应该是负责人,能略微用英语交谈。搞清楚我的目的以后,很客气地告诉我,没有名额了。我有些不太甘心,说,如果有名额是否可以马上通知我,我愿意付排位费。刚一提钱,那位女士就激动异常,给了我一个蓝色的小本本,然后找出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电话去那里。
洋洋得意啊,心里猜,她也只不过是打工的,肯定让我直接打电话给老板。回到家把小本本仔细研究了一下,又狠查了一番字典,原来那是南特市政府一个专门为外国家庭孩子服务中心的热线电话。难道是看穿我们这种亚洲人付不起学费,只配上公立学校?不管了,先打过去再说。
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完全不能用英语交谈,我就是不挂电话,管她听得懂听不懂,就说我需要给孩子找学校。最后,电话对面的人找来了会讲英语的同事,听了我的情况,让我直接去位于市中心的办公室。
第二天带着女儿去了,出来接待的略懂英语,告诉我全南特的公立托儿所都满了;私立的,也是一样。不过,她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去大学医院办给自己职工的托儿所问问,因为老李在那里工作,也许有希望。
老李的同事倒是挺帮忙的,带着他去了,带回来的信息是,医院的职工都至少要排一年以上。同去的法国同事自言自语说,看来,他老婆大肚子时就要来这里报名了。回到实验室以后,又跟已经有小孩的同事了解了一下情况,确实很难进托儿所。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家或者工作单位附近雇人看小孩,三岁以后就好了。
可是,我偏偏不相信,法国第六大城市所有的托儿所,难道没有一处放得下我小小的女儿吗?再去市政府的外国家庭和孩子服务中心。接待人员英语有限,我不管,那不是我的问题,反正不给解决,我就不走。最后实在没办法,他们给我预约了一个时间,说是从他们的上级部门临时借一个英语好的同事来半天,专门处理我的问题。
去了,大家客客气气。我有很充分的理由,全家刚来,没有任何朋友,都不会讲法语,大人尚可,小孩再这样下去,恐怕心理会出问题。我们这么急于给孩子找学校,是为了让她从小就接触法国社会,尽快融入。也许,他们早就商量过了,反正我一说完这番话,他们就说,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家附近的公立托儿所愿意让女儿一周去两个半天。
至于费用,我暂时睁开另一只眼睛看看。所有的公立和私立托儿所都是统一的,收费按小时,根据上一年家庭平均收入分成十几档。我们上一年在法国是零收入,所以每小时收费才几毛欧元。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但是如果有选择的话,我情愿多花钱。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再穷不能穷教育。
女儿小时候有比较严重的过敏,到了法国转用了新的奶粉,再加上气候寒冷等原因,经常咳嗽。我们不太确定引起咳嗽的原因,所以分别看了儿科医生和专科医生。这中间的过程很痛苦,因为如果没有医生的处方,就不能买到药。而一般如果没有严重的发烧等状况,预约儿科医生需要一到两天的时间。
在看了几次儿科医生以后,他建议我们找专科,确定过敏源。打电话去预约,竟然要三个月以后。没有专科医生确诊的情况下,儿科医生只能开一些普通的止咳药,而这些药,对女儿作用不大。
过敏的小孩最怕咳嗽引发哮喘,这些常识儿科医生不会不知道。但是,我想,他是不会为我们这样的外国人去冒险的,即使我跟他套近乎,说老李也在医院工作。不过,最终,他给了我们一个建议,如果小孩咳嗽实在厉害,就直接去急诊。如果确实是过敏引起的,那里的医生会开防过敏药和喷雾。
怕什么就来什么,某天早上,女儿吃了一条酱菜以后,开始剧烈咳嗽。立即飞车到大学医院的急诊室,下车以后那是一路飞奔啊!那条二百米的走廊好像有二万五千里那么长。到门口就被人家拦住了,让我们兵分两路,一个抱着小孩先进去,另一个去挂号处办理手续。默契啊默契,都没有四目相望,我抱着女儿就进去了。眼角余光瞄到老李一边向挂号处狂奔,一边摸了摸口袋确定钱包在里面。
到了儿科急诊,淡绿色的墙壁,很柔和。先出来一个护士,给小孩脱了衣服,量体温,测血压,大概是确定没有生命危险。接着又出来另一个护士,询问情况,我也听不太懂,就直接说过敏(这个单词英语法语是一样的,发音略有不同),然后掐着自己的脖子拚命咳嗽,再指指小孩。这种世界语大家都懂,那个护士笑着记录在案。然后,就让我们去另一个区域等候。
等候的地方有各类儿童读物和玩具,人也不是太多,两排十多张椅子都没坐满,估计前面也就五六个小孩。这时候,老李也办完手续进来了,看到女儿上蹿下跳玩玩具,挺意外的。女儿看上去精神还不错,只是时不时还有剧烈咳嗽。
我们是早上九点上下出门的,等啊等,等啊等,一直等到肚子都叫了,还在同一个地方等。在我们后面来的,有些已经被叫到小房间里去了。生怕他们漏了,或者搞错什么,过去问,说是没有漏。
看看时间,已经中午十二点了,这时候的女儿除了偶尔有一两声咳嗽,就是喊肚子饿。不敢走远,去走廊的机器上买了点心和水,女儿吃完躺在椅子上舒舒服服睡午觉了。过了一个小时,再去问,还是让等。
等得我都快睡着了,听见叫女儿的名字,赶快把她弄醒,去到小房间。进来一个护士,量体温,测血压。又进来另一个护士,询问情况。我再重复原来的动作,接着指指墙壁上的挂钟说,早上九点,早上九点。其实,说了也白说。
护士出去以后,又等了大概二十分钟,医生总算来了。这时候女儿已经一点也不咳嗽了,午睡以后简直是生龙活虎。和医生交谈以后,她也笑了。看看女儿没什么事,再加上听说老李也在这里工作,索性和我们聊天了。
原来,法国医院的急诊是分级制的。到了以后先看生命体征,如果有生命危险的,肯定是马上抢救;如果没有生命危险的话,根据不同的情况,分成若干等级。我自己猜,像女儿的情况,体温血压正常,咳嗽也没有到上气不接下气的地步,大概是排在最后一等的。
最后,那个医生给我们配了各类抗过敏药,还有一大瓶急性发作时需要的浓缩药水,并且语重心长关照我们,这些药让专科医生长配,以后再碰到类似的情况,自己给药,不用上急诊。我们解释说,专科医生已经在预约中了。她自己也笑了,说,我这次给你们配的药水,大概够用两年。
等我们从医院出来,去药房配完药,回到家里,正好淘米烧晚饭。
在法国人人都说法语,这是我的抱怨。法国人觉得这句话很好笑,我自己也是。很多时候他们会反问我,难道在中国不是人人都讲中文吗?是的,是的,我们都讲中文。可是如果面对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至少大家都觉得天经地义。在法国却不是这样,似乎只要你踏进这个国家,讲法语才是天经地义的。
去法国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把语言当成一个大问题,虽然之前也听说法国人不愿意讲英语。对于法语,我当然是热爱的,也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在法国这个浪漫的国度学习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是一件多么令人愉悦的事情啊。
但是,在还没有掌握这门语言之前,在法国我只能维持基本生存,因为去超市买食物不用开口。直到现在我还对老李的教授怀有深深的敬意,是他,陪着我们去银行开户口,为我们打电话开通电力和煤气,和警察局打交道办理居留证等等。
说起来简直不能相信,南特市政府专门办理外国人居留的职员居然不会讲英语。当然,去那里的绝大部分是来自前属殖民地的阿拉伯人或者黑人,他们是会讲一点法语的。可是,世界上除了法国和法属殖民地,其他地方的人不会讲法语是很正常的呀。
办理居留证本身就很繁琐,需要大量无用的材料。好不容易什么都搞定了,预约了时间去拿,我们说自己去就可以了。到了那里,还是出问题,我是完全听不懂他们讲什么,猜出大概意思是缺了一份什么东西。
一开始,我还比较顾及仪态,和颜悦色解释,我们不懂法语。没想到,窗口里面倒出来一句听得懂的英语,说是,如果你不会法语应该叫懂法语的朋友陪你一起来。我刚心里一窃喜,总算有个懂英语的,谁知接着又传出酸溜溜的一句,这里是法国不是英国,马大姆(Madame,夫人)。
“明白,明白,在我的国家我们也不讲英文。”
“你们讲什么话?”
“我是中国人,我们讲中文。请问马大姆,你会讲中文吗?”
“???”
“你不会讲中文,我不会讲法语,我们是否可以用英语沟通,马大姆?!”
“我要告诉你,我英语不好啊。”
“没关系,没关系,法国离英国比中国离英国近多了,我的英语更不好。”
可能是他们还从来没见过像我这么嚣张的外国人,连缺的材料也不收了,在护照上贴了打印出来的居留证就把我打发走了。出了警察局大门,我又把这几句话默默背诵了一下。还真是的,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很多,这几句话屡试屡得手,甚至到了第二年去南特大学对外法语系报名还用上了。这个系是专门开给要入读专业的外国学生的,秘书居然也不会讲英语!
精通中文的美国人克雷顿跟法国人结婚,他告诉我,在中国时,他只要一开口讲“你好”、“谢谢”,周围的中国人都会赞扬他中文讲得好。而在法国,即使他能讲不错的法语了,法国人还是抓住他阴阳性的错误。“说真的,我讨厌法语。”他最后这样对我说。
我说,我倒是不讨厌法语,因为我已经彻底发狂了。不信,去瞧瞧我家的墙壁和每一扇门,贴满了法语的动词变位和数字名称。因为在法语里面,从70开始不再是70,而是60加10,71就是60加11,以此类推一直到79;到了80呢,又不是60加20,而是4乘20,81就是4乘20加1,以此类推到89;90则是4乘20加10,91就是4乘20加11,以此类推一直到99。不把这些贴出来,我连支票都不会开。而在法国,很多地方,特别是一些非商业行为,只能以开支票的方式来完成。

快译通、文曲星、法语王等等电子词典,应该说是相当普及的东西,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弗朗教授对这东西非常反感,看到亚洲学生几乎人手一部,更是不住地摇头。有些考试是可以带词典的,但是碰到他手里,非用传统的大部头不可。有次,不知道哪个学生不识相,按出了声音,这下可把他彻底惹火了,不断咆哮你们亚洲学生如何如何。
公平一点说,法国的教授,至少我遇到的都还是比较敬业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时不时把你们和我们挂在嘴边。比如,在食堂吃饭,冷不防会来一句,你们中国人早餐吃什么。再比如,放假之前,会炫耀道,我们法国人冬天去滑雪。
我极其无礼,心里把这等教授统统划为“乡下教授”一类,以弗朗为代表。可不是吗?他住在离南特市几十公里外的一个百多人口的小乡村,每天从家开车二十分钟到火车站,然后坐四十五分钟火车到南特市,再倒两趟有轨电车到大学。从他的言谈,我比较敢肯定,他只出过国而绝没有出过欧洲。
我们外国学生刚开始学语言的时候,大家还都是用各色好好坏坏的英语来交谈。对于白人学生说英语,他还比较能接受,但对于亚洲学生说英语,他的反应相当大。私底下,大家已经摩拳擦掌,要找个机会杀杀他那不开的眼界。
有次,讲到魁北克的法语,他居然问我,知不知道魁北克有什么问题。不过,实事求是的讲,那时在校园里我是清汤寡水不怎么打扮,每天送完女儿上学匆匆赶去,身上油烟味甚浓。当时我法语虽然很有限,但是下定决心要让“乡下人”开开眼,于是用故事式地倒叙法:某年某月某日,我当时某岁,参加了一次很有趣的活动——中国上海的学生和加拿大魁北克的学生通过卫星进行对话。在对话之前,电视台还特意从外国语学院找人来教我们几句诸如“笨猪(bonjour)”之类的法语。为什么呢?因为魁北克省讲法语。在约定的节目录制时间,却收不到对方任何画面。那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正在闹独立,当天首府蒙特利尔全市罢工游行。
他当然不会死心,话题一转,指着另一个中国男生,让他说说世界上还有那些地区有类似的问题——也就是地区人民想独立,但是国家政府不支持。巴尔干、波黑、前南斯拉夫等等等等,那个“80后”男生用结结巴巴的法语几乎是把一战以后的东欧历史讲了一遍。我至今想起来,还深深地为他自豪。他的名字里碰巧也有个“豪”字。
接下来,有个巴西学生倒很搞笑,突然问了一句,我们来是学法语的,不是吗?大家哄笑。乡下教授唯有紧闭嘴唇,发出连续两声爆破,bon bon(好的)。
在法国租住的第一个房子,冬天雨季过后,一面墙壁开始发霉。家有幼女,所以决定搬。特地找来相关法律看,这发霉的原因如果是因为外墙没有保养的缘故,就跟房客无关。确实,外墙可以看见很明显有条缝,我们通知了房东。
搬家之前,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打扫,不夸张地说,肯定要比搬进去之前干净。一方面,不让房东有克扣押金的理由,另一方面,也不想给中国人丢脸。房东委托专门的公司来收房,检查下来完全合格。在所有的文件上签字以后,说是押金三个月之内就会以支票的形式寄给我。
三个月?是的。根据当时的法律,房东退押金的期限是三个月。两个半月的时候,打电话去询问,说是三个月期限还没有到。三个月过去了,还没有收到支票,再打电话过去问,说是会扣除部分押金,发票会随支票一起寄出。
好不容易三个半月之后收到了支票,押金被扣去一大半。发票上开着是粉刷发霉的墙面和修理地板。发霉不是我的事,地板的话,专门的公司检查过,文件上都有签字,就这样,还要扣我钱,太无赖了。
接下去,打电话也好,去信也好,就是不理。在法国的很多外国人就是这样眼睁睁看着押金被无理克扣,而毫无办法。有很多人,其实已经离开法国了,根本没有办法取回。还好,我们家老李是有工作的,因此长达两年的追讨就此开始。
先是收集证据,一年的房租单,水电煤气单,以证明我们没有拖欠。给房东的退房挂号信,以证明我们是按照法律提前三个月通知退房的。房子外墙的照片,谢天谢地,我们去拍的时候那条缝还乖乖地横躺着。房子租给我们之前的地板状况和搬走时的状况,这些都是由专门公司鉴定,有双方签名。
把所有这些交给律师,律师评估以后有百分之九十九胜算把握,然后通知房东,准备告了。房东不理,于是排期上告。这之前有个调解,直到这个时候,房东给我打电话,说愿意退回粉刷墙壁的钱。我当然拒绝。讲老实话,如果可以的话,我更愿意用拳头来解决这件事情。
再打电话来,房东开始东拉西扯问我们在法国待多久,有没有工作。气得我在电话里大叫:你们政府已经给我们全家sejour(居留)了,我们会一直待到你寄给我支票的那一天;如果月底之前收不到你的支票,我们庭上见,你还必须付请翻译的钱,我是外国人!
“Vous parlez bien francois,Madam.(您法语说得挺好,女士。)”废话,用得着她表扬吗?从那一天开始,我自己也觉得法语过得去了。接下来,她还居然要求分两张支票开给我。我真想说,如果她肯给我扇两个大嘴巴,可以不用寄支票。
不要以为碰到这样的事情是我们不好运,这几年下来,因为有前车之鉴,我们帮着讨回押金的,不下十起。
朋友夫妇,刚生完小孩,觉得房子不合适,马上要搬家。根据法律,这样是不对的,应该提前三个月通知房东,否则要赔偿三个月房租。后来,电话跟房东协商,他们自己找房客来住满三个月,当时房东答应得好好的。
等到搬家那一天,老李帮着车东西,带着女人小孩去了新住处。房东到来,突然说不同意其他人来住。如果要搬走的话,必须赔偿三个月房租外加押金不退回——这是很明显的讹诈了。我和那家男人急得没办法,打电话告诉老李。
老李一听火了,让我们待着,他马上车两个大箱子回来。这期间,我脑子冷静下来,把已有的关于租赁房子的有关法律想了一下,心里有点谱了。老李到了以后,我们告诉房东,决定不搬家了。并且明天就会去银行停了自动转账,他们一家三口会不付房租地一直住在你这个房子里,你没有权利赶他们走,除非你叫警察,警察也不会赶他们走,因为根据法律,冬天是不可以把付不起房租的租客赶出去的,他们最长可以在这里免费住半年。
恶房东没办法,只好当场开出支票,同意搬走。后来,蛮搞笑的,他居然把电话打到朋友的实验室,询问朋友是否最近失业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对付流氓的办法就是比流氓更流氓。
Rose Marie,是我们朋友的房东,绝对是少有少有的好房东。自从把多余的房子租给中国人以后,就一直只收中国房客。我们人前人后都管她叫老太太。很多时候,周末正无聊,电话铃声响起:喂,过来吧,到老太太这里来烧烤。接到电话的可不止我们一家哦,前呼后拥总有十几个人。
老太太并非无儿无女,儿子女儿孙女外孙都在本市。但是听说,子女们每年圣诞节会来吃一顿饭,仅此而已。反而,住在她那里的中国学生倒成了亲人。过年大家包饺子会请她一起,烧烤也带着她;还很多次送她去急诊。不过,老太太也确实对大家不薄,家里古董餐具随便我们用;花园随便我们种番茄种小葱;樱桃熟了随便我们摘。
她特别喜欢我女儿,每次她的房客请客,总是再三关照一定要打电话给我们。我女儿也是,一到她那里,根本用不着我们管,钻进她的房间半天不出来。我偶尔探头进去看看,老人孩子和狗正玩得欢呢。
每次吃过晚饭,还欢迎大家在她的客厅里打牌。后来,我们家地方大了,还有一副麻将牌,吃过晚饭以后,都去我们家,老太太就非常不高兴。再后来,随着队伍越来越壮大,我家一桌扑克一桌麻将也还有人手多余。于是,留下部分在老太太那里开辟第二战场,她又高兴了。
有时候,我们说起老太太也挺感慨的。不是吗?住着大房子,有儿有女,却需要我们这些异乡青年才能热热闹闹。我也曾经亲耳听她说过,没有把房子和财产留给子女的打算。于是,大家就起哄,让她认中国干儿子。
也许,你会觉得,做子女的太冷漠,没有亲情,不关心老人等等。这倒也是事实,西方社会的这个问题远比中国严重。不过,时间Ggengn3h0BShoGHE+PfmJQ==久了,我却慢慢品出,责任不完全在子女一方,而是和整个社会福利体系和观念有关。
好的方面来说,法国的孩子从在母胎里七个月开始一直到三岁,每个月都有国家的补助,补助的金额足够奶粉和尿布;从幼儿园到中学,全部免费上学;老人则有退休金或者补助,反正足够维持穿暖吃饱的生活。全国上下,老老小小,一律享有医疗保险。换句话说,一个法国人的生老病死还有基本教育,完全是国家包了。一般来说,大多数年轻人工作以后就不住在家里了,如果有了工作,和父母就算是撇清了。亲情的断裂就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这时候的父母,基本上房子车子供完了,孩子也都搬出去了,自己也接近退休或者已经退休,有钱加有闲,正是享受第二春的大好时光。而这时候的年轻人,刚刚工作,工资不高,结婚以后,需要供房子供车。这倒还不是主要的,年轻人经济上不依赖父母是应该的,等到年轻夫妇有了孩子,而在孩子或者自己生病,或者有事情需要人临时照看孩子的时候,他们完全处于无助状态。
父母也有父母的想法,生病看医生可以用医疗保险,照看孩子可以花钱请保姆。用钱可以解决的事情,何必来麻烦我们呢?等到他们老的时候,子女当然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再加上,等到父母七老八十,子女也都进入享受第二春的年龄,他们连自己的子女都不管,还会管父母?一代一代,基本上都这样。
我们认识一对法国老夫妇,人相当好,但是他们对子女的态度在我这个中国人看来是十分不理解的,在法国人中却绝不是少数。夫妇两人已经退休,都是知识分子,退休工资颇过得去。三个孩子,儿子据他们说是对学校生活严重过敏,因此初中毕业就去石匠铺做学徒;大女儿是三个孩子中最漂亮和聪明的,是大学音乐系的学生;小女儿患有非常严重的厌食症,体重不足七十斤,完全失去工作能力。
他们的儿子因为从外地搬来,租房子需要担保人,他们就非常生气。因为,如果儿子万一失业不能交房租的话,就需要他们交。大女儿因为大学毕业想继续升读研究生,音乐专业很少有奖学金,他们拒绝支付学费,后来在大女儿一再保证会努力打工还钱的情况下才寄出支票。
小女儿的情况更糟糕,因为我接触下来,觉得她不仅有厌食症,还有社交方面的障碍,他们却逼着小女儿自己去有关部门申请补助,自己一个人在外面租房子住,甚至逼着她去找工作。有一段时间,小女儿就在酒店做清洁工,后来在医生的干预下才停止。
我曾经直接问过他们,为什么不让小女儿住在家里。丈夫说,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她必须学习自己独立生活。妻子说,每次我辛辛苦苦做了饭,她都不吃,我快要发疯了。他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对象是病人更是他们的女儿。我无话可说。相信,等到他们拄着拐杖的那一天,子女最多能做到的大概就是打个电话让养老院把他们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