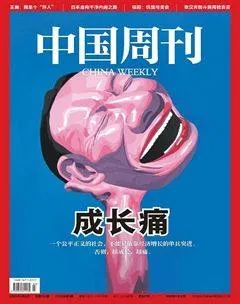国企高管缘何被纳入渎职犯罪主体
日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渎职刑事案件适用若干法律问题的解释(一)》,首次明确渎职罪主体涵盖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该解释第7条明确规定,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国家管理职权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行政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照立法解释的规定,适用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本条所指立法解释,是指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章渎职罪主体适用问题的解释》之规定:在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行使国家行政管理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或者在受国家机关委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有渎职行为的,依照刑法关于渎职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刑法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罪之外还在第168条规定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的失职、滥用职权犯罪,既往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立法解释规定的“组织”是否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存在不同意见。
“两高”的司法解释在学理上必然会重新激活一场由来已久的争论。即“两高司法解释”是个案解释,还是一般解释?是具体解释,还是抽象解释?“两高司法解释”是对立法和立法解释的补充或明晰,还是僭越立法或者立法解释重新造法?“两高司法解释”如若违反宪法和法律之规定,其制度化的纠偏机制应该是什么?尽管不断面临上述质疑,但“两高司法解释”事实上已起着统一办案标准、指导司法实践的重要作用。中国是一个采行成文法体制的国家,国家立法权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门享有。但国家立法的粗糙、僵滞以及国家立法机构的运行缺少灵便,效率低下的状况,事实上也使得中国法治的发展越来越依赖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的司法解释。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法律解释的决定所确定的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之边界,也早已被现实突破。此种宪政体制与法律实践严重脱轨的现象,是未来中国法律变革必须认真对待并予以妥当解决的重大议题。否则现实问题凸显之下,法治统一淡出,仅仅让存在必要性证明制度的合理性,舍弃法治的终极价值追问,那将导致法律的权威永远无法生根发芽。
国企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国企之存在初衷在于因应重大公益性、重要民生性、竞争不能性所必须。但当下中国的国企耦合了计划经济、资源掌控、行政垄断以及意识形态等多重元素,使得其所行所为时常偏离大众观感。国企高管选聘的晦暗不明,市场与权力的双重嫁接,容易滋生权贵资本;过度的市场与行政垄断,使得民资望而难入其门;经营效益低下与高管巨量高薪形成绝然反差;奢靡无度与资产重大流失让民众怨声载道……国企高管渎职犯罪最为显明的特质是渎职行为与贪污贿赂双栖双飞、共生共养、相互勾连、因果关系纠缠不清。
当下常见之国企高管渎职犯罪行为主要有以下各种:借由对外合作之际,让利外(对)方,收取巨额回扣;上下勾结,故意降低下属单位上缴利润,瓜分或者挪用隐匿资产;另开私人公司,分流国企利益,或者制造虚假债权、债务,掏空国企资产;利用监管承包、租赁之际,相互勾结,虚列开支,虚报产值,扩大成本,隐瞒利润;好大喜功、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投资浪费;巧立各种盲目,集体私分国有资产;滥用管理职权,私设“小金库”,或者内外勾结,窃取国家金融资金;不顾国企盈亏和长远发展,变卖厂房设备,或者盲目提供抵押担保,杀鸡取卵,损害企业动脉……
综合上述现象,过去法律仅将渎职犯罪主体限缩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难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状况和司法实践中打击渎职犯罪的现实需要。将所有国企高管渎职犯罪一律归类为企业、公司人员的渎职犯罪,则又不符合罪刑法定、罪行适应的刑法原则。“两高司法解释”是为了缓解法律规范与现实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其成效如何,当由未来的司法实践来予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