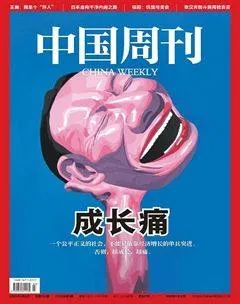警惕城镇化成为瓜分利益的盛宴
十八大之后,城镇化成为热词,被解读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引擎。
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人口红利正在消失的中国,该怎样理解城镇化?城镇化会否成为利益阶层“交换利益的新平台”?
战略资源专家宋健坤接受《中国周刊》记者采访时称,中国城镇化建设的开始,标志着中国跨入第三次社会变革期。
Q=《中国周刊》
A =宋健坤(战略资源专家)
第三次社会变革
Q: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遇到了哪些瓶颈?为什么要提出城镇化这个方向?
A:我们走到今天,由于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已经不能在原有的模式和速度上继续发展,但是需要给世界一个回答,我们能否再进行可持续发展和高速发展?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动能依然主要是靠投资拉动,但消费和出口贡献度明显放缓甚至下滑。GDP破八以后,如果找不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会很快继续下跌。问题就归结于重要的一点: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动能选择,应尽快在战略上及政策层面上予以明确。十八大后,城镇化和工信化将成为中国资源空间价值提升的重要路径和动能选择。驱动中国社会和经济总价值提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其核心动能是城镇化。
Q:“城镇化”的内核是什么?
A:“实施城镇化建设”实际上是一场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新社会变革,其深刻内涵是中国将全面进入“要素体系创新与建立阶段”。1949年,整个社会的结构调整,是生产资料的重新设置,这是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巨大变革。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盘活要素为主,实现了经济体制的变革。我们从农村改革走到城市改革再延伸到政治改革,循环的结果是回到城乡差异矛盾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割裂历史,城镇化是必然路径,也必然要触及到从土地制度到社会制度一连串的问题。所以说城镇化无论是政治上的选点也好,还是历史的步伐走到今天也好,因果是相叠加的,是必然的。
Q:也就是说“城镇化”既是发展动能,同时又是社会问题?
A:过去经济发展中的要素解放是局限在村与村,户与户,个体联产承包,生产要素并没有达到集群解放,也就是要素没有达到规模化的发展阶段,自然而然带来了今天在局部上必须要“土地变性”才能产生增值,才能使农业的发展进入到规模化的阶段。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其承载的含义远远超越经济领域,绝非仅限于满足社会需求的生产力范畴,已经全面触摸到整个社会的结构性变革,也必然要触及到从土地制度到社会制度一连串的问题。城镇化建设不是刺激内需的权宜之计,而是撬动生产关系再调整,推动中国走向第三次社会变革的历史性跨越。
Q:为什么用“社会变革”来形容?
A:历史无数次告知后人,任何一次社会变革,都是“利益的再平衡”的集中爆发与“残酷博弈”的过程体现。今天,年轻的中国农民“抛家舍业”不惜遗下空巢老人而跻身城市,这同时预示着一场即将改变中国未来的深刻变革已经拉开序幕:一方是凭借强大资本实力觊觎廉价土地已久的利益阶层,另一方是幻想通过“土地换身份”来实现与城市人同富贵的农民们。两者较力的矛盾爆发点将集中于“利益交换的结果”,前者是想以最小的代价交换最大的成果,后者是想以仅有的维系性命的土地要素来交换滋补未来新生活,结果是不言而喻的。而双方“残酷博弈”的过程,将深刻体现出政府的利益倾向,而这正是这场变革所昭示出的深刻社会意义之所在。
所以说,“城镇化”这个看似很小的主题,承载的内涵是非常大的,它孕育着要素的创新和新制度的建立。因此用“第三次社会变革”来形容即将展开的城镇化建设并不为过。
历史使命
Q:过去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城镇化被忽略了?
A:一直以来,我们利用“剪刀差”的方式发展经济,利用农业的利润来反哺工业。早期我们在主观上选择和世界同步发展,但是在客观上被国际封锁,因此不得不选择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只能靠农业的产品销售争取外汇,再通过外汇国际贸易的补贴换回一些机器、技术来补充和发展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工业是在这种条件下建立起完整的体系。这之后,即便有了对农业进行的一些直补,但效益很小。等回过头来看,城市的发展与农村实际的发展、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发展,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把原有、并不大的实际差距扩大为天壤之别。
推及到我们过去所有的发展路径,曾经选择过教育作为产业,最后失败了;医药选择也失败了;房地产的选择开始挺高兴,后来发现也不是个正事儿。好像是不经意之间拉开了城镇化的帘幕,却发现一个巨大的洞,这个洞竟然是我们几十年没有看到的。
Q:为什么几十年看不到?
A:其实不是看不到,而是一再推诿没有解决。说得不太好听一点,我们主观上不是太愿意拉开这一幕,因为问题实在太大。
Q:那如今,城镇化又将如何完成社会变革?
A:中国农村,今天所能看到的,仍然是袒露着凹陷与差距的社会现状。中国农村出现一个巨大的危险:断层和沉降。农民工,追求城市人生活,拒绝返乡和拒绝务农。它犹如社会结构出现断层和沉降,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正在出现的巨大危机。“二元结构”社会长期固化、沉积埋下的隐患开始发酵。所以说,实现城镇化必须消除“二元结构”社会、建立“新型土地”制度、实施“社会改造”工程。这三项是历史所赋予城镇化的核心使命。
Q:三大使命皆任重道远。
A:是的。消除“二元结构”社会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战略目标。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补齐失缺度,具有完整性。而建立“新型土地”制度则是中国城镇化建设最为艰巨的历史重任。“社会改造”属于文化层面,将贯穿于中国城镇化建设始终。
Q:土地问题,历来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聚焦的最为敏感问题。城镇化如何破解这一难题?
A:中国城镇化建设过程所环绕的主题,实质就是土地的制度设计问题。任何想绕过此问题或试图肢解开此问题,以求破解城镇化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不可否认,促进“土地配置市场化”与“土地流转规模化”,是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发展乃至搞活农村经济等诸多宏伟目标的基础性条件。
盘活土地资源必然触及“土地确权”问题,有可能出现两种可怕的演变结果:一是利益集团从农民手中拿走“地权”,农民将无奈地再次沦为“雇农”;二是农民以土地换得城市身份,最终成为“城镇游民”。
Q:这两种情况似乎都有苗头,人们在担心城镇化“中等陷阱”。
A:今天看,土地制度的设计与管理权的选择方式,无论做出何种选择,都将深深刺痛各方的利益。要警惕城镇化成为各利益方攫取中国国家公共红利的最后一次晚宴,切实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重大考验
Q:从微观角度看,城镇化又回到了一些老问题,比如人口的问题上?
A:城镇化解决的其实还是人的问题,这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有问题的目标是一致的。比如,“缺钱少地”是目前中国农村面临的真实现状。从目前中国各个社会群体的情况来看,最需要养老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的,就是农村的农民群体。从城里寄回乡下的打工钱,成为农村空巢老人们期盼的救命钱。老一代农民所面临的养老困境正在一步步逼近,他们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跟城里人一样,就近领到养老金。如果不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必将给未来中国的发展和稳定带来影响。所以,破解农民养老难题,就成为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之一。
Q:城镇化带来的新考验又是什么?
A:未来五年,将会是考验执政者的最重要时期。接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将关注政府的施政方向和利益倾向,而最应该谨慎的就是防止追求短期刺激经济而造成非理性的城镇化。
Q:如何防止?
A:工业、农业、就业三个层面都可能出现非理性城镇化。首先,就要警惕房地产经济的破坏;其次,防止土地利益的重新分配引起农民的不满情绪;最后,就是解决大批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最后一点也是最可怕的第一点,如果安置不好失去土地的农民,城市将出现大批城市游民。
Q:但是农民要真正成为城市人很难,他们还要面对很高的城市门槛?
A:不可否认,今天的“城镇门槛”,已经成为城里人——既得利益的守护者与城外人——欲求分享的跨入者间的一道生死线!为攫取存入城镇账户的待分配或按人头可获取的公共红利,双方的博弈已经展现出群发性特征。中国城市化率目前高达50%多,但是其中有超过10%的流动人口是不享受市民待遇的,这是现今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缺憾”。如何以包容的心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吸纳农民工“进城”,让进城的农民工在医疗、教育、户籍等方面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的平等待遇,这对城里人,尤其是城市管理者而言,面临实质性考验。改变农民的身份,进而削平中国本不该长期存在的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对此,城镇化毫无疑问是一个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工程。以城镇化发展的“承载力”水平来设定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安全阀值,这才是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科学方式。
城镇化的过程好比是一个经历过暖冬的人们,习惯与惰性无时不再提醒人们:再多迈一步就是春天。但是,严酷现实将会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教训明天的人们:严寒才刚刚开始。我们总在想,再熬过两天就是春天了,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城镇化的复杂性,迎接我们的可能就是严冬了,就是考验,甚至是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