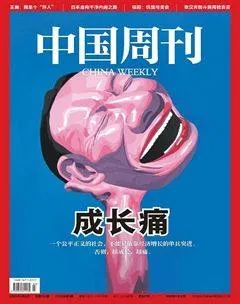“我们村是怎么没的”
大哥出门去干建筑,嫂子给工地做饭
孩子在市里上学
二哥考大学去了北京,二嫂是山东的
妹妹嫁给了粉刷工,住在了县城
后来,爷爷死了,埋了爷爷。
52只羊,卖了!1头牛,卖了!
葬礼上把1头猪杀了。吃了!
牛圈羊圈都塌了。地没人种,荒了!
再后来,奶奶也死了,埋了奶奶。
葬礼上把鸡都杀了,鸡蛋,吃了!鸡窝塌了。
大黄狗,送人!大狸猫,去流浪了。
大哥在市里,给孩子攒大学学费
妹妹和妹夫筹措买房首付
二哥的小孩需要人照看,父亲退休后
父母一起去北京带小孩,父亲在小区口摆地摊。
土豆卖了!黄豆卖了!玉米卖了!
谷子碾成米,卖了!向日葵榨成油,卖了!
被褥衣服,运到北京!锅碗瓢盆家具,送人!
一场雨后,院子里长出荒草。
菜地的篱笆,倒了。窗户纸让大风刮干净了。
有一场雨后,山洪水冲进烟囱,冲垮了灶台。
爷爷奶奶的坟头,荒草一茬接一茬疯长。
偌大的山,山下偌大的村庄,
只剩下两孔窑洞,像两只深陷的眼睛
黑洞洞地盯着村口。
只剩下村口弯曲坎坷的路,蜿蜒向远方

一
三十年了,纪彦峰一直在迁徙。他一直希望找到的安稳,总是会弃他而去,如同他“抛弃”家乡。
2005年冬天,爷爷去世了,家里的东西包括牛羊一类的大牲口全都变卖了,只给唯一还生活在村里的奶奶留下了一个200平米的小菜园,20多只鸡和一头猪。这一年,家里的耕地早就荒了。
没过几年,家里人再次变卖了家产——80多岁的奶奶一个人住在村里,这让家里所有人都不放心,奶奶被接到了延安市,住在二爸(二叔)家里。奶奶离开家的那天,鸡和猪被端上了饭桌,破家具劈成了柴。
最开始,纪彦峰对家的概念没那么强烈。他从小就不断地挪窝,由于父亲是小学老师,频繁的工作调动,使得纪彦峰上了四所小学,村里、镇上、乡里,每一次,都是住在学校给父亲安排的临时住所里。初中住了两年校后,父母终于在镇上里安了家。一年后,纪彦峰去了子长县城读高中,从这时起,家就变成了一个回去探望的地方。
再后来,爱好文学的纪彦峰考上了西安外国语大学读中文系。家里并不富裕,虽然他很想成为大学老师,但身为长子,他不可能继续读研读博。毕业后去找一份赚钱的工作,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
于是他抓住了一个校园招聘的机会,来到山东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几年下来,有了一定积蓄,在淄博市贷款买了一套房子。2007年底,他搬进了这套房子,结了婚。
2010年,公司在北京找了个项目,纪彦峰被调到了北京,他想在北京扎下根来。他已经过了30岁,也到了要孩子的时候了。
去年,他买下了自己所在房产公司在郊区开发的楼盘,付了首付。春节之后,纪彦峰回了一趟山东,出租了那套已经没人居住的公寓,变卖房子里几乎所有东西,只有几百册书,封存在地下室里。
这是他经历的第三次变卖家当了,只是这一次,不是在陕北农村老家,而是城市里。虽然不用卖粮食,不用杀猪,但同样的场景让纪彦峰感觉空落落的,“结婚在那里结的,生活很安稳了,当时体重已经长到140多斤了。”
纪彦峰略显清瘦,他一直保持着一天两顿饭的习惯,现在让他吃早饭依然很不适应。
“我为什么对家这么在意……我真的没有家”,纪彦峰念叨着。
“现在国外、港澳台,大城市基本咱也都去过,但现在做梦还是小时候爬过的那个山啊,小时候放牛放驴去过的地方,山山水水,全是老家。山东呆了六七年,从来没梦到。”
二
“特别想出来,如果现在让我去美国发展,太好了。如果说月球发展得不错,让我去月球做生意,太好了。”
从小,父亲就告诉他一定要走出大山。陕北自然环境恶劣,村里人只能靠天吃饭,作为小学老师的父亲,知道窝在村里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从有意识起,纪彦峰就想去看看外边的世界,想走出去。他从小就看爱一切有字的东西,那时候,看书是唯一“走出去”的方式。《西游记》是他看的第一本字书,9岁时,奶奶纳鞋底的鞋样就是用《西游记》的书页做成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
父亲有两个弟弟,他们是纪彦峰看到外边世界的另一个窗口。纪彦峰小时候,在城里打工的二爸(二叔)和三爸(三叔)会给他带回来外边世界的只言片语。“他(三爸)讲在晚上看守工地,喝一瓶小二,哎呦太好了。那时就觉得,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生活。”
6岁时,纪彦峰第一次去延安市里,“虽然没什么意识,但对城里也留下一些光怪陆离印象:汽车,火车,第一次喝汽水,像吃辣椒一样,第一次晕车,都是很独特的体验。”
在2亿流动人口的大军里,陕西人绝对不是一支主力军,即便是比较靠近游牧地区的陕北。农村里的人走出去,一般就是指到县城,或者延安、西安,很少出省。
纪彦峰觉得,到西安并不算是走出去。所以当那家山东地产公司来校园招聘时,他选择了比陕西发展程度更好的山东。
可是淄博这样的三线城市依然没有让他感觉到自己走出去了,总觉得淄博平台还是太小,加上互联网的蔓延,这个地方让纪彦峰觉得和自己的梦想仍有差距。
一个大学时的同班同学给了他走去更大城市发展的刺激。2004年他们一同来到淄博,两年后,同学去了上海发展。又过了两年,纪彦峰去上海出差时见到了这个同学,短短的两年时光,已经让他明显感觉到了两人之间的差距,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或者收入上。
当公司准备派人去北京时,纪彦峰毫不犹豫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十年前,高考结束后,他烧了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想彻底离开这个环境,想和高中的压抑生活做决绝的告别”。
当今年把山东房子的家当都变卖后,纪彦峰也算告别了山东。
三
这些年,亲戚们都成功地“抛弃”了村子。
1962年出生的二爸是家里最早出去的人。
在1980年代,作为全家公认“有想法”“爱折腾”的二爸,就在农村待不住了。
二爸高中成绩很好,如果当年没退学,纪彦峰可能不会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
一直想干点儿什么的二爸,忍耐不了学校单调的生活,便回家务了农。可种地的枯燥他更加受不了,几年之后,20岁出头的二爸去了延安市。
在延安市,二爸在建筑工地干过,开过拖拉机,倒腾过服装,贩过煤。这些都没干长。几年后,带着二妈和两个孩子回家了。家里人评价二爸没耐性,不好好干活。
这一回家,就是十年。他承包过几百亩土地,以机械化耕作的方式,种植药材、向日葵等经济类作物;找过大型货运卡车贩卖当地特产土豆。而这些致富方法都以失败告终。
一次,二爸得知一个远房本家亲戚在延安市里做起了卖面皮的生意。凭着多年“折腾”的经验,他再次离开村庄,跑去延安市给这个远方亲戚打工。
这回二爸终成正果,在打了一两年工后,自己开起了面皮作坊。而后,又把家里的很多亲戚带到延安市。
如今,延安市三分之一的面皮生意都被纪家做了。家里人的侧重点不同,二爸、三姑父、二姑、大姑家的两个儿子都分别有自己的作坊,产销一体,分别卖擀面皮、面皮和荞麦碗坨。
今年过年回家时,大姑家的大儿子和二爸再次讨论了家里生意的前途。他还是希望能够把家里的小作坊拢到一起,实行现代化管理,可没人支持他的建议。他又提出养猪的计划,更是被二爸以“想法太大、不切实际”给否了。
大姑家的大儿子算起来是纪彦峰的大表哥,头脑非常灵活。高中毕业后,大表哥去当了兵,在他的计划里,当兵就是为了捞一个“政治资本”。几年后,大表哥踌躇满志地回到村里,准备竞选党支部书记,可是事与愿违。“从政”不行,只得“下海”,大表哥做民工,搞传销,去山东、东莞的刀具、造鞋厂当工人。2005年,纪彦峰在山东临沂见到了打工的大表哥,看着他穷困的样子,心里很难过,“这么聪明的人,混得这么苦”。
大表哥在外四处碰壁后还是选择了回延安跟着二爸干,虽然理念上总是有冲突,但总算有个正经活计做了。
今年春节,纪彦峰基本把家里人都见到了。他的平辈人基本都上了大学、大专,在子长县里开大货车的二姑家老三也由家里出钱在县城买了两孔窑洞,娶妻生子了。
三爸在宝鸡做值夜保安,白天打另一份工,经过多年,也在宝鸡扎根扎得很稳了。二十年前,他被迫离开村子。作为最小的儿子,他本想在家侍奉父母,但是由于生在陕北大山里,是不会有姑娘嫁过来的,二十七八岁才结婚的三爸深知,不出去,就意味着找不到媳妇。

四
父亲说,等你妹妹嫁出去了,一定回老家去。“我觉得这不可能,连奶奶都没做到。”
只有父亲总念叨着要回老家。为了给二爸帮忙,父亲在学校办了内退。父母几年前搬到延安市,在农贸市场开了个卖以面皮为主的主食摊子,但这几年做得并没有什么热情。父亲在城市里没有朋友,父亲的青春、工作都是在村里度过的,在延安,他过得不舒服。
父亲留在城市里的最大原因,就是女儿。高考前夕,由于学业压力过大,纪彦峰的妹妹患上抑郁症。之后这几年,父亲带着妹妹去了延安、西安、北京治病。父亲希望,等妹妹病好以后嫁人了,他就回老家。可说到回农村,纪彦峰认为这不现实,家里什么人都没有了。
纪彦峰的老家,陕西子长县南沟岔镇南家焉村,如今只剩10来户人家,不到30人。20多年前,村里有40多户,200多人。
春节回老家时,又走了一两户人家,“没有新的人回来,人往外走,老人死掉了,小孩长大出去挣钱。”
纪彦峰的朋友,陕北榆林诗人李岩写道:每个村子只剩下四个人:老婆儿、老汉儿、队干、憨憨(形容笨人)。
在陕北农村,很多人回老家,只是意味者上坟。
纪彦峰一直坚持写诗,在诗的世界里,村庄缓慢的变迁被具化,变得更加透彻。他的另一个诗人朋友谭克修在题为《潜伏者》的诗中,将萧条的村庄比作一个巨大的充电器。
古同村有黑暗的木房子和鲜艳的红砖房子
每座房子里有人秘密潜伏
他们化装成老人、妇女和儿童
他们勤快地扫地,擦拭门窗、桌凳、柜子上的灰尘
喂养家畜和家禽,晒发霉的被子和
新的传言
据说这些都是幌子
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制作充电器
他们要把房子制作成一个巨大的充电器
每到年关,充电器能给长途汽车运来的电池
那些疲倦的电池、快耗尽的电池,
快速地充满电
让电池不管出门多远,电量至少能
用上一年
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需要回乡充电了。看起来,他们抛弃了乡村,可李岩在诗里说,他们是被赶出了乡村。
连经历了创伤的人
连辱没了祖宗身子不干净的妓女
也不情愿再回到那里
叫浮肿的耳根子再听听山里
贫穷而干净的风声
叫膝盖跪在老坟前嚎一嚎自己的屈辱
出门,就是村庄唯一的主题
是贫穷,也不是贫穷的鞭子抡在半空
把他们像牲口一样吆赶出
庄稼人世代命根子一样
紧紧搂在怀里的土地

纪彦峰特别羡慕生在城乡接合部的人,“不用背井离乡,同时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他更希望能够均质发展,不要把资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可城乡二元化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裂缝,只能更多靠那些走出农村的人,用自己的肉身去填补。
城里的压力从不分辨任何人的出身,在偌大的北京城,纪彦峰和所有人一样,要考虑房子、车子、工作,以后也要面临上有老下有小。他计划将来把父母接到北京,父亲有退休工资、母亲没有,母亲在老家上有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可如果在北京生了病,还需要自己掏钱。跨地域的医疗保险,还在政府手里攻坚。不太遥远的将来,是一个巨大而叵测的黑洞。
纪彦峰有个侄子也在北京,一年也见不了一两次。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