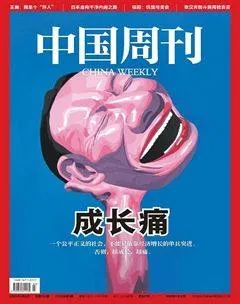长大成人就在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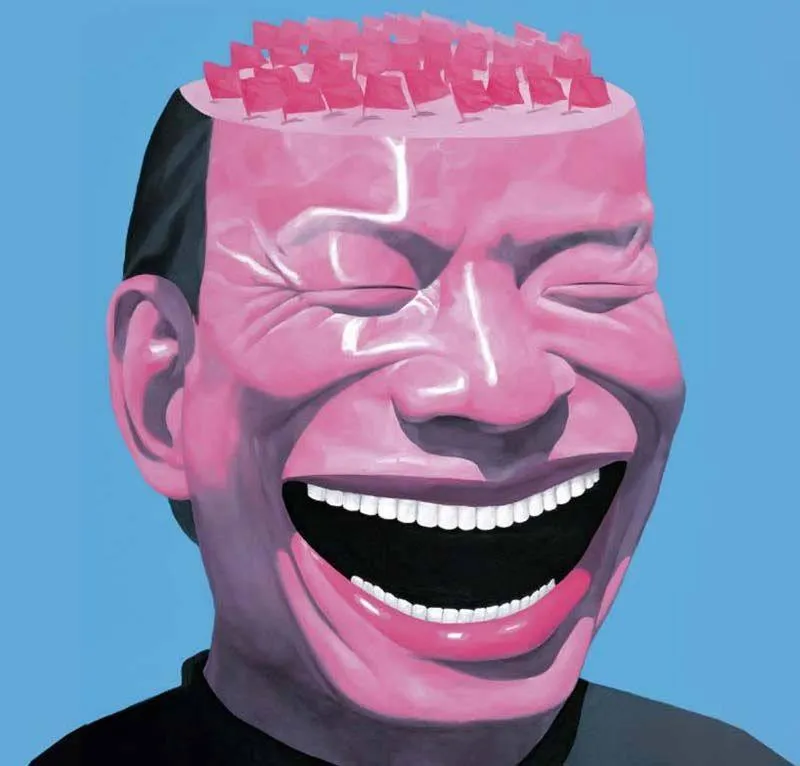
我曾亲身经历过一次疑似生长痛。
那是小学五六年级时的一个夜晚,碰巧还是停电,在蜡烛下正写作业时,突然感到小腿肌肉疼痛。让我有些惶恐的是,这种痛毫无征兆,且完全陌生。家人纷纷安慰,记得父亲对我说,要“既来之,则安之”。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成语,从此就对它没好印象。
那疼痛来得快,去得也不慢,后来也再没痛过。1980年代,父母还没小心到事事要带着孩子到医院去。不过母亲本在医院工作,她去问了儿科的同事,回复说,可能是生长痛。母亲解释为:小孩子长得太快,营养跟不上出现的疼痛。
生长痛的医学解释,是指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肌肉、骨骼、筋腱生长不协调产生的疼痛。
生长痛的几个关键词是:快速成长、不协调、疼痛。
于人而言,生长痛并不算一种疾病。但于社会国家,则很难简单地“既来之,则安之”。
中国的快速发展众所目睹,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从吃不饱饭到坐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用了30多年,古今中外都无先例。不过,这快速的发展,绝大部分都集中在经济的层面。改革徘徊在深水区前已久,水深且急,摸着石头过河已绝无可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其他层面的相对停滞,形成了强烈的不协调。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腐败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等等,都成为显性矛盾,让这个国家不时陷入成长痛中。
不可否认,即使在经济层面之外,中国社会也有向上的发展——传统文化开始得到尊重、公民社会已在搭建中、法治至上的观念在纸上畅通无阻、连空气污染都在艰难中达成了共识。可为何上行线上,社会情绪反而更容易激化?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专门解释了为什么法国会在1789年发生大革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并不能简单解释那场革命。当时,德国的农民还不能离开领主的庄园,而法国农民已经成为土地拥有者。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法国人所受到的封建压迫反而是最小的。品尝过合理生活的人,才会对不合理难以忍受。“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而对外开放,也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即使那些从未品尝过的权利和生活,也让人们期冀。30年前,没有人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没有人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没有人要求司法独立……可人们坚信,凡此种种,本不该排除出一个国家健康的肌体。
在医学领域中,一个孩子的生长痛之所以不是病,是因为生长本身在基因稳定的控制下,是个自然有序的过程。偶然的疼痛,不会改变长大成人的趋势。而一个转型期的国家,则面对太多的不稳定。改革开放30多年,没有人能够准确预判到未来的趋势;而将来的时代,做出预判需要考虑的因素,则更为复杂。
可这个国家还在飞速地发展、长大,把国家的发展过于依赖经济的发展,危险就在此处。经济一旦减缓发展,被经济增长所暂时掩盖的其他矛盾,就会变得更加尖锐。
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也遭遇过严重的生长痛。那时候的美国,联邦政府弱势,商业势力强大,在社会公正匮乏的情况下,商业力量野蛮地如癌细胞生长——官商勾结、腐败横行、贫富差距惊人、食品安全问题严重、普通人的权益遭到践踏。一场及时的社会进步运动最终拯救了美国。那场进步运动,或可看做美国版的“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进步不但不能只限于经济增长,反而会因为经济增长的偏科,而显得问题重重。是时候“将权力关在笼子里”了,是时候将公正、开放、包容、法治等更多因子大剂量注入这个国家了。
长大成人就在彼岸,搭建一座所有人都看得到、信得过的大桥,或是迈过成长痛之河的唯一路径。 (徐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