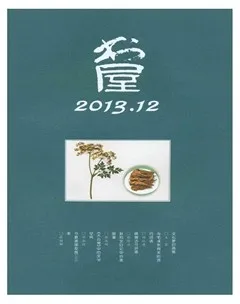我读《书屋》
数月前,阅读2013年第三期《社会科学论坛》上载周实先生撰写的一篇题为《李普先生》的文章。其文一开头,作者即引用李普老人于1997年底写给他的一封书信。该信有两处作如下之言,一处是:“……最近才知道有个《书屋》,……看了很高兴!你寄来的第五、六期也看了,很好很好,为湖南争了光。”另一处则是:“每次读《同舟共进》,……我的家乡湖南就没有这样档次的刊物登那些文章吗?……《书屋》不仅容纳了本省的,而且吸纳了全国的,你可以想象我多么高兴!”由此而令我们可喜地看到,李普老人对《书屋》的评价该是何等之高呀!
如今一经追忆,除少儿时期读过启蒙之类的小型刊物外,当我在抗战胜利后的次年考入家乡初中时,曾订阅过开明书店出版发行的两本杂志,其中一本是《中学生》,另一本是《开明少年》,遂而成了自己的良师益友。为释情怀,进入老境的我曾为此发表过一篇题为《昔日开明育才育人》的小文而述及诸多旧事,如今思之,仍有恋恋不舍之依念。自此六十余载以来,除“文革”那段非常时期外,笔者与多种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而终生受益。
作为理工专业出身的笔者,近四十年的专业工作,使我无暇顾及,且又无力重温青少年时代对人文学科的青睐历程,如今退休了,也就得到了延续的机会。于是乎,读书上网即成为我的退休生涯的真实写照。
在退休生涯中陪伴我的几本杂志中,最为钟情的是湖南长沙出版的《书屋》。
《书屋》创刊于1995年8月,迄今已逾一十八个春秋。斯时斯景,若比作男子,将近弱冠之年,若比作女子,则为及笄之岁。时至今日,诚乃正值大展宏图之际。作为一名长年爱读该刊的读者,仅因经年阅读后不由而生的感佩之情,即有不吐不快之念。
其一,犹如一个人的着装,可以由表及里从中窥出这个人的气质内涵。作为一本杂志的封面装帧,恐亦复如此。它的重要性,不仅意在取悦读者的眼球,更为重要的一面,而是在于它是杂志品味高度概括的缩影。由此当可看出,《书屋》的封面整体设计,依愚之见,黛绿色的主调,一方面象征着青春活力的散发,另一方面则表征了古朴典雅的韵味,且又不失时尚的审美享受,足令读者爱不释手,诚乃最佳构思也。至于扉页、封三乃至封底,每期刊载的那些或馆藏或私藏或旧作或新作的各类艺术品鉴赏,更是美不胜收,回味无穷。
其二,书屋者,乃藏书之所,诚可谓海纳百川之谓也。《书屋》的栏目设置,可谓丰姿多彩,其特色当可归纳为三:一是体现了办刊宏旨,二是浓缩了篇章导向,三是道出了编创团队的心声。出于好奇,我大致统计了一下,栏目设置竟多达二十余种,可谓涉猎了多方位的话题。其中,书屋讲坛、灯下随笔、书屋品茗、流年碎影、人物春秋、史海钩沉、思史佚篇、书林折枝等等,更是笔者喜闻乐见的。至于每期的卷首语,亦即单双月交替出自两位编辑之手的《书屋絮语》,虽谦称絮语,而实为导读,言简意赅,入木三分,深获大家的钟爱。若说美中不足,能否作如是言:今之《书屋》者,实乃再现春秋的书屋。今后若能稍增库容,由现有的88页扩大到100页,定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其三,《书屋》刊载的各类篇章,大抵是围绕当前深为读者关注的、传奇的,或为淡雅的、邃密的,甚乃敏感的、争议的诸多话题而予以精辟细腻的阐述和见深见底的铨释。至于诸多作者妙笔下的那些对古今人物的臧否,中外名家的轶事趣闻,经世致用之学以及人间哲理与人世箴言等各个方面,更是描述得绘声绘色,从而使读者获得了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洗礼。一言以概之,犹如将一幅人生轨迹的素描展示在读者的面前,字有形,文有声,可谓见微知著,淡妆浓抹总相宜。其朴实无华的用词遣字,行云流水般的叙事功底,更使读者亲切感受到这是用平常的语言作为蘸着浓墨的笔端,绘出了一幅不平常的意境水墨画,诚乃平实见厚重,淡雅见真情。笔者认为,诸如此类的着墨点必然会引发阅读者的思想共鸣。在这里若借此说上一句溢美的话,则不啻篇篇熠彩而鞭辟入里,字字珠玑而掷地有声耳。总之,近二十年来,《书屋》奉献给广大读者的诸多美文佳作,可谓非附势而人性,非晦涩而明快,非易逝而隽永,确乃光彩照人。从感性上去领略,犹如一泓清泉,沁人心扉;而从理性上去领悟,则为小中见大,虚中见实,由往见今,由近见远。所有这些,无不在散发着各类文化元素的醉人神韵。
其四,近二十年来,《书屋》发表两千多篇文史哲范畴的各类华章佳作,可以说,这是诸多作者对该刊钟情的一种无形表达,也是该刊同仁多年来筚路蓝缕理当获得的回应。我们早已知道报刊界,素有“北有《读书》、南有《书屋》”之传闻,但《书屋》本身从未刻意宣扬而淡然处之。应该说,这是来自广大读者的心语,既无掠美之嫌,也无溢美之媚。此外,犹如创办学校三要素(高素质师资队伍、充沛的图书资料和必备的实验设备)一样,创办刊物三要素乃为学养深厚且见解略同的编辑团队、能够体现刊物宗旨而以文论道的作者群体以及乐于阅读并继而拥戴的广大读者。由此着眼,《书屋》杂志社不但具备了这样的条件,而且时有锦上添花之举。比如说,先后推出了三辑“《书屋》文丛”以及发行了创刊十年纪念文献光盘,即为一例。尽管《文丛》选本都是以前所发文章的辑录,但据笔者所知,其成果依然显示了一定的客观效应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此一良举在报刊界虽不能说是开了先河,但恐怕也不是常见的现象。
其五,理应指出,《书屋》所发表的有关抒情、解惑、释理、论道乃至争鸣的各类华章佳作,可谓包罗万象,雅俗共赏;阳春白雪有之,下里巴人亦有之。时至今日,对广大读者而言,说是一部文史哲类的小型百科全书,亦不为过也。特别是处于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时代,诸如《书屋》之类的人文社科刊物,今后将得到蓬勃的发展,应是理所当然的。至于说到《书屋》的作者群体,可谓专业作家与业余写手二者兼顾,专题约稿与广纳来稿相得益彰。言至此,笔者当顺势铙舌一句,不仅仅只为名家而是面向大众提供交流平台之举,体现了《书屋》的编辑风格。而这一点正是应验了常言所道,自古英雄百姓家。
走笔至此,当可再说一句:在我与《书屋》有缘结伴的八年里,深感受益良多。有道是,老来蹀躞足不前,坐看《书屋》暖心田。仅缘于此,故而不顾遭溢美之嫌而泚笔作书,以抚心曲,以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