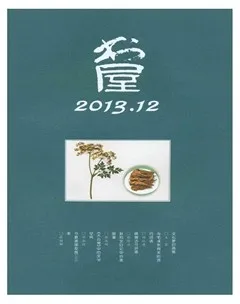日本书纪(三)
欧阳修新发见书简九十六篇
東英寿,《歐陽脩新発見書簡九十六篇:歐陽脩全集の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13.
日本九州大学东英寿教授致力于欧阳修研究近三十年,发表了若干相关论著,但从未预想自己能发现欧阳修的佚文,更不敢想像是数量巨大的九十六篇佚简。原因很简单,欧阳修这样的一流文人,一直为世所重,自南宋编纂一百五十三卷的《欧阳文忠公集》以来,直至明清,其诗文数量相当确定,清代欧阳衡找到七篇佚文,已是十分难得了,今天想找到欧阳修一两篇佚文难于上青天。所以,2010年6月,东英寿教授发现这九十六篇佚简时,也不敢贸然确信,经过考证确认后,至2011年才向学术界公开了这一消息,随即引起东亚媒体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东英寿教授所发现的九十六篇佚简,现在已经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2012年第一期),而且也有了一些相关的研究。
东英寿教授这本《欧阳修新发见书简九十六篇》披露了发现佚文的经过和相关版本考证。全书上编主要考证九十六封佚简的真实性,其中第二章为九十六封佚简的整理校点稿,已发表的校点稿将底本的文字改为通行字体,本书中的校点稿力图再现底稿文字字形,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影印全部佚文内容。下编主要对欧阳修全集版本源流的考证,其中有三篇是书评,对中国出版的几种欧阳修文集作了直率的评论。全书最后还有一个附篇,记叙了寻找考证相关版本和佚文的经过。
这里根据该书,先说说东英寿教授何以可能发现这些佚简。他是在研究《欧阳文忠公集》版本问题时发现这批佚简的。《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为南宋周必大等人编纂,目前能见到的宋刻本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十种;台湾藏本三种,一种破损严重,无法考察,另两种记录已表明是复刻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一种,存六十七卷;奈良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本一种,东英寿教授就是从这个本子上发现九十六篇佚简的。“天理本”虽有后人补写,但最大程度上保存了宋刻原貌,因此被日本定为国宝,能接触到的人比较少,这是佚简一直不为人知的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是图书馆目录著录和先行研究都认为“天理本”与“宫内厅本”皆为周必大原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一种相同,所以一般人不可能会想到其记载错误,加上中日两国之隔,更是难以对这些版本加以比对,事实上东英寿教授说自己获得国宝“天理本”和“宫内厅本”的复印件已经有十年左右,但一直没有意识到佚简的存在。
比对几种通行的本子之后,东英寿教授决定到北京仔细核对,才能确定这些佚简的可靠性。他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通过胶卷查看了十种内的八种,另两种没有胶卷,不能查看,不过恰巧这两种也缺失《书简》部分,对调查不影响。他在其中一个仅剩九卷的本子中,发现了“天理本”佚简的九十六封中的三十六封。这让他很沮丧,因为他原先假设这些佚简是“天理本”独有,不过,转念一想,这也证明了“天理本”的佚简并非日本人的伪作。
接下来就是要确定这些佚简的来源,也就是这几个宋刻本的关系问题。《关于周必大原刻本〈欧阳文忠公集〉》一文指出,《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由南宋周必大整理刊行,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邓邦述跋本”就是当时的原刻本,该本仅存二十至二十三共四卷,其中第二十卷最后,其他版本添加了一段编校说明,而此本独缺,应该可以证明其为原刻本。这个本子原先没有引起东英寿教授的注意,当时他去北京,通过朋友联系到了图书馆的人,希望复印另外一个本子,但送来的却是这个四卷本,最后通过比对,意外在认为这正是周必大的原刻本。
第二次刊行的刻本比原刻本增加了十九篇书简。通过刻工名字等相关调查,可以确定日本“宫内厅本”与东英寿教授称为“国图本”(四十六册,卷三至卷六、三十八至四十四、六十一至六十三、九十五、一百三十四至一百四十三配明抄本,该本国图藏三种,另两种残缺更多)为同一版本,东英寿教授认为原刻本刊行之后,周必大等人又找到了十九篇书简,就直接加在“书简”部分的相关位置。这一系统的版本后来进入明代内府,而明代内府本为目前各种通行版本的祖本,如清代欧阳衡本、民国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也即这些本子的祖本与“国图本”相同。
“天理本”是原刻本的第二次增订本。“天理本”的刻工名字与“国图本”、“宫内厅本”皆不相同,该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也藏有一个仅九卷的残本,东英寿教授认为这是周必大之子周纶的修订本,增加了九十六篇书简,即这是其他版本所没有而为东英寿教授发现的佚简。“天理本”收藏经过十分清楚,日本鎌仓幕府建立金泽文库,自中国购入大量书籍,此时,想必南宋末年战乱等原因,此本在中国反而没有保存下来,也没有进入明代内府。金泽文库收藏后,经京都堀川的伊藤家,现在入藏于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1952年成为日本国宝,源流十分清楚。通过这一系列的版本考查,可以确定这九十六篇书简的真实性及其价值。
呜呼哀哉
佐藤保、宫尾正樹,《ああ哀しいかな——死と向き合う中国文学》,东京:汲古書院,2002.
这个书名应该译成“呜呼哀哉——面向死亡的中国文学”,因为编者在前言说它来自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公文》的结尾,其实不必指定,这样的感叹在碑诔文的结尾俯拾皆是,只不过,今天哀悼之文中已经不常见而已,初见日本学者也有此主题的研究,颇有意外之感。全书不计前言后记共十七篇文章,虽不是通史式的写作,但将哀悼传统延伸到当代——最后一篇论文是石井惠美子的《茹志娟与邓友梅:追忆的文工团》;研究邓友梅的《阿姐志鹃》,有评论说邓文是一篇连茹志娟女儿王安忆也写不出的文章——很是可观。
矢岛美都子的《陆机的〈吊魏武帝文〉》是从汉魏以来“吊文”的系谱角度看陆机的吊文。陆机游秘阁得读魏武帝《遗令》,发现《遗令》竟以身边琐事为意,颇有英雄气短之概,失望之余,作《吊魏武帝文》。矢岛美都子论文例以《文心雕龙》所论汉魏以来诸作,认为陆机此文相对于正统的吊文是一个异例,几乎要称其为破体之作了。当然,章太炎《菿汉雅言劄记》中已经指出了陆机《吊魏武帝文》:“此虽吊文,抑何似谤书也。”矢岛美都子似乎没有看到章太炎的论述,但仍从文体的角度响应了章太炎的观点。论文指出吊文其实暗含着陆机本人的身世之感,还展示了英雄之死与魏晋复杂的文人环境。
黑田真美子的《魏晋的悲怆》以《世说新语·伤逝篇》为中心,考论魏晋士大夫的生死观。魏晋既有士人任诞放纵反礼教,也有士人强调“名教中有乐地”,这两种相对的观念也表现在《伤逝篇》的“哀悼”之中。而这里哀悼所表现出来的生死观,弥漫着对死亡的恐惧。
尾形幸子的《悼不遇的诗人》是从中国历代诗歌选集、类书等“哀悼”的分类开始说起,如《文选》、《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唐诗类苑》等,都有“哀悼”这一分类,足见哀悼在中国文学中所占的位置。论文特别分析了方回《瀛奎律髓》“伤悼类”中的贾岛。贾岛有两首“哭诗”,哀悼不遇的诗人孟郊,“伤悼类”中同时也收录了唐人两首诗,哀悼同样“不遇的诗人”贾岛。方回同时收录伤悼孟郊和贾岛的诗作,正是置两诗人于“不遇的诗人群象”之中,死本堪伤,何况其一生不遇?方回这一做法,是因为孟、贾两人在文学史上,早已经形成了“寒瘦”的形象,方回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而已。读这些伤悼之作,伤悼的传统及其意义脉络早已占据读者心中,而如何恰当还原其个性化的场景,则是读者所要面对的问题。
大西阳子的《死亡的日常风景的具象化》论述了北宋诗人梅尧臣。大西阳子笔下的梅尧臣几乎是书写哀悼的专业诗人,妻子、次子、父母、朋友乃至身边小动物,死亡成了梅尧臣周围的日常事件,他经验着死亡的悲哀,对死亡有着敏锐的感受。本不应是“日常”的死亡,诗人不断书写,以致成为一个“日常”的风景,而梅诗就是这一风景的具象化。
全书虽然成于众手,但都注意发掘中国文学中哀悼的传统,或侧重于吊文的文体脉络,或侧重于文人哀悼的思想脉络,或侧重于诗歌分类的思想脉络,甚至还有一篇论述中国文哀悼传统在日本的例子——直井文子《书写墓铭的山阳先生和拙堂先生》,通过对这一传统的重新检视,我们也许有机会再认识古人的生死观和情感世界。
唐诗推敲
静永健,《唐詩推敲:唐詩研究のための四つの視点》,东京:研文出版,2012.
静永健的《唐诗推敲》里有很多奇思妙想,值得深入讨论。全书分四个部分:音声、典故、校勘、域外,这就是副标题中所谓的“研究唐诗的四个视点”。四个视点中,我认为日本学者最难的应该是“音声”,即唐诗的格律,这需要很深厚的汉语功力,比如平仄的分辨,这对中国人来说,也往往需要借助方言才能奏效,因为古代的入声字在现代汉语中不容易辨别,所以仄声字往往容易出错,对于一个外国人而言,这应该更有难度。
但是,读完全书,我最喜欢作者讨论“音声”的部分。关于格律,作者以自己的经历破题,说求学时经常记不住《代悲白头翁》妙句,不知道是“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还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后来学了格律,就知道前者为非。而且他还在文中介绍了一种方法,通过日语汉字的读音来分辨入声字:若日本汉字旧读的最后一个发音若为“フ、ク、キ、ツ、チ”中的一个假名时,一般都是入声字,算是开了方便的法门。这样日本人也能如中国人那样分辨平仄了。
也是在“音声”部分的《贾岛“推敲”考》一文中,作者根据格律的要求,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贾岛“推敲”的典故是众所周知,而且也知道这个典故并不可靠,作者考证了这个典故的“创作”过程,然后指出这个典故还是应该有一定的依据。他随后提出的问题更值得关注:为什么贾岛会难以选择“推”或“敲”呢?因为这两个字都合乎格律,放在句中都没有问题。作者经过统计后指出,在贾岛时代,“推门”或“敲门”都不是常见诗语,而贾岛之前,最常用的诗语应该是“叩门”,而“叩”为仄声字,放在句中不合格律,所以贾岛要新铸诗语,自然犯难了。而最后选择“敲”字,作者认为是因为“敲”字与“叩”字中古音读法更接近,而且日语中“敲”字也比“推”字更接近“叩”字的读音。这样的解释,也许给“推敲”这个典故带来更多值得推敲的内容吧。
静永健这本虽然是新书,但部分文章已经在中国大陆发表,比如《“卫公宅静闭东院”考》一文已经发表在《白居易写讽谕诗的前前后后》一书中了,作者认为白居易《新乐府·牡丹芳》一诗中“卫公宅静闭东院,西明寺深开北廊”的“卫公”,不是指旧注所说的卫国公李靖,也不是指李德裕,而是用典,是指汉代名将卫青,而与这一古典相对的今典,则是指其功堪比卫青的唐人郭子仪。这一点已经有傅绍磊《白居易〈牡丹芳〉中的“卫公”指谁》(《江海学刊》2009年第一期)有了深入讨论,傅文在大方向上认可静永健的用典说,但是与古典相对的今典,傅文认为是杜鸿渐。
也许作者是白居易研究专家,所以该书虽题名为唐诗,但所讨论往往以白居易为例,如第三部分“校勘”、第四部分“域外”几乎都是讨论白居易,并没有形成唐诗研究的新方法,所谓四个视点倒不如文章中一些奇思妙想更值得讨论。
白居易文学论研究
秋谷幸治,《白居易文学論研究:伝統の継承と革新》,汲古书院,2012.
该书由作者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从白居易的诗序、书信等材料中发掘其文学理论。第二章论述了白居易的“美刺”说及其渊源;第三章结合元和年间的社会风尚及青年期白居易的经历,论述了白居易对律赋的批评;第四章论述江州司马时期的白居易的文学见解,为这一时期其讽喻诗和杂律诗数量变化提供了理论的背景。
白居易研究可以说是日本汉学中的一门显学。想要在众多高质量的研究中出类拔萃,应该对先行研究作深入的考察,才能发现前人未及的论题。本书的开头正是白居易研究综述。对日本白居易文学理论研究,作者考察了铃木虎雄、兴膳宏和静永健三位学者的研究。
二战以来,日本对白居易的研究主要是以讽喻诗、闲适诗以及《长恨歌》为中心展开的作品研究,所以下定雅弘《日本的白居易研究》这一研究综述性的文章中就没有展开“白居易文学理论”这一项,而关于白居易文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有铃木虎雄《白乐天的诗说》、兴膳宏《白居易的文学观——以〈与元九书〉为中心》、静永健《诗集四分类的构想》、《白居易〈新乐府〉的创作态度》等。
铃木虎雄《白乐天的诗说》(见氏著《白乐天诗解》前言)考察了白居易《与元九书》,认为白居易重视讽喻诗,而认为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一样,可以删去不存,但在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十二》中又对《长恨歌》和《琵琶行》这样的感伤诗自矜自得。铃木虎雄揭出的这一矛盾在兴膳宏的文章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兴膳宏认为《与元九书》中否定《长恨歌》并非白居易的本意。而静永健的两篇文章(收录于氏著《白居易讽喻诗研究》一书)也指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和《新乐府序》中表达的思想并没有实际的作品,所以认为这里的文学思想也许并不是白居易的本意。
作者考察了上述三位白居易研究的重要学者,指出这些白居易文学理论的研究中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白居易关于文学言说的矛盾;第二,白居易文学理论与创作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其实是对白居易文学理论的理解不够全面造成的,所以全书从白居易的文学理论的研究展开。
作者对静永健的批评,在静永健对此书的书评《文学理论家:白居易研究的第一步》(《东方》第387号,2013年5月)一文中得到了首肯,并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白居易的恋情文学论
諸田龍美,《白居易恋情文学論:长恨歌と中唐の美意識》,勉誠出版,2011.
白居易研究真可谓是日本汉学中的一门显学,近年除了前面提到秋谷幸治《白居易文学论研究》,还有下定雅弘《陶渊明与白乐天》(角川学艺出版,2012)、诸田龙美《白居易恋情文学论》等。诸田龙美所摄取的关键词“恋情”,在日本白居易研究中是颇为独特的。
诸田龙美这部书中所谓的“恋情”是指“恋慕异性的感情”,侧重指“感情”。作者认为中国文学直到了白居易时代,对“恋情”的率真表现和描写恋爱行为都是持否定的态度,到了中唐才从“人情的自然”这一立场出发,对这一“偏颇”的传统作了根本的变革。诸田龙美此书的第一个写作目的是论述白居易文学中所具有的“普遍的魅力”;其次是以《长恨歌》的流行为切入点,讨论中唐的价值观和审美意识,挖掘读者之所以能产生共鸣的原因;最后讨论中唐的恋情文学对后世的影响。
作者认为恋情的角度观察,可以说白居易是一个“多情的官能的诗人”:醇酒妇人、音乐美食无所不好,确信“身体”与“感情”一体,而“情”是诗歌的源泉。因此作者认定白居易文学的本质就是对“情”的根源性的深刻认识,而这一文学本质贯穿其讽喻诗、闲适诗和感伤诗,如讽喻诗是表现“情的普遍性”,闲适诗是表现“情的身体性”,而感伤诗(恋爱诗)则表现“情的根源性”。全书试图通过“恋情”这一角度来重新考察白居易的诗作。
作者通过与杜甫的对比来突显白居易的“恋情”特色。杜甫《哀江头》中“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是在永远的自然面前的喟叹人生,而作者认为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表现的是“天长地久有尽时,长恨绵绵无绝期”那样,相对于自然,感情才是永远的,正与杜甫是相反的认识。而中唐社会审美意识的成熟,发展出“好色的风流”的观念,艳情诗流行,尤物论自成系谱,显示了“恋情”观念的长足发展。不过,我认为以“恋情”考察白居易,这样的白居易似乎很多日本文学的特色,或许这正是白居易在日本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