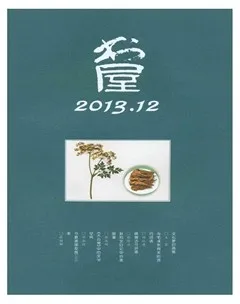花期雪期会有期
与往事可以干杯,但积淀的历史传统智慧必须要继承。古典的理解因为文字和教育的断裂,让现代国人颇费脑筋。因而,稀有的可以解读古典的学者的作品对于我们理解古典思想似乎就不可或缺了。不久前,来美访学的胡晓明先生所赠《古典今义札记》(海天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就给我对中国古典思想和历史传统的理解补了一课,很有启发。下面就谈几点我阅读中很有感触的地方,作为与胡先生谈话,更准确第说是求教的继续。
一、“祭如在”与社会秩序
胡先生在《绝地天通》、《祭如在》、《王庭决大议》等文章里,对信仰、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关系在中国古典文献和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关系演变有颇富洞见的理解和阐述。与天的通与不通,关系到政与教的关系问题,意义的提供方是谁的问题。胡先生以史华兹的观点,“绝地天通”是中国思想的一个逻辑起源出发,认为中国思想史的开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天地相通的原始思想阶段,意义世界由巫来管理,民众没有意义自主;第二个阶段人人都是巫,意义的源泉开放了,意义自主了,但意义的世界充满了冲突和战争;第三个阶段“绝地天通”,政教合一,以集团或阶级或国家或集体的利益诉求,赋予个人生命的意义,意义之源被垄断,取消了自主。胡先生说,接下来,第四个阶段则要对前三个阶段进行整合,既不是没有自主、没有权力的被赋予状态,也不是意义世界各自为政,意义与意义的战争状态,而是既有意义又有区分,既自主又和谐的一种状态,这是一种新的“天地相通”吗?这是胡先生的自问,但没有自答。
对这个思想史的分类和逻辑推演,很有启发性,帮助我们寻找生活的意义的思想资源。郑也夫先生在《后物欲时代的来临》一书中探讨过这个现代意义的话题。传统上是宗教提供人生意义的价值观,在消费主义盛行之前,政治家是人生价值观的提供者,而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商人要取代政治家,成为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或者叫意识的供应者。但问题是,商人提供的这些价值观,是消费主义取向的,脱离了人深层次的心灵的充实。所以,因为“绝地天通”是意义产生的“官方化、国营化、计划化”,但是实际上商人的出场让这个“绝地天通”已经无法实现了。胡先生的“意义世界的真实性、合法性由谁来定”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所以,在《祭如在》一文里,胡先生回到了孔子的智慧。《论语·八佾》里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胡先生采用钱穆先生的译文:先生在祭祖先时,好像真有祖先们在受祭。他祭神时,也好像真有神在他面前一般。先生说:我若不亲身临祭,便只如不祭。胡先生对这句话的理解是从人的有限性来说的。他说:“孔子并不否定人的力量,但对人的力量有所保留,有所控制,有所转化,有所引申,这是孔子很了不起的智慧。”就是说,孔子依然为“神灵世界”保留了位置和空间,对人本身有所保守,认识到了人的有限性,基督教常说的人的“软弱”。胡先生认为,没有了这种“祭如在”的精神,就是“今天的人之所以无恶不作”的原因,因为“取消了人心上面的存在,赋予了人无所不在的权力。打到了皇帝,取消了神灵,推翻了上帝,抹杀了传统,甚至砸烂了秩序,人没有忌讳了,人失去了必要的监督与限制,所以人无所不为,无往不胜”。“如神在”就是“要以一种人心所预设的文明创意,来相对制衡人无限的权力”。人类文明中宗教的地位应该是核心的,不管是“绝地天通”还是天地相通。宗教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2011年出版了《人类演化中的宗教》对宗教在人类文明中的核心地位有很详细的论述。
二、“关天意”的学术
在这本札记里,胡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理解和阐释很富有启发。陈寅恪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符号,只有理解他的丰富心灵内涵才能为我们的学术届和社会输送难得的精神营养。在《吾侪所学关天意》一文中,胡先生从陈寅恪挽王国维诗句:“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开始,问道“为什么‘吾侪所学’就肯定‘关天意’?”这就要回到晚清变法思想之“二源”:郭嵩焘代表的“历验世务”,自下而上的变法,和康有为代表的浪漫政治,自上而下的路线。而陈的家学就是前者。胡先生引经据典认为,陈寅恪的“吾侪所学”就是历验世务的史学和借镜西国以助成中国变法的新学。陈寅恪揭破了今文古文的褒贬兴衰是一种制造出来的故事,一种叙事策略,而在这种策略下“将求真的规范理论与求权力的解释理论混为一谈”。而这关系到“求真的规范性理论”要与种种求权力的解释性理论区别开来。接着,胡先生归纳到第二点,中国经学史上一个与生俱来的病根,即以善取代真,政治伦理的考虑优先于知识真假之考虑。社会思想和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知识可以改变历史,阅读可以产生事实,思想可以生产事件。康有为看到了文化/理性可以构建社会,利用符合的力量搞社会变法,结果伤害了知识本身,也误导了社会。
现在的学者如何呢?在《香江书简》一文里,胡先生对知识和知识人的观察和思考正是对时局下的知识人的学术取向问题。现代的学术政治,似乎学术本身政治化了。比如胡先生总结的现代“学术政治”所凭依的条件和素质,有这样几点:清醒的目标感和有序的追逐活动、敏锐的发现能力、旺盛的生命才情、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人事关系、尽可能多渠道争取各种资助的经费、老练的组织能力、手下有相当数目的二老板、掌握着可呼风唤雨的刊物和举足轻重的学会。学术已经演变为一场学术生存方式中追求权力的游戏,这场游戏中,学术的终极关怀和真正的敬意都缺席,价值理性失落,读书人粗糙化粗鄙化。胡先生在文中说,在香港“接触到不少从事社会科学的学人,他们的专业水准、心理素质、工作态度无疑是第一流的,他们做人的态度也是严肃的,但是他们的人文素养却低得颇成问题,几乎不能谈文化,更粗俗到不屑谈文化,一谈就俗,一俗就不可收拾。极端的单面人(one dimensional man),逸事不胜枚举”。这种情势下的知识人如何才能“吾侪所学关天意”?
没有大关怀,进境难高。即使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著书唯剩颂红妆”,也是对明清痛史给予了很深的感情。有了这份情怀,才有学问的大根基。胡先生引用了波兰尼观点,认为“科学情感具有科学中的逻辑的功能,它们给科学贡献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胡先生通过陈寅恪的“吾侪所学关天意”确实给当下读书人一个警醒:一是学者要提高精神境界有大关怀,二是莫把获取权力的政治伦理与规范性知识理论混淆在一起。
三、花期雪期与知识人的“家”
知识人寻找精神家园的漫漫旅途,发出了“敢问花期与雪期”的询问。胡先生借助叶嘉莹教授的诗句,对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人的文化精神漂泊羁旅无“家”可归作了描写和深刻关怀。这种关怀是一种生命和人文的深切关怀。通往乡关的路上,有花,有雪,有美与诗,有生命与意义。在《敢问花期与雪期》一文里,胡先生提到了雷峰塔的倒掉的文化蕴涵。曾在教课书里读过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还不知道其象征意义,如陈寅恪所言,是殉了中国文化。
胡先生对古典文学的美和生命的意义有深刻同情的理解,他曾著有《万川之月:中国山水诗的心灵境界》、《中国诗学之精神》、《诗与文化心灵》等等,对中国古典的人文和生命的美学做了深入的研究。现代人们的精神世界,根据郑也夫先生的后物欲时代来临的观点,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人们有两个趋向:一个是堕落,一个是升华。而古典的游戏比如诗词歌赋等等就是这种游戏,可以提升人的精神不至于堕落。像叶嘉莹教授这样“敢问花期与雪期”的知识人,在当下的世界已经是凤毛麟角了。我想胡先生、郑先生和叶教授这些知识人所关怀的都是面对物质消费主义的世界,为人的精神世界寻找一个菩提善道。
在《风雪夜行人》一文里,胡先生借助饶宗颐教授的诗词的评论谈到了美妙的古典诗词与精妙的游戏。胡先生说,选堂(饶宗颐号选堂)诗词以和韵为重要特点,其中就有与古人的次韵。次韵要突破前人是很困难的,所以次韵又有着“竞赛”、“竞技游戏”的意味,于是胡先生说:“我们不能不承认,古代中国诗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竞技游戏,是高雅的语言艺术活动,其难度、深度与复杂性,不亚于世界上最精妙的游戏。”而且次韵的诗学,有助于诗人探访文化心灵的故人,谛听到历史精神的回声,历验诗人写作的秘径,参与艺术生命的创造。胡先生引用哈罗德·布鲁姆的观点:凡文学史上后来的诗人,往往有一种“影响的焦虑”,即面临着前辈大师的优秀作品,他们必须要以一种迟到的身份作殊死的搏斗,努力创造有意的误读、修正甚至颠覆的美学,以此来营造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独特空间。郑也夫先生的“游戏论”认为,走向升华的道路要通过这种有难度和深度的游戏,“游戏是我们最好的选择,很可能也是我们最终的依赖。它是良性的刺激;被一个有深度的游戏俘虏,或者说上瘾之后,就不必再去寻找肤浅的刺激了,因此游戏是可持续的刺激”。
回归古典文化里的文学和诗词“游戏”,大概是知识人回“家”的漂泊之旅中的舟车,“花期雪期会有期”也许在这个旅途的某个山洼村巷。我这样附会诗词这样的古典文学的游戏性质与知识人在消费社会里的文化回归,胡先生大概会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总之,阅读胡先生的《古典今义札记》,触发我的很多思考。我似乎就在这个旅途中不时踏雪寻梅、一路上有着康德的理性、托克维尔的自由、陈寅恪的史神、柏林寺的书香、西湖的奇雨、钱穆的文学、仲尼与文王等等,还体验着胡先生的“音乐体验”、一起“星马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