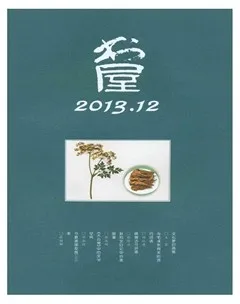赵烈文日记中的曾国藩
赵烈文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和无话不谈的弟子。他有一部《能静居日记》,记录了当时大量重要人物与著名历史事件,内容关涉湘军、太平军以及清廷的诸多方面,尤其对曾国藩与清廷的矛盾,南京失陷时清军烧杀掳掠之暴行,以及李秀成被俘等事实记叙颇详,是研究太平天国和晚清历史的极好材料。
另外,这本日记还记录了曾与赵的大量谈话,不仅内容包罗万象、完整详实,而且谈话时两人的一颦一笑都活灵活现地记了下来。通过他们的交谈,我们可以认识和了解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曾国藩。
既为时局担忧,又感到无能为力、悲观失望
同治六年六月八日天黑不久,曾国藩来找赵烈文聊天,见有客人,就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来久谈。曾国藩说:因为捻军窜到河南东部,未能堵截防御,昨天皇上发下措词严厉的谕旨,对统兵的各位将领予以训斥。沅弟(曾国荃)被摘去顶戴,与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同交部议处。李鸿章戴罪立功。谕旨中还有这样的话:“各疆吏于捻贼入境,则不能堵御,去则全无拦遏,殊堪痛恨!李某(李鸿章)剿贼,已届半年,所办何事?!”语气非常严厉,是近来所没有的。曾国藩为此担心:李鸿章和曾国荃的胸襟和涵养还欠磨练,万一焦躁愤慨起来,以致发生意外,则国家的局面更难预料。大局成这个样子,决不允许再有什么差错发生,否则,“吾恐仍不免北行。自顾精力颓唐,亦非了此一局之人,惟祈速死为愈耳”。曾国藩说这话的时候,神气凄凉,赵烈文一时竟找不到恰当的话语安慰。
八月六日下午,曾国藩又来和赵烈文久谈。当说到捻军进了山东境内,形势越来越严峻,负责剿捻的李鸿章受到朝廷指责,剿捻的任务可能会再次落到曾国藩头上时,赵烈文说:要彻底剿灭捻军,必须把建立骑兵部队作为优先考虑的事情,因此建议曾在江南开辟一处牧场驯养军马,另外在闲田多的地方大力开展屯垦,解决部队的粮草供应问题。曾国藩听了,虽然为之动容良久,却无可奈何地说:“吾老且死,奚暇计久远,足下休矣!”
感叹国家选拔的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同治六年五月十一日,曾国藩到赵烈文处闲谈,说到今天有个四川籍的翰林院庶吉士来见他,言谈举止根本不像一个士大夫;前天也有一个湖南籍的庶吉士送诗给他看,但排律不成排律,古体诗不像古体诗,国家选拔的人才居然是这个样子,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当时久旱无雨,曾国藩忧心忡忡,导致牙根上火。因牙痛得十分厉害,所以跟赵烈文闲谈时,曾国藩常常捂着嘴巴,发出痛苦地呻吟,结果小坐一会就离去了。
九月十四日下午,曾国藩和赵烈文闲谈时,再次说到科举选拔人才:这次在贡院钤榜时,与上江(安徽)朱学台(负责一省教育事业的提督学政)挨着坐,朱学台对考生的文章也不满意,两个考官的举止尤其粗俗。朱学台于是拉着曾国藩的手,在他掌上写了一个“酸”字,曾国藩看后,会意地笑了笑。曾国藩又说:今年录取的这些举人,比甲子科(同治三年)录取的差远了。同治三年即1864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失败,两江总督曾国藩立即在辖境内恢复已经中断十多年的乡试,因此把这一年的考试称为甲子科。
曾国藩言犹未尽,又说道:我驻军祁门县时,祁门城位于山脚下,形势局促,不开阔,很难守卫。我于是对人说,这样的城,又有什么用?不如毁掉它!城里有人知道了这件事,写来一信说:大清朝初年,我们祁门曾经有人中过举,康熙年间一位江西籍的官员来这里当县令后,选定这个地方做县城,到现在一百好几十年了,再没有考中一个举人,您如果决定拆毁城墙,百姓没有不乐意听从的。我于是下令拆毁城墙,建造了不少碉楼,用来防御太平军的进攻。工程竣工后,有人请我写一段城邑记之类的文字,我在上面批了四句话:“拆去西北城,岁岁出科名。东南留一节,富贵永不歇。”说来奇怪,自我做了这个批示后,甲子科乡试,祁门考中了三个举人,今年这一科又考中了两人。曾国藩因此很有感触地说:看来风水先生的有些话,是有它的根据和道理的。赵烈文于是和曾国藩开玩笑说:您有关拆城墙建碉楼这段佳话,应该刻一块石碑,埋到祁门,数百年之后,便完全可以和诸葛碑相媲美了!曾国藩狂笑而去。
人才必须合理使用,有胸襟的人才能取得成功
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下午,曾国藩又来和赵烈文聊天。此次谈话内容非常广泛,论完兵事,又说人才。曾国藩说:“世言储才,不知第二、第三等人可求而储之,第一等人可遇而不可求。李少荃(李鸿章)等才则甚好,然实处多而虚处少,讲求只在形迹。如元浦(曾国荃)之攻金陵,幸而有成,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今渐悟矣。”于是继续发挥说:“人生无论读书做事,皆仗胸襟。”赵烈文表示完全赞同。但当赵烈文建议曾把自己的文章拿出来,早日刻印成书,否则“千载以形迹相求,失公之神矣”,曾却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值得留给后人的东西。
八月二十八日午后,曾国藩和赵烈文谈话时,纵论宋、明时期人物。当说到王船山即使取得高位也未必能治国安民时,曾进一步发挥说:“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出异人……”曾话未说完,赵烈文马上举手打断说:“大哉宰相之言!”曾掩面大笑说:“足下奈何掩人不备如此!”说完又鼓起掌来。正鼓掌时,有人送了一张纸条进来,曾看过后,点头表示同意,然后故作神秘地对赵烈文说:“此何物?足下猜之。”赵烈文说他猜不到。曾说:“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赵烈文对曾的俭朴美德称赞了一番,然后说:“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鸭),亦食火腿否?”曾回答说:“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馈送矣。即绍酒亦每斤零沽。”赵说:“大清二百年,不可无此总督衙门!”曾说:“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说完,两人在大笑中结束了这天的谈话。
自古成就大事的人,都是肯用心的人
同治六年六月十六日午后,曾国藩邀赵烈文到内室谈话,遍论咸丰末年清军致败的原因和诸位将帅的缺失后,曾说:回想周腾虎刚到我军中时,曾对我说,自古成就大事的人,都是肯用心的人。他又说:我普遍观察了长江下游的统兵将领,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料定他们最终都会失败。曾公您目前虽然兵微将寡,但最后能成就大业的人一定是您。曾国藩于是深有感触地说:“余时深佩其‘用心’一语。其论世超出寻常者甚多,不可谓非异才。”周腾虎是赵烈文的姐夫和推荐人,当时正是有了他的推荐,曾才下决心从江西派人并带着二百两白银,千里迢迢赶到江苏阳湖,聘请赵烈文加入自己的幕府。如今周腾虎已去世六年,家眷全靠赵烈文照顾和接济,曾旧事重提,自然会引起赵的伤感,于是话未说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然而还没有坐下,曾就跟过来与赵久谈,至于谈了什么,赵没有详记,估计是一些安慰开导的话语。
官场交情离合,有在情理,有不在情理
同治六年六月十九日,赵烈文到曾国藩处闲谈,问起郭嵩焘和毛鸿宾为何闹矛盾的事。曾国藩说:毛鸿宾早年在京城时,看到郭嵩焘的文章很有文采,就想与他结交,后来毛出任湖南巡抚,又屡次请他做幕友;等到毛鸿宾担任两广总督,就保举郭做广东巡抚。毛的能力平平,郭到任后,毛却以恩人自居,两人又彼此争权,不和就这样产生了。左孟星、王闿运、管才叔三大名士到广东后,互相标榜有王佐之才。郭嵩焘本质上是个文人,这三大名士因此多偏袒郭嵩焘。左孟星甚至写信诋毁毛鸿宾,说他“不齿于人类”。他们两人最后闹成这个样子,平心而论是郭对不住毛,毛鸿宾没有什么过错。曾国藩接着说:因为我曾经保举过毛鸿宾,郭嵩焘后来连我也怨怪上了,说“曾某保人甚多,惟错保一毛季云”。我反唇相讥说:“毛季云保人亦不少,而惟错保一郭芸仙。”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捧腹大笑。赵烈文于是说了几句郭嵩焘不该这样做的话。
此时有客人来,赵烈文只好告辞出来。不一会儿曾国藩跟过来了,接着刚才的话题说:“交情离合,有在情理,有不在情理。刘霞仙(刘蓉)之与朱石翘(朱孙贻),不啻子弟之于(与)父兄,而卒大番至刊诗相诟厉;芸仙之于(与)毛季云,又少次;沈幼丹(沈葆桢)与余亦大番,然余数函修好而不答;李次青(李元度)一番之后,至克复金陵,余曾疏言其功,彼近时常通书问,庶几复合;至左(左宗棠)则终不可向迩(靠近、接近)矣。”
七月五日午后,曾国藩到赵烈文处闲谈,再次说到郭嵩焘和毛鸿宾的事。赵烈文说:郭嵩焘在广东名声狼藉,有人给湖南巡抚骆秉章写信说:故乡的高官大吏都好像豺狼虎豹一样。民间又流传这样的谚语:“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郭嵩焘);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毛鸿宾)。”怎么会败坏到这种地步!曾国藩说:这些坏名声都是他们自取的。比如劝富人捐款捐物,赞助军饷,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来就应该靠自愿,不能强迫;只有对那些为富不仁和向来有劣迹的人,才能采取强制措施。郭嵩焘在广东却不加区别,一概强制执行,所作所为,无不任意而为,怎么不遭反对和非议!郭却悍然不顾,真没想到他会荒谬到这种地步!
能做事的人都有脾气,但不能由着性子来
曾国藩和赵烈文谈话时,经常臧否古今人物。同治六年五月十八日下午,曾来和赵聊天,看到他还躺在床上,就站帐外等候;赵烈文发现后,急忙起来陪他坐下。这天两人谈话很久,涉及刘长佑、官文、胡林翼、左宗棠、李瀚章、李鸿章、吴棠、沈葆桢等众多名人。曾国藩说:“刘印渠极长厚谦下,故做直督数年甚稳,其心地亦端正,性能下人,而非为保位之计。官秀峰城府甚深,当胡文忠在时,面子极推让,然有占其地步处必力争,彼此不过敷衍而已,非诚交也。其心亦止容身保位,尚无险诐,外间传言胡死后,官封提其案卷,则又言之过甚。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己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李小荃血性不如弟而深稳过之,吴仲宣殊愦愦,沈幼丹自三年以前争饷后,至今未通信,其人大抵窄狭……”
六月十七日,曾和赵谈话时,再次历数几位部属的优缺点:“沅浦(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事体安得不糟,见闻安得不陋!”接着又说:“李少荃(李鸿章)血性固有,而气性也复甚大,与沅浦不相上下。李小荃(李瀚章)亦有脾气,杨厚庵(杨载福)尤甚,彭雪芹(彭玉麟)外观虽狠,而其实则好说话,遍受厚庵、少荃、沅浦之气。”赵烈文说:“做事人总有脾气,不然也做不成。”曾国藩说:“甚是!”
八月二十五日,曾国藩和赵烈文闲谈时,再次说到自己的心爱弟子李鸿章:“李少荃在东流、安庆时,足下常与共事,不意数年间一阔至此。”赵烈文说:“烈(同治)元年冬到沪(上海),少帅犹未即真苏抚,邀烈坐坑(炕),固问老师处有人议鸿章者否?意甚颛颛。不一月实授,从此隆隆直上,几与师双峰对峙矣。”曾国藩说:“湘、淮两军之始末区奥,足下殆无不洞若观掌矣!”说完含笑而去。
对自己的耐性和倔强十分欣赏
同治六年五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到赵烈文处久坐。当说到李鸿章剿捻遇到麻烦时,曾说李性子急,遇事缺乏耐性,军事成败是常有的事,如果朝廷要求他尽快取得成效,或者言官对他抨击一通,他一定不能忍受。说着说着,曾国藩情不自禁地自我表扬起来:“余自乙丑年(同治四年)起,凡七次被参,总以不变不动处之,少荃未必有此耐性耳。”
对于自己的耐性和倔强,曾国藩确实十分欣赏。同年八月二十八日,当赵烈文谈到李鸿章“事机不顺,未必能如师宏忍”时,曾国藩立即不无得意地说:“吾谥法为‘文韧公’,此邵位西(邵懿辰)之言,足下知之乎?”
有一股誓不服输的劲头
曾国藩不仅性格倔强,做事有耐性,而且有一股誓不服输的劲头。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曾与赵烈文闲谈时说:我最初在京城做官时,与许多名士有交往。当时,梅曾亮(字伯言,桐城派后期代表人物)因为擅长写古文,何绍基(字子贞,清代著名书法家,尤长草书)因为擅长书法,在士大夫中间享有盛名。我经常观摩他们的作品,觉得自己不比他们差多少,心想只要多读书,勤努力,以后或许也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水平。但是没过多长时间,我的学问没有做成,官却越做越大,每天与公务文书打交道,只能把读书做学问的愿望和志向压在心里。咸丰以后,我奉命讨伐太平军,戎马倥偬,更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拿书本。如今再读梅曾亮的文章,发现确有过人之处,说明自己当时的一些想法,还是意气的成分居多。不过到现在我还是坚持认为:只要能够给我读书做学问的时间,对梅曾亮、何绍基这些人,还是不甘拜下风的。曾国藩一停嘴,赵烈文就鼓掌大笑说:每个人的想法,真是难以说清!有的人做了皇帝,却喜好臣下的称号,于是汉朝有自称为富平侯(汉成帝刘骜沉溺声色犬马之中,常常假借富平侯张放的名义在长安城内外玩乐)、明朝有自称为镇国公(明武宗朱厚照在佞臣江彬的怂恿下,自封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到边地宣府亲征,回去后又给自己加封太师)的皇帝;老师的事业超越千古,唐、宋以下几乎无人能比,却遗憾自己的文章和书法技不如人,老想跟他们一比高低!不过从老师这番话语里,我也真切感觉到您的志向历来不凡,有一股誓不服输的劲头,这可能正是您能够发挥自己的最大潜能,最终战胜太平天国的原因吧!曾国藩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为一笑。”
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什么放不下
同治六年五月十七日,曾国藩看到赵烈文在读佛教典籍,就开口问其中的含义。听了赵解释后,曾又嘱赵解释佛经梵文名词,以便于自己阅读。十天后的五月二十七日,赵烈文送了一本《圆觉经略疏》给曾国藩,并为曾国藩解释和翻译其中的名词术语,抄写一册给他备查。
因为对佛学有共同兴趣,所以在五月十七日的谈话中又把话题转到《庄子》上来。曾国藩说:你刚才所说佛教经典的意境,《庄子》一书也有论述。赵烈文说他对《庄子》没有很深研究,不敢擅自断言。接着他就顺着《庄子》的话题问曾国藩:老师的学问阅历十分丰富,大事与小事,成功与失败,大喜与大悲,都经历过、体验过,人生可以说达到了很高的境界,现在对自己能否做到十分的把握呢?曾国藩对这个话题似乎很感兴趣,于是摸着胡须想了很长时间,才回答说:把握不敢说。但目下想来,就是有股不怕死的精神,因此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本着死的想法,不知算不算足下所说的把握?赵烈文说:一切至高至大的境界,都不过生死,连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什么放不下呢!不过从佛学的最高境界来看,不怕死仍然是境界未到至高至大啊!因为不怕死仍然是有一念在心中,还没有到真本原。曾国藩听后,表示完全赞同。
七月十九日下午,曾国藩到赵烈文处闲谈,坦露自己多年来艰难困苦终于有所成就的心路历程。他说:我刚创办湘军那会儿,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怀疑,对我的非议和诽谤也很多。靖港之败后,更是受到湖南地方官僚的指责和谩骂,布政使徐有壬、按察使陶恩培甚至要求骆秉章弹劾我。我的部下出入长沙城,也是“恒被谯诃,甚有挞逐者”。咸丰四年以后,我在江西作战数载,遭遇挫折,经历了各种磨难,更是成了众矢之的。咸丰八年重新出山后,朝廷忽而让我进兵四川,忽而让我援助福建,自己丝毫不能做主。到了咸丰九年,因为得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支持,彼此亲如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
总督衙门也藏有“私盐”
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曾国藩到赵烈文处,见他正在吃饭,就没有进去。饭后,赵到曾内室久谈。曾国藩将《五礼通考》的最早刊印本拿给赵看,笔画如手写一般,十分可爱;曾又把进呈给皇上的《御批通鉴》刊印本拿给赵看,赵无意中看到书堆中夹有民间刊刻的《红楼梦》,十分惊讶,于是笑着和曾打趣说:“督署亦有私盐邪!”《红楼梦》是禁书,盐由国家专卖,曾国藩私读禁书,当然与私卖食盐一样,都属违法行为。
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
督署不仅有“私盐”,而且曾家也有一本难难念的经。同治六年九月十日,曾国藩设宴为赵烈文饯行,菜肴非常丰富,谈话尤其畅快。赵这次是去湖北看望在那里做巡抚的曾国荃(曾国荃出山做湖北巡抚后,上章弹劾湖广总督官文,一石激起千层浪,京中流言四起,曾国荃自己也陷入极大的困境中),所以曾国藩的谈话主要是围绕自己的家事进行。
曾国藩说:“未受寒士之苦,甫欲求馆而得乡解,会试联捷,入馆选。然家素贫,皆祖考操持。有薄田顷余,不足于用。常忆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假归,闻祖考语先考曰:‘某人为官,我家中宜照旧过日,勿问伊取助也。吾闻训感动,誓守清素,以迄于今。皆服此一言也。而家中亦能慎守勿失,自昆弟妻子皆未有一事相干,真人生难得之福。亲族贫窘者甚多,虽始终未一钱寄妻子,顾身膺膴仕,心中不免缺陷。复得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我偿素愿,皆意想所不到。家中虽无他好处,一年常无病人,衣食充足,子弟略知读书,粗足自慰。”赵烈文说:“聆师所述,足见积累之厚。至家庭相谅,子孙逢吉,皆师清德所感。上天报施之道,屈彼申此,自然之数也。”
宴请结束后,赵烈文去别人那里走动,回到总督衙门已是初鼓时分。听说曾国藩两次来找过他,赵当即赶了过去。一见到赵,曾国藩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这回主要是说他的九弟曾国荃:“乡间塘泺所时有,舍弟宅外一池,闻架桥其上,识之者以为似庙宇,所起屋亦极拙陋,而费钱至多,并招邻里之怨。”赵烈文有些不解地问:“费钱是矣,招怨胡为者?”曾国藩说:“吾乡中无大木,有必坟树,或屋舍旁多年之物,人藉以为荫,多不愿卖,舍弟已必给重价为之,使令者则从而武断之。树皆松木,油多易蠹,非屋材,人间值一缗者,往往至二十缗,复载怨而归。其从湘潭购杉木,逆流三百余里,又有旱道须牵拽,厥价亦不啻数倍。买田价比寻常有增无减,然亦致恨。比如有田一区已买得,中杂他姓田数亩,必欲归之于己,其人或素封,或世产,不愿则又强之。故湘中宦成归者如李石湖、罗素溪辈买田何啻数倍舍弟,而人皆不以为言,舍弟则大遗口实,其巧拙盖有天壤者。”赵烈文说这正是沅帅为人厚道的地方。官宦之人回到原籍后,购置产业是正常情况,与其做得巧妙,不如拙实好。拙不过损害一时的清廉名声而已,心意毕竟是好的,没有刻薄寡恩之嫌,一定能给子孙带来福祉。即使遇上兵荒马乱年代,因为是用厚实得来,所以忧患也比较轻。曾国藩说:“此理诚是,然如舍弟亦太拙矣。忆咸丰七年,吾居忧在家,劼刚(曾纪泽)前妇贺氏,耦耕(贺长龄)先生女也,素多疾,其生母来视之,并欲购高丽参。吾家人云:‘乡僻无上药,既自省垣来,何反求之下邑邪?’对曰:‘省中高丽参已为九大人买尽。’吾初闻不以为然,遣人探之,则果有其事。凡买高丽参数十斤,临行装一竹箱,令人担负而走,人被创者则令嚼参以渣敷创上,亦不知何处得此海上方。”赵烈文大笑说:“沅帅举动真英雄不可及,书之青史,古人一掷百万,奚以过之。”随后又问曾国藩四弟(曾国潢)是怎样一个人?曾国藩说:“极长厚人,而好事喜功,不顾清议则同。在乡有狱讼,县邑不能决者,往往来诉,辄为分剖,胜者以为所应有,负者则终身切齿。足下视此,以为居乡宜乎否乎?”赵烈文紧皱眉头想了会儿,说:老师兄弟一别,已经十年了,何不招四弟来此一游?曾国藩说:“吾久为斯说而不见听,奈何!方今多故,湘中人人以为可危,两舍弟方径情直行,以敛众怨。故吾家人屡书乞来任所,以为祸在眉睫。”
无话找话,相互调侃
曾国藩和赵烈文的谈话不仅海阔天空,无所不包,而且常常无话找话,相互调侃。如同治三年七月八日下午,赵得知曾被清廷封为一等侯,就入内贺喜,并打趣说:“此后当称中堂,抑称侯爷?”曾笑着说:“君勿称猴子可矣!”说完,两人都大笑不止。又如同治六年九月六日,曾国藩到赵烈文处闲谈,当时刚好有人送给曾一只古碗,非常大,于是对赵烈文说:“余脾胃甚坏,故欲得数小碗盛菜,期醒目耳。今此大碗安用之?”赵听得有趣,也忍不住开起玩笑来:“甚有用处。”曾很认真地问有什么用?赵烈文说:“烧满碗鱼翅以饫烈,亦妙事也!”曾于是大笑说“诺!”赵也大笑说:“烈今年三十有六而童心方盛,奈何?”曾说:“此正过人处。”说话间,曾国藩脱下马褂放到床榻上,谈话结束时忘了带走,赵拿起一看,不仅面料里料都很普通,而且非常短小,贫寒之士都很少穿这种衣服,赵烈文为此感叹不已。
像这类相互打趣的事例,赵烈文日记中随处可见。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生动有趣的细节,才在我们面前呈现了一个完整而又真实的曾国藩。